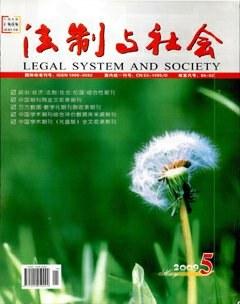被害人品格證據研究
范紅達
摘要隨著品格證據研究的日益深入,被告人、證人品格證據已經有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是被害人品格證據目前在理論界和立法上都還是空白,亟待深入探究。本文首先闡述了被害人品格證據的定義、使用前提等基本內容,然后針對整個品格證據的共性問題相關性進行論述,進而提出被害人品格證據具有獨特的相關性并對被害人品格證據存在的價值予以分析。
關鍵詞被害人品格證據 相關性 聯邦證據規則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5-035-02
一、刑事被害人品格證據概述
所謂品格證據是關于一個人的個性特征的證據,是基于名聲或是意見確定的,關于一個人道德地位的證據。品格證據所特有的傾向性可理解成為一種行為意向趨勢或者偏好,依照邏輯推理我們可知:在其它條件相同的前提下, 同不具有某種行為傾向的人相比,具有某種行為傾向的人更容易在特定場合下實施符合其行為傾向的行為。這就是品格證據具有證明價值的原因。許多學者認為習慣應該包含在品格之中,筆者認為這是不恰當的。倘若假定習慣屬于品格證據的一種,那么根據美國的《聯邦證據規則》對品格證據一般持排除態度,故習慣作為品格的一部分也應被排除,但事實卻是相反:習慣或操作規程對證據對于具體場合下的行為是非常有利的證明,可見習慣具有自身獨特的證明價值,不應屬于品格范圍之內。
在刑事訴訟中,品格證據包括被告人品格證據、被害人和證人的品格證據,但是被害人品格證據由于被害人在訴訟中地位的特殊性及不同法系司法制度的差異性從而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重要性。首先表現在被害人品格證據既可以作為直接證據證明案件主要事實也可以成為間接證據證明具體事實,前者往往是在“品格處于爭議”的情況下,即被害人品格證據構成刑事犯罪或辯護要件。但絕大多數的案件被害人品格證據是當作間接證據使用的。其次,筆者注意到被害人品格證據具有特殊的適用范圍。被害人品格證據的使用一定是發生在侵犯公民人身、財產及民主權利的案件,嚴格來說這個范圍還應該縮小到在被害人可能有過錯的暴力侵犯案件。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在一起盜竊案件中,被告人舉證要證明被害人具有撒謊的品質或是暴力傾向的品格是很荒唐的。
二、被害人品格證據存在的價值
由于被害人品格證據其證明對象主要是“誰先動手”的爭議事實,雖不會出現像通常關注被告人卑鄙的品格那樣使陪審團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影響,不過被害人品格證據還是屬于品格證據仍然會給陪審團帶來一些偏見,但我們必須看到被害人品格證據的價值:
(一)在客觀上有利于保障被告人辯護權利
一個人刑事被告人不應該在沒有任何機會提出合理懷疑的情況下而去面對定罪的結局。被害人不良的品格證據的證明是一種懷疑,由被告人首先提出被害人品格證據后的確會使陪審團因此產生被告人無罪的懷疑。允許并采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供的證明被告人品格良好的證據,給予被告人機會充分進行辯解,增加了被告人被宣告無罪或者罪輕的可能性,加大了公訴方證明被告人有罪的難度,這也體現了保護被告人的司法價值取向。
(二)從實證的角度分析被害人品格證據
陪審團對于一個已經死亡或者重傷的被害人的心理態度是同情或是憐憫,即一個“好”的印象。即使被告人提出若干被害人不佳的品格證據,如果把之量化的話是從對于被害人品格“好”的印象中減去“壞”的印象。其結果還是“好”或是有點“壞”。相反,若把被告人品格證據量化的結果是從陪審團對被告人“壞”的印象再加上“壞”的印象,這勢必會使陪審團對被告人不佳的品格過分關注,忽視案件事實的重要性從而導致誤判的發生。但是對于被害人品格證據而言,所引起的不公正偏見相對于被告人品格證據要小的多。喬治·E·狄克斯說過:“你看不見它(證據)的價值要比排除它的危害大。”被害人品格證據固然有其天生的不足和缺陷,但關鍵在于如何制定合理的證據規則在保證發揮其證明價值的前提下盡量減少其危害。在被害人品格證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國家的證據規則可以為我們所借鑒,比如美國的《聯邦證據規則》。
三、《聯邦證據規則》對我國證據立法的借鑒意義
眾所周知,普通法國家在品格證據方面規定的嚴謹和細致成為其他國家紛紛仿效的對象。我國由于在品格證據立法上的缺失從而使得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實現變得困難,所以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自己的品格證據制度。在借鑒的對象上筆者認為鑒于刑事訴訟程序上的相似性,選擇美國的《聯邦證據規則》是合理的。
(一)聯邦規則404(a)(2)之分析
通常情況下, 被害人的品格在刑事案件中與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之間是沒相關性的。因此檢察官不能主動提出被害人的品格證據,只有當被告人提出被害人具有不佳的品格證據后才可以提出反駁意見。在這里需要特別注意兩點,首先是檢控方反駁的對象必須是“同一品格特性”的證據即在原文中的“rebut”一詞。檢控方反駁的限制范圍是被告人提出關于被害人的品格的特征,比如被告人提出被害人具有暴力的品格證據,那么控訴方只得就暴力這一范圍的特性進行反駁。
其次,有很多學者主張檢控方一律不得首先提出被害人品格證據,這其實是個認識錯誤。在一般案件中這種主張是成立的,但是在兇殺案件(我國刑法規定的故意殺人)中,控方可以在被告人沒有提出被害人品格證據的前提下,首先使用被害人平和的品格證據予以反駁。我們不難發現這樣規定的理由,由于案件性質的特殊性,檢控方提出被害人品格證據所產生的不佳后果要小于在一般案件中的使用,立法者所擔心的不良結果不會發生。
由于本條中對被害人品格證據的一般規定,故可以在我國立法中予以直接借鑒。但是對于其例外情形,筆者認為這不僅是涉及證據法更重要的是對刑事訴訟基本價值的規定。目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沒有堅持“無罪推定”價值取向,對于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沒有像美國那樣重視。倘若不改變目前現在的“有罪推定”的態度,那么404(a)(2)條的規定在我國是行不通的。
(二)性侵犯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證據的研究
從《聯邦證據規則》412(a)的規定可以理解為兩層含義:第一是所有涉及被害人性行為或性傾向的名聲或意見證據絕對不可采。第二就是在一般情況下涉及被害人性行為或性傾向具體行為的證據也不可采。聯邦規則412條其重要價值就是作為404(a)(2)的例外出現,換句話說就是在一般情況下有關被害人的性行為或性傾向的證據是予以排除的,但也有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為前兩個例外過于精確從而限制了最后例外情形的合理范圍。聯邦規則的起草者也許發現這個問題,于是就用“(C)該證據被排除會侵犯被告人的憲法權利”作為其他例外情況的兜底條款來使用。
如果從法理上來研究,憲法的地位遠大于聯邦規則,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必然憲法會具有優先適用的權力。這個問題在法理上是合理的,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卻使審判者陷入窘境。在一起性侵犯案件中,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原則”使被告人有權向法院提出調查被害人是妓女的證據,以證明被害人是同意的并具有誣告嫌疑,這樣做毫無疑問是符合憲法的。但卻不折不扣地違反了412條(a)規定的,但最高院還是會裁定被告人的舉證有效。我們知道憲法是以保護被告人的憲法權利和人權為目的,聯邦證據規則更側重保護被害人的隱私權及防止陪審團不公正的偏見。筆者認為不妨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法官來調和憲法和聯邦規則的價值沖突。法官是否應該允許被告人基于憲法的權利得以提出違反聯邦規則的規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這種違反應該是有個標準的,那就是被告人提出被害人有關性的品格證據所具有的證明價值是否明顯大于給被告人帶來的(名聲)損害,并明顯大于給被害人帶來不公正判決的危險。
“在強奸、猥褻等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可以提出一切關于被害人性行為或性傾向的證據。公訴人和被告人律師必須在開庭前十日以內在法院進行證據交換、相互質證并由法官決定證據是否被采納。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只得就已經采納證據的證明力進行交叉詢問。被告人經過法院同意才可以提交新證據,但必須重新組織對該證據的質證。”這是筆者對我國強奸類案件的立法建議。筆者認為在一個秘密、封閉只有控辯審三方的環境下,普通法所擔心的種種對被害人的“第二次傷害”不會發生,反而會使被害人鼓起勇氣積極配合控訴方追訴犯罪,更快更好地查明案件真相。因為在開庭前的秘密的證據交換和質證,已經由法官排除了諸多不具有相關性的證據,在正式開庭后只會對已被采納的證據的證明力予以辯論,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被害人的隱私權。同時這也保障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允許他提出一切關于被害人性行為或性傾向的證據,不會出現像聯邦證據規則412條(b)(C)模糊不清的易導致混亂的憲法條款。
參考文獻:
[1]高智忠.美國證據法新解-相關性證據及其排除規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美]喬恩·R·華爾茲. 何家弘譯.刑事證據法大全.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劉立霞,田野.刑事被告人品格證據相關性研究.燕山大學學報.2007(1).
[4]陳一云.證據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宋 勝尊.罪犯心理評估.北京:群眾出版社.2005年版.
[6]陳界融.美國聯邦證據規則(2004)譯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7]GeorgeE.Dix. McCormick on Evidence. America: Law press,1999年版.
[8]李子煊,王進.美國品格證據規則及其借鑒意義.安徽理工大學學報.2006(8)年版.
[9]蔡巍.美國品格證據規則及其訴訟理念.法學雜志.2003(24).
[10]黃士元,吳丹紅.品格證據研究.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2(10).
[11]何家弘,姚永吉.兩大法系證據制度比較論.比較法研究.2003(4).
[12]Notes of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Report No.93-65.
[13]Ronald J. Allen. Evidence text, Problems, and Case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Lnc.2006.
[14]王利平.簡析品格證據.法制與社會.2007(3).
[15]張曙.論刑事訴訟中的不良證據.吉林公安高等學校學報.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