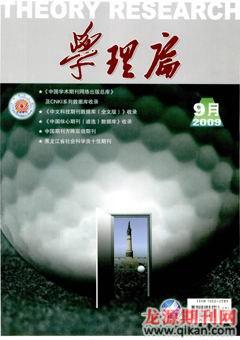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若干思考
時照建
摘要:本文提出了為什么理論研究從開放現行文件“熱”到政府信息公開“冷”、政府信息公開等不等于檔案信息公開等問題,談了政府信息公開引發的檔案理論困惑并進行了思考。
關鍵詞:政府信息公開;文件;檔案;檔案理論
中圖分類號:D630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3—0015—02
1.為什么理論研究從開放現行文件“熱”到政府信息公開“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沒有正式頒布實施前,在我國檔案館就普遍建立了現行文件利用服務中心,向社會開展了提供開放現行文件利用服務。這一新興事物的出現對檔案學的相關理論也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國檔案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研究,力求為開放現行文件尋求理論上的支持和解讀。一段時間內發表了許多關于開放現行文件的理論研究文章,形成研究熱潮。但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隨著《條例》頒布,這種理論研究卻戛然而止了,由“熱”忽然變“冷”。然而,問題并沒有解決。第一,對開放現行文件的理論研究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也沒有一個觀點能對開放現行文件這種現象給以合理的解釋。對于現行文件公開利用的理論依據,王茂躍先生認為:主要有四種觀點,其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其二,文件與檔案管理一體化理論;其三,借用委托——代理理論;其四,現行文件的第一價值和第二價值理論。并對這幾種觀點進行了簡評,基本上予以否定。他認為:“從我國現有的檔案學理論中,我們找不到開放現行文件的理論依據”,“探索精神可嘉,但得出的結論卻難以令人信服”。[1]不管是持肯定的還是否定的觀點,都忽略或者回避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現行文件可以公開利用,而轉化成檔案后,卻要封閉30年后才可以開放被利用。這個問題不解決,任何關于現行文件公開利用的檔案學理論依據都沒有說服力。第二,《條例》的頒布,并不能代替理論研究,《條例》的頒布只是對開放現行文件給以法規方面的規范,并不解決理論問題。為什么檔案理論界由對開放現行文件的理論研究“熱”到《條例》頒布后的理論研究“冷”?這里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2.政府信息公開等不等于檔案信息公開
《條例》規定:“屬于主動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應當自該政府信息形成或者變更之日起20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但是《檔案法》則規定:“國家檔案館保管的檔案,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三十年向社會開放。”于是,人們產生疑問,已經列入政府信息公開范圍的文件材料,“文件在政府機關已經予以公布,待歸檔保存一定年限移交檔案館后反倒要經歷‘形成滿30年的考察,從邏輯推理上似乎具有諷刺意義,從現實執行上似乎也存在程序矛盾。”[2]那么,政府信息公開等不等于檔案信息公開?對此,理明先生認為:“政府信息公開≠檔案信息公開”,“承載政府公開信息的文件(以下暫限于人們通稱的‘已公開現行文件)與其內容相同的館藏檔案,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所謂聯系者,即檔案是由文件轉化而來的,”“所謂區別者,文件轉化為檔案是有條件的,并非所有文件都可以轉化為檔案,它必須經過辦理完畢、區分價值,對于有長期保存和利用價值的文件,再按照一定規律整理后,才能真正轉化為檔案。同時,文件歸檔有法定的范圍,尤其要強調歸檔文件的原始性,即不具有原始記錄性的文件,不能隨意轉化為檔案。就拿現行文件來說吧,一份已公開的現行文件,人們能夠識讀到其中的內容信息,而當該份文件歸檔的時候,檔案人員還要收集這份文件形成過程中產生的背景信息,如文件的起草人信息、修改經辦人與修改經辦信息、簽發人與簽發信息,等等。這些背景信息與正式頒發的文件一起,構成了該份文件的檔案。也正是這些背景信息,保持了該份文件的原始記錄性,使得該文件具有了檔案的本質特征。一份重要的文件,正式發布時只有短短的幾頁紙,但當它歸檔時,要形成數十甚至數百頁檔案,道理就在這里。”[3]理先生提出的觀點很新穎,論述的有道理,然而,仔細分析問題就出來了。理先生的論述既不符合檔案學基本理論,概念也不清。其一,檔案是由文件轉化而來,還是由文件+文件背景信息轉化而來?其二,收集“文件形成過程中產生的背景信息”是不是文件轉化為檔案的必要條件?其三,正式頒發的文件沒有原始記錄性嗎?其四,理先生理解的“檔案是有文件轉化而來”中的“文件”指的是什么?是正式頒發的文件+文件背景信息?正式頒發的文件是不是文件?
劉東斌先生與理明先生有相同認識,也認為:“文件和檔案是兩種不同的事物,文件開放并不等于檔案開放,所以才有現行文件的公開,才有檔案的封閉期。”[4]但是,與理先生相反,劉先生卻是用他的顛覆傳統經典檔案學理論的“檔案形成在前論”來解讀,劉先生的“檔案形成在前論”認為:“檔案形成在前,是原始記錄,是文件的前身”,“文件則是檔案最終稿本的復制件”。[5]劉先生說的雖有道理,然而,其理論前提是“檔案形成在前論”,這畢竟是一家之言,并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可。而且,也有一些疑點值得商榷,劉先生將收文排除在檔案之外就是問題。
政府信息公開等不等于檔案信息公開?《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再看《檔案法》第二條:“本法所稱的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歷史記錄也是一種信息,兩者并沒有什么不同。現行的可以公開,歷史記錄更應該公開,為什么不能公開呢?再看《條例》第十條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應當重點公開下列政府信息:”“扶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實施情況”;第十一條:“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縣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重點公開的政府信息”,“搶險救災、優撫、救濟、社會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況”;第十二條“鄉(鎮)人民政府”“重點公開下列政府信息”:“搶險救災、優撫、救濟、社會捐助等款物的發放情況。”這些信息不就是民生檔案嗎?政府信息公開等不等于檔案信息公開?實在令人困惑。
3.筆者的思考
對于政府信息應該公開而檔案卻要封閉30年后才可以開放被利用的問題,理明先生提出的:“政府信息公開≠檔案信息公開”[3]觀點和論述,雖然合理地解釋了這種現象,而且論述的很有道理,也是事實。理先生說的對,文件可以開放,但是,文件的背景信息是需要一個封閉期后才能開放的。把正式文件與文件底稿及發文簽一同存檔,也是檔案實踐中經常要求和經常做的。然而,理先生的解釋卻引出了檔案學理論的更多問題,究竟什么是“文件”?檔案學理論所說的“文件是檔案的前身”“檔案是由文件轉化而來的”中的“文件”是什么?是由“正式文件+文件背景信息”組成的嗎?正式文件是不是文件?如果理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話,那么,其一,傳統經典的“檔案是由文件轉化而來的”理論就有問題,或者是其中的“文件”概念有問題,其“文件”概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件概念,而是包括“正式文件+文件背景信息”在內有特殊含義的概念;其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也有問題,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檔案是處于文件生命周期中的第三或第四階段,也就是非現行文件。既然正式文件(現行文件)已經不具備原始性,又不含有文件背景信息,它怎么能運動到第三或第四階段成為檔案呢?它運動到第三或第四階段就自己增加了文件背景信息了嗎?其三,文件價值理論也有問題,文件第一價值(現行文件)它根本沒有文件背景信息,它怎么能過渡到檔案就有文件的第二價值(檔案)呢?其四,“檔案形成在前”的觀點正確嗎?劉東斌先生同樣認為檔案包含文件和文件背景信息,符合理先生的觀點,但是,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完全顛覆了經典的檔案學理論,同樣讓人困惑,到底是文件形成在前,還是檔案形成在前?
究竟是現有的檔案理論錯了,還是理先生的觀點錯了?劉先生的觀點對嗎?理先生和劉先生強調檔案包含文件背景信息,這不僅是檔案實際工作中經常做的,而且,在信息時代,為保證電子檔案的真實性,更是強調“內容、背景和結構成為文件的三種要素”[6]看來兩位先生說的沒有錯,那么是檔案理論有問題?雖然,這有些令人困惑,但是,兩位先生的觀點為認識什么是檔案,發展檔案學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
對于政府信息公開引發的檔案學理論的困惑和問題,筆者認為,在檔案學理論研究中要遵循系統性、連續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其一,系統性。檔案學理論應是系統的,在這個理論系統中,尤其是檔案學基本概念和檔案學基礎理論應基本系統一致,互相吻合,不應出現在局部合理,而與系統中的其他部分不相協調或者自相矛盾的現象。其二,連續性。檔案學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如果是基本正確的話,那么,它就應該有連續性,它不應因不同需要的變化而變化,檔案的本質應該說是不會變化的。不應不顧檔案學的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把某些非檔案本質的屬性放大成檔案的本質屬性。其三,獨立性。檔案學理論雖不應脫離實踐,但也有相對的獨立性,它不為解釋實踐的合理性而存在,某些實踐的存在并不完全合理。某些法規也不能代替檔案學理論。
參考文獻:
[1]王茂躍.開放現行文件理論依據的若干觀點簡評[J].北京檔案,2004,(3).
[2]陳永生.從政務公開制度反思檔案開放——檔案開放若干問題研究之二[J].浙江檔案,2007,(7).
[3]理明.政府信息公開≠檔案信息公開[J].浙江檔案,2008,(1).
[4]劉東斌.檔案形成在前說對現行文件公開利用的解讀——七論檔案形成在前[J].檔案管理,2008,(4).
[5]劉東斌.檔案形成在前說對電子檔案管理的啟示[J].檔案管理,2007,(3).
[6]馮惠玲主編.電子文件管理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2.
(責任編輯/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