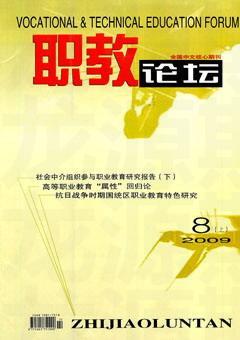高等職業教育“屬性”回歸論
黃 蕾
摘要: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從制度層面、決策層面上看名不符實。且偏離其屬性甚遠。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關鍵是:從內涵上發展必須回歸高等職業教育“高等”的屬性、“職業”的屬性,使其體現高等職業教育的多層次性和高等職業教育的職業學位(職業準入資格證書)功能;從外延上發展必須回歸高等職業教育的“大眾(普及)”屬性,使其規模蓋過全日制非職業類型高等教育。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本質屬性;回歸
作者簡介:黃蕾(1973-),女,湖北天門市人,武漢商業服務學院工商系副教授,碩士,武漢市優秀青年教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實務和高等教育。
基金項目:武漢市屬高技科(教)研項目“高職人才培養模式研究”(項目編號2008K022)的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7518(2009)22-0018-04
有關高等職業教育屬性的論述可謂眾說紛紜,對其屬性的理解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但對高等職業教育是否體現其屬性幾乎沒有涉及。是否反映其屬性鮮有探討。事實上,高等職業教育的屬性論僅僅停留在理論上,僅僅停留在研究之中。高等職業教育的實踐離其屬性尚有一段距離,最為明顯而典型的是制度層面、決策層面偏離高等職業教育的屬性。從外延到內涵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關鍵是高等職業教育必須回到其屬性的軌道,沿著自身的本質屬性前進。
一、高等職業教育回歸“高等”的屬性
高等職業教育首先是一種高等教育。高等職業教育是中學教育之后實施的專門教育,確切地說是高中階段后進行的各種專門教育。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制定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nternatip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Of Edu—cation,簡稱ISCED)1997年版的描述。高等教育為“第三級教育”。“第三級教育”不是泛指高中后的教育階段,ISCED將整個教育體系劃分為7個層次。其中ISCED4屬于高中后的非高等教育階段,為“非第三級教育”階段。“第三級教育”分為兩個階段:“第三級教育第一階段”(ISCED5)有大學專科、本科、碩士研究生三個層次:“第三級教育第二階段”(ISCED6)是“通向高等研究資格證書”的階段。即獲取博士學位的階段(博士研究生階段),這同我國高等教育(無論全日制高等教育,還是成人高等教育)劃分為專科、本科、碩士、博士研究生四個層次是一致的。足見,無論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還是與國際慣例接軌,完整的高等教育應該是四個層次,而專、本、碩是基本的層次。高等職業教育偏離“高等性”在于其既偏離高等教育的完整性、偏離高等教育的層次性,又偏離高等教育的基本層次性。具體表現是高等職業教育終止(終結)于專科層次,本科及以上層次與高等職業教育無緣。高等職業教育失去了內涵發展上升的通道,失去了發展內在的驅動力。由于高等教育體制層面、決策層面封閉了高等職業教育突破專科的層次,致使高等職業教育定勢地被看成是高等教育的最低層次、最低擋次。高等職業教育與專科劃等號,這一信號似乎表明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四等公民”,其社會影響不言而喻。一些地方、一些教育部門并不把高等職業教育當回事,有高中校長說。上級考核和各高中暗暗較勁的是本科升學率,特別是比一本率,高中教育的升學率指揮棒已悄然變為“升本率”、“升本率”,高職已不屬于大學之列了。于是,高職院校紛紛想跳“職業門”,通過各種途徑“專升本”(“專并本”),一旦擺脫“專科”的身份,就可去掉“職業技術學院”的后綴,堂而皇之成為非職業類高等學院。正由于本科、碩士等層次高等教育無“職業”之說。故一些院校升“本”、改成“大學”之后就找不到北了,不知道該如何定位了。
應還高等職業教育“高等性”的本來面目,一方面,使一部分本科院校恢復其高職教育的身份,另一方面,使一些師資力量雄厚、實訓基地建設已具規模、校企合作融洽、市場導向良好的高職院校“專、本”兼招。一旦條件成熟以“本”為主,可考慮招“碩”。高等職業教育回歸“高等性”方可使其內涵發展步入良性循環,使高等職業教育看清發展方向,明確發展目標,不會因盲目升“本”而舍掉職業教育的根本。相反,高職院校“專升本”不是高等職業教育的削弱,而是高等職業教育的加強,是高等職業教育內涵式的發展,是從根本上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視。
二、高等職業教育回歸“職業”的屬性
高等職業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的“起步價”、不是高等教育中的底層,不是高等教育中的一個層次,而是高等教育的一種類型。“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國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職業教育不同于研究型、工程型高等教育,不是培養學術型人才、工程型人才,而是培養技能型人才。高等職業教育以培養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急需的高技能專門人才為背景;以傳授某種職業(崗位群)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為教育內容;以面向就業,重要的是面向企業,滿足企業對有創新精神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為目標。但是,高等職業教育的這種職業性在制度層面、決策層面并未得到認可,其表現是高等職業院校只能發專科文憑,只能證明學生是否專科畢業,別無其他。于是。要求高等職業院校推行“雙證書”制度,要求高職畢業生取得“雙證書”的人數達到80%以上。也就是說,高職畢業生不僅要拿專科畢業證書,而且還要拿職業資格證書,高等職業教育的職業性只能通過職業資格證書的獲得率來衡量。一方面,國家從形式上承認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個類型,具有職業性;另一方面,在操作層面上又不授予高等職業教育機構有發放職業資格證書的權力,高職生只能參與由有關部門組織的職業技能考試獲取職業資格證書,事實上。高等職業教育是否具有“職業性”,是否是合格的高職院校不是由學生是否獲得畢業證書、是否受企業歡迎決定的,而是由職業技能鑒定機構組織的考試一錘定音,即看高職生是否能拿到他們的考試合格證書。高等職業教育冠之以“職業技術學院”名實不符。
高等職業教育鎖定專科層次,使其低人一等,高等職業教育的畢業證書與職業不沾邊,有違其職業性。高等職業教育偏離職業性的后果有四;一是學生忙于考證,既參加校內的常規考試拿畢業證,又參加社會上的考試拿職業資格證:二是高職院校的教學秩序、實訓與實習往往會受制于學生的職業資格證書考試:三是增加學生的學習成本,應付“雙證”考試,既增加費用開支成本,又增加精力支出成本;四是高等職業教育面向職業(崗位群)的可信度降底,高等職業教育只剩下專科教育一重性了。
高等職業教育回歸“職業性”的關鍵是使其畢
業文憑與相應的職業資格等值(劃等號),同時,與完善高等職業教育的“高等性”相配套,建立“職業學位”制度。從另一個角度講,不能授予“職業學位”的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嗎?全日制的非高等職業院校可以授予學位,非全日制的成人高等教育亦可以授予學位,唯獨全日制高等職業教育不能授予學位,是歧視看不起高等職業教育呢?還是不信任高等職業教育呢?
高等職業教育使其職業姓名至實歸的重要途徑是畢業文憑與職業資格掛鉤,推行專業學位(職業學位)制,克服眼下高職院校發畢業文憑,職業技能鑒定機構發職業資格證書的狀況,使“雙證書”合成“一證書”。使高等職業教育同學位相聯系。高等教育學位的授予有兩類:一類是學術性學位,另一類是專業性學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并于1996年7月22日頒發的《專業學位設置審批暫行辦法》第二條規定:“專業學位作為具有職業背景的一種學位,為培養特定職業高層次專門人才而設置。”其目的是“加速培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高層次應用性專業人才”。如果說法律、醫學、建筑等是以律師、醫師、建筑師等職業為背景可以授予專業學位的話。那么,高職院校則是最典型的以職業(崗位群)為背景的高等職業教育,更有充足理由授予專業學位。國務院學位辦副主任謝桂華同志說,我國的專業學位在一些發達國家稱之為“職業學位”,它是作為從事某種職業的必備條件。高等職業院校不能授予“職業學位”,從本質上自我否定了“職業”屬性,高等職業教育授予“職業學位(專業學位)”勢在必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制訂的ISCED1997版將“第三級教育第一階段”(ISCED5),即高等教育的專、本、碩階段分為A、B兩類,ISCED5A為“面向理論基礎/研究準備/進入需要高精技術專業的課程”:ISCED5B為“實際的/技術的/職業的特殊專業課程”,ISCED5B的課程計劃實際上是“定向于某個特定職業的課程計劃”,ISCED5B“主要設計成獲得某一特定職業或職業群所需的實際技術和專門技能——對學習完全合格者通常授予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有關資格證書”。ISCED5B同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從培養目標、從課程設置等內容上完全相同,因此,ISCED5B也可稱之為高等教育層次的職業或技術教育類型。ISCED5B可授予我們通常所說的職業資格證書或職業學位。不僅有學士職業學位,還有碩士職業學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既然與ISCED5B從教育層次、教育類型上講并沒有什么區別,而且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與其他全日制高等教育一樣,均以完全高中文化程度為人學條件,為什么不能按國際慣例對“學習完全合格者”授予“職業學位”或“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有關資格證書”呢?使高等職業教育成為名正言順的高等教育層次的職業教育類型呢?
三、高等職業教育回歸“大眾(普及)”的屬性
溫家寶同志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合理調整教育結構,重點加強職業教育。”“無論是中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要擴大職業教育的規模”。為什么要擴大職業教育的規模,為什么要在高等教育中擴大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呢?職業教育是“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的教育,職業教育應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夠找到適合于自己學習和發展的空間,從而使教育事業關注人人成為可能。”職業教育具有民生性,具有全民性,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的教育,具有大眾性、普及性的屬性。
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其數量之龐大可想而知,而我國目前在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素質偏低和技能型人才緊缺問題十分突出。現有技術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而且多數是初級工,技師和高級技師僅占4%。如果將技師和高級技師所占比重提高10倍,使其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意味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規模要成倍地擴大。否則,難以滿足生產第一線對高技能人才的需要。
社會人才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類,但各類社會人才在數量結構上有一個合理的比例,若比例失調,不僅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會造成人才結構供需失衡,使一些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失業,使一些企業招不到需要的大學畢業生缺乏人才氣使兩種矛盾的現象并存。經濟和社會發展既需要科學家。又需要工程師和經營管理人才,還需要高技能人才,他們之間的數量關系大體以10倍級累進,如數十萬的科學家,數百萬的工程師和經營管理人才,數千萬的高技能人才。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億計高素質勞動者培養的重擔落在中等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肩上,數以千萬計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必須山高等職業教育完成,無論是中等職業教育還是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都遠遠不能滿足如此巨大的人才需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刻不容緩。
社會人才的來源主要有兩條渠道:一條是國內自己培養(包括自學成才),另一條是從海外引進。通常情況下,科學家、工程師和經營管理人才可以雙管齊下,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其科學家、工程師和經營管理人才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國外。然而,高技能人才一般靠本國培養,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制造業大國,高技能人才只能寄希望于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寄希望于高等職業教育的大發展。
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在1906所普通高校中。高職院校1168所,占61.28%。從院校數量而言,高職院校數遠遠超過本科院校數。遺憾的是,高職院校的在校生無論是總體規模還是校均規模都不理想,占普通高校六成以上的高職院校,其在校生只占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的45.7%。顯然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結構不協調。與經濟和社會發展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倒掛。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的重點是發展高等職業教育,擴大高等職業教育的規模。一是提高高等職業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規模。高職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規模不到4000人,只有3909人,不及包括高職院校在內的普通高校平均在校生規模的一半,2006年普通高校在校生平均規模8148人,2007年為8571人。“萬人高職院校”僅4所,而非高職院校平均在校生規模已逾1.1萬人,可謂沒有萬名在校生不是“本”,有些名牌高校的規模達7、8萬人,直逼10萬人的“航母高校”規模,高校的擴招主要是本科院校、特別是名牌高校的擴招。高校在校生規模可謂本末倒置。研究型大學在校生規模不宜大,以“精英”為對象。高職院校在校生規模理應大,以“大眾”為起點,調整普通高校在校生的結構,使高職院校在校生從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總數的45.7%,提高到65%以上,達到近期在校生總數1000萬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高職院校在校生總規模應逾千萬人,否則,難以培養出“數以千萬計的高技能人才”。調整高等教育內部結構,使研究型大學、工程型和教學型院校、高職院校之間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假設在規模相同的情況下,有人認為他們之間的比例以1:20:40為好,按此推算,目前應將近100所本科院校轉為本科高職院校,以培養高技能人才為目標。客觀上講,許多本科院校的畢業生不僅從事高技能的工作,而且不乏經過職業院校“回爐”后再去從事高技能工作的畢業生,與其這樣走彎路,不如扎扎實實地定位于本、碩高職教育,既可以使高等教育內部結構合理,又可以使高等職業教育專、本、碩的層次鮮明。
總之,高等職業教育“回歸”其高等性、職業性、大眾(普及)性的關鍵不在基礎操作層面,各高職院校都有展現其高等性、職業性、大眾(普及)性的內在動力,因此,必須從制度層面、決策層面解決問題,唯此,高等職業教育才有大發展,才能培養數以千萬計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責任編輯肖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