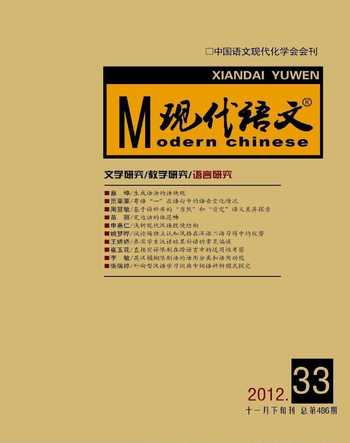論陜西方言走向電視的文化依據
摘 要:方言是特定文化的載體。陜西方言成功地走上熒屏有著深厚的文化依據:厚重的歷史積淀與濃郁的黃土特色、三秦兒女的鄉音情結與文化認同、平實化的電視審美回歸與當代大眾心理以及豐富多彩的民俗與多元視聽,共同促成陜西方言電視節目的穩固地位。陜西方言電視節目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陜西方言 電視 文化認同 審美回歸 多元視聽
馬歇爾·麥克盧漢(2000:382)指出:“在英國,電視來臨之后,最非同尋常的發展動態之一,是地區方言的復興。”
近幾年,我國許多傳媒機構紛紛辦起了形形色色的方言類欄目。作為現代文明的標志和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媒介——電視,更是成為這一趨勢愈演愈烈的主陣地。就陜西而言,有郭達、石國慶(王木犢)的小品,有方言譯制片《貓和老鼠》;有以方言播報天氣的《百姓報天氣》,還有方言劇《百家碎戲》等全部起用地地道道的普通百姓去演繹自己身邊的生活、道鄰里之間的家長里短,進而延伸出方言綜藝類節目,如《碎戲明星班》等。影視劇創作中也越來越多地加入了陜西方言的成分,如《美麗的大腳》《武林外傳》《高興》《走著瞧》等。今年吵得沸沸揚揚的《白鹿原》無疑將陜西方言又推向了一個高度。總之,陜西方言正以越來越活躍的姿態出現在熒屏上。
在大力推廣普通話的今天,方言逐步滲透并能在大眾傳媒中形成一定的影響,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并對其發展做出展望。本文將分析陜西方言走俏于媒體的深層文化因素。
一、語言與文化水乳交融
“文化”一詞內涵豐富、博大精深。自英國泰勒第一個為“文化”做出界定后,后人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研究各抒己見,但殊途同歸:文化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性成果。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現代漢語詞典》2005版,1204頁)。語言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是一種寄寓著深厚情感的文化載體,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播在當代有著突出的地位。申小龍(1988:5)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樣式,是對一個民族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系統和意義系統,人文性是語言的本質屬性。”如果說普通話反映的是當代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文化現象,那么方言則是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的社會文化知識體系。只要有文化交流與傳播,就有語言的相互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學是文化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陜西方言中的特色文化
(一)厚重的歷史積淀與濃郁的黃土情結
陜西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炎帝和黃帝的誕生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和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中國歷史上多個朝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現代中國革命的圣地,為炎黃子孫的生存、繁衍和人類歷史文明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歷史在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跡,陜西方言是古漢語的活化石,陜西人將“豬”念作“zhi”(之),實際就是古漢字“彘”;此外陜西話也成為方言當中與普通話最為接近的一種。在秦、漢、唐等朝代,陜西方言也是官方的普通話,直至今天,當地人仍在津津樂道詩人李白、杜甫和楊貴妃說的都是陜西話。
陜西地處中國西北地區,由北向南形成了以關中平原為主的三個特色自然區,共同構成了陜西文化的多元色調和博大品格。“八百里秦川塵土飛揚”道出了這里厚重的黃土地氣息、古樸的人文風韻和粗獷的關中風情,我們稱它為特色的“黃土文化”。胡適曾在《〈海上花列傳〉序》(1930)中說:“方言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于古文,但終不如方言能表現說話人的神情口氣。”外人眼中的陜西話總是那么言簡意賅、一針見血,憨厚中帶些硬漢勁。一句“嫽咋咧”就包含了“極好、很帶勁、很舒服”等語義。陜派電視劇《關中匪事》在展現關中風情的同時,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式的秦腔秦韻風行大江南北。陜西方言本土歌舞片《高興》中,當五富用陜西方言說,他最享受的就是能掙到錢拿回家扔給老婆說:“他媽的,狗日的,給,用去!”,雖然是罵人的話,但黃土味十足。
(二)三秦兒女的鄉音情結與文化認同
許多在外打拼多年的陜西人到頭來都會發出這樣一句感慨:還是咱老陜話最親切、最舒服!簡單的一句話道出了三秦大地兒女的戀鄉情結。“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讓我們感到了鄉音的力量,這種心態是廣義文化的核心。
文化認同指個體對于所屬文化以及文化群體形成歸屬感及內心的承諾,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屬性的社會心理過程。地方電視臺的受眾范圍主要是當地觀眾,這個地域內的觀眾對本地域的文化有著一種潛在的特殊心理,而方言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的載體,從某種意義上說為當地人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歸屬感和安全感,特別能夠引發文化和情感的微妙共振,是當地觀眾認可的一種文化形式。同時,方言通過言說的方式傳遞著自身的文化潛質,影響著這個地域內的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人們對方言電視節目就具有一種方言認同感。這與傳播學中的“使用與滿足”理論(從受眾如何使用大眾媒介以及大眾媒介如何滿足受眾需求兩個角度研究媒介與受眾的關系)是相契合的。文化認同感讓觀眾喜歡這種方言節目,從而為方言節目獲得了一定的市場生存空間。
陜西電視臺《百家碎戲》欄目是以陜西方言為基本形態、以藝術再現的手法反映市民關注的各類社會及市井話題,追求真實,反映“秦人、秦地、秦風、秦韻”為內容的一個“全新演繹生活萬象、本色表達平民情懷”的欄目劇,表現了發生在當代都市和農村普通人生活中的真善美。深諳陜西文化的受眾在劇情與語言的解讀中,能夠感受到其中的文化韻味和審美體驗,由此產生對家鄉、對本土文化的認同與自豪。
(三)平實化的電視審美回歸與當代大眾心理
電視的發展歷程,從最初的文化認知、教育功能,轉向尋求感官刺激、娛樂、游戲功能,如今又逐漸呈現出返璞歸真的傾向。
電視真實是實現電視審美的前提。電視真實地使時空無限地延續保留下來,提供了人們回味、研究、比較的可能。隨著當代人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們的是非判斷能力增強,過于虛假、浮夸的東西只能增加觀眾他們對節目的厭惡感。真人秀、方言短劇、紀實類作品卻能滿足他們的觀賞需要。如《非誠勿擾》《人間》收視率飄紅就是有力的證明。《百家碎戲》通常是由市民自導、自拍的,劇中簡單明了的故事仿佛是觀眾剛剛親身經歷的。在普通話全面推廣的今天,方言節目給了受眾一種回歸自我的新鮮感。
(四)豐富多彩的民俗與多元視聽
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時代和地域中不斷形成、擴大和演變,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服務。它是一種來自于人民,傳承于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為、語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歷史悠久的陜西是一個民俗文化大省。“陜西八大怪”是最有影響力的陜西民俗的代表,“板凳不坐蹲起來,房子半邊蓋,姑娘不對外,手帕頭上戴,面條像腰帶,鍋盔像鍋蓋,油潑辣子是道菜,碗盆分不開”生動詼諧地述說了陜西人特有的生活風貌,展示了陜西方言多元化視聽的特色。當操著一口純正方言的老漢端著一碗熱氣騰騰、鮮紅勁辣的干面圪蹴(蹲)在自家門口一邊咥(吃)、一邊啐嘴的時候,怎么看都覺得地道和過癮。
“八百里秦川黃土飛揚,三千萬老陜高吼秦腔。”語言是音樂的變形,言為心聲,樂亦為心聲。“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礎,比如中國數百種地方戲曲和說唱藝術形式都是以當地方言為依托的”(張阿利,2008)。以關中話為基礎方言的秦腔作為經典劇種之一,以其高亢激越的聲音、悠揚的曲調深受西北地區廣大群眾的喜愛,陜西電視臺的《秦之聲》就是當地頗具影響力的電視節目。
另外,“馬勺社火”“華縣皮影”“鳳翔剪紙泥塑”等等都紛紛登上了熒屏。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使陜西方言電視節目在大浪淘沙中得以站穩腳跟。
三、結語
斯科佩克認為:“一種文化存在的最明顯的標志是獨特的或具有特異性的言語形式的使用,尤其在以區域性某種社會階層為題材反映地域文化的電視(影)劇中,采用當地群眾普遍適應的方言方音,似乎也是電視劇發展的必然要求。”(丹尼斯·K·姆貝,2000:22)
陜西方言以其厚重的歷史積淀與濃郁的黃土特色、三秦兒女的鄉音情結與文化認同、平實化的電視審美回歸與當代大眾心理以及豐富多彩的民俗與多元視聽,構成了陜西文化舉足輕重的一部分,形成了陜西方言走向電視的多重文化依據。
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和豐富多彩,是中華文明的本質特點。這決定了中國各地少數民族語言及其方言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語言的多樣化。方言以其獨特的魅力登上熒屏是對地區傳統歷史文化的再現,是對自我之“根”的追念,是自我價值的滿足,也是現代媒體不斷調整自身表現手段的重要因素,符合當代大眾的審美趨向,更是實現祖國多元文化的途徑。
(本文系寶雞文理學院關隴方言基地重點科研課題,項目號為BY03;寶雞文理學院院級重點科研項目,項目號為zk0861。)
參考文獻:
[1]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
[2]現代漢語詞典[Z].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3]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論綱[J].北方論叢,1988,(5).
[4]張阿利.陜派電視劇地域文化論[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2008.
[5]丹妮斯·k·姆貝.組織中的傳播和權力:話語、意識形態和政治
[M].陳德民,曹慶,薛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何艷萍陜西寶雞寶雞文理學院中文系 7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