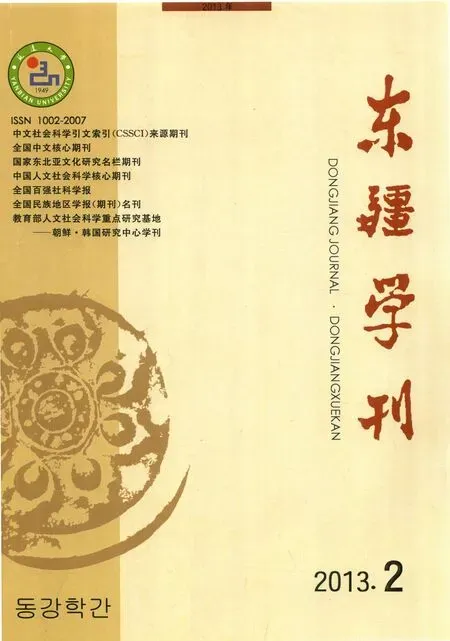莊子與盧梭的自然觀比較及其文化意義
董 曄
莊子和盧梭是東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啟后的大家。雖然時代、地域不同,但二人在哲學、美學思想方面,尤其是在自然觀方面很相似。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他們追求二者的和諧統一;在社會理想方面,他們追求自由、平等;在審美態度方面,他們追求本真、拒絕人為。當然,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二人的自然觀在哲學基礎、社會理想和審美態度等方面也存在著根本不同。這些異同點為二人及其思想的比較研究提供了闡釋的有效空間。
一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基本哲學問題上,莊子和盧梭均主張二者和諧相處,而反對將其對立起來。原始的自然崇拜、天人感應思想,在老莊的道家學說那里被提升為整體的哲學認識。在莊子看來,“天”與“人”是統一的整體,相互依存,相互包容。“人”與“天”都統屬于宇宙之“大全”,“人”如果從“天”中分離出來,“天”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存在,宇宙也就不具有整一性。所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①本文所引《莊子》原文均出自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只標篇名。(《齊物論》),就是說天地雖大,乃與“我”共同存在;萬物繁多,卻與“我”并無差別。莊子站在物性平等的立場上,主張天地萬物的同生同體,所謂“天與人不相勝也”(《大宗師》)。可見,莊子主張人與自然應該是一種相互包容、相互推動、相互依存的關系。
相比之下,“歐洲人從來不委身于自然”[1](118)。從古希臘直到近代,西方文化中一直在演繹著人與自然的對立和斗爭。特別是近代以來流行的功利主義、倫理主義,更是片面強調人的價值,信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甚至弱肉強食的法則。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觀念導致自然被過度開發索取,人與自然的關系十分緊張。直到 18世紀,盧梭呼吁“回歸自然”,才啟發西方人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盧梭說:“在宇宙中,每一個存在都可以在某一方面被看作是所有一切其他存在的共同中心,它們排列在它的周圍,以便彼此互為目的和手段。”[2](394)他認為物質世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實體之間是美妙和諧的關系;事物發展是無數生生不息的因果鏈條,在特定的因果聯系中,每個事物又互為目的和手段,緊密聯系與配合。正是在這種整體論自然觀的基礎上,盧梭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應當是平等和諧的,其“回歸自然”的口號便有了東方哲學的思維特點。
當然,盡管莊子與盧梭的宇宙自然觀都強調人與自然的緊密聯系而反對將二者割裂開來,但由于東西方哲學思維模式不同,又使他們對人與自然做出了相異的價值選擇。總的來說,中國古代哲學偏向于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模式,一向認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與自然合而為一、和諧相處是一種必然的選擇。在認識論方面,中國古人也不主張對物質和精神進行二元劃分,而強調認識主客體間的依存與包容,表現為一種不可做物我分離的一元論。比如,“心齋”、“坐忘”作為莊子哲學中最重要的體道方式,就避開了心物之爭,要求盡可能地淡化主體意識,從以“我”為中心的狀態里解脫出來,在與萬物的交融共存中體悟生命的真諦,因而具有典型的一元論特征。
與東方哲學不同,西方哲學長期以來專注于認識與找尋“自我”,導致西方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由原始混沌狀態逐漸向物我分離狀態演化,最終將“自我”從外在事物中分離了出來。“心與物之間的區別——這在哲學上、科學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經成為常識了”[3](179)。尤其是近代的笛卡爾把世界區分為心與物兩種實體,更是對機械論自然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哲學傳統成為盧梭全部思想的一個當然前提。盡管他極力回避并消除機械論自然觀的影響,但不僅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西方哲學的傳統思維模式,還繼而在這種模式下建立了自己的學說和理論范疇。
所以,莊子與盧梭在對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理解上存在先天的差異:前者在物我不分的思想前提下領悟自然的存在,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強調“天”對“人”的包容;而后者則在主客二分的理論前提下觀照人與自然的關系,將人和自然視作兩個獨立存在的實體,強調它們之間的平等。從根本上說,這是東西方哲學傳統思維模式的差異,亦即一元論與二元論的差異。需要說明的是,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難免不造成價值判斷上的非此即彼,而且很容易導致對問題的實質作形而上學的分析。所以,盡管盧梭竭力通過自然教育、社會契約等方式來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但卻一直周旋于自身學說的二律背反之中。實際上,他只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轉化為人性演進中的感性與理性、社會契約中的個體自由與社會必然、文明發展中的自然與文化沖突等問題,而并沒有在根本上脫離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束縛。
二
探索人性的自然、本真,是莊子與盧梭自然觀念的又一個共同特征。在他們那里,“自然”一詞均具有人性的本然、天然、自然而然等含義,所以,這一范疇不僅與宇宙認識觀相連,而且還有著倫理的、審美的內涵。生活于當時社會歷史轉型期的莊子與盧梭,認為文明發展戕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因而對歷史的前進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在他們看來,文明發展不僅使人性失去了原初的真實,還導致了各種社會罪惡,因而主張自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遂以“自然”作為標準來衡量現存的倫理秩序。實際上,莊子與盧梭正是基于對一種完全未經文明浸染的人性“自然狀態”的預設和追溯,批判了伴隨社會文明進步而來的人類生存境遇的異化狀態。當然,由于他們身處不同的文化語境和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所以其批判的對象不盡相同。這意味著面臨社會文明進步所帶來的人類生存困境問題,莊子與盧梭必然選擇不同的解決路徑。
先秦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反對人為。所謂“人為”,即用外力強行干預事物的發展變化。在莊子的學說中,這類非自然、反自然的“人為”活動,既包括“落馬首,穿牛鼻”(《秋水》)等野蠻行為 ,也包括“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天地》)等技術行為,還包括儒家的“殺身成仁”、墨家的求道于“義”等忽視個體生命自然存在狀態的禮樂仁義與賞罰刑法等。具體地說,莊子一方面抨擊了仁義禮樂制度對人之自然本性的背離,認為這些制度毀棄了自然人性,倡導仁義禮樂將最終導致天下分崩離析,所謂的“……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在宥》)。在莊子看來,自黃帝倡導仁義始,人之自然本性就已散亂;隨著儒、墨成為顯學,人們越發追求巧智,各種刑具和懲罰制度亦逐漸興起,所以猜疑、欺詐、責難、譏刺等淆亂人心,天下漸趨衰敗。另一方面,莊子還揭示了禮義仁德的虛偽,所謂“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知北游》)。認為儒墨兩家倡導的禮義仁德是在失卻“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們不但遮蔽了人性的自然本真,還內化于世俗人的各種形式化、工具化行為,成為“道”的偽飾與亂之禍首。他提出“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漁父》),并且認為真正治天下的理想境界是順應人性自然,實現人與萬物同生同存的“至德之世”,所謂“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馬蹄》)
如果說莊子面臨的是中國農業文明早期人為的“鑿木為機”的狀況,那么,擺在盧梭面前的則是像“礦坑、礦井、熔爐、鍛爐、鐵砧、鐵錘、彌漫的煤煙和熊熊的爐火”[4](92)等西方工業文明初期的機械化作業。盧梭極力反對人類的“胡作非為”,即理性之誤用,認為科學理性、工具理性不但破壞了人們的自然生活圖景,還造成了自然人性的扭曲和生存環境的惡劣。不僅如此,他還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伴隨科技發展而生的私有制社會,認為其所孕育的專制政體戕害了個體的自由和平等。在盧梭看來,處于人類社會“黃金時代”的人們依照本性生活,人與人之間既沒有相互的奴役和剝削,也不存在道德意義上的不平等,彼時的人性呈現出原初的自由和本真。然而,“那些在自然狀態下幾乎不存在的不平等,隨著人的能力的開發和思想的進步而擴大、加深,隨著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而穩定下來,變得合法”[5](138~139)。在私有制出現后,人類的天賦自由消失了,人與人之間逐漸淪為統治與服從、主人與奴隸的關系,過去處于自然狀態的自由的人現在成了受人支配的奴隸或支配他人的主人。為了改變這種異化狀況,盧梭指出,以往的社會公約只是為一個人的專制制度服務,無法保障人與人之間基本的平等,而療治時弊的唯一辦法就是平等地簽訂社會契約,轉讓個人所有的權力甚至財產,使“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6](24),由此產生一個公意指導下的政治國家。
因此,盡管莊子“所采取的方式非常完整地預示了盧梭后來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及《論科學和藝術》中所采用的方式”[7](237),但二者卻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如果說莊子的社會理想是萬物各適其性的“至德之世”,即人與禽獸同樂、與草木同生的原始社會狀態,而這種狀態實際上不可能存在;那么至少從表面上看,盧梭也同樣追懷純樸的太古時期,只不過他的“回歸自然”并非真要人們退回到身穿獸皮、手拿石斧的蠻荒時代,也并非主張“毀滅社會”、“返回大森林和熊一起生活”[5](155)。在此問題上,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給予了公正的評價:“盧梭關于自然狀態的描述并不是想要作為一個關于過去的歷史記事,它乃是一個用來為人類描畫新的未來,并使之產生的符號建筑物。在文明史上總是由烏托邦來完成這種任務的。”[8](78)所以我們認為,盧梭批判人類社會的歷史,但并不否定歷史的發展;他反思理性的誤用,但并不否定理性的作用。盧梭思想的關鍵點不是破壞而是重建,這突出表現在他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設計中,即通過契約轉讓重塑社會歷史秩序,讓每個人在契約社會中重獲自由與平等。
三
由上可知,莊子與盧梭分別從不同的路徑找尋自由和平等,即前者是“順應自然”,而后者是“回歸自然”。如果說莊子向往的是“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 ,命曰天放” (《馬蹄》)的無為境界,是一種取消個體自我意識的消極存在,那么,盧梭追求的則是致力于建立符合自然本性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有為狀態,是一種凸顯主體自我意識的積極存在;如果說莊子把個體養生當作最重要的生活目標,而將國家帝王之事視為“緒余”、“土苴”,難免有否定人類文明的虛無主義嫌疑,那么,盧梭則強調主體創造歷史的能動性,試圖通過改變社會制度來盡可能地還原理想的自然生活,從而具有重塑人類文明的理想主義色彩。進一步說,如果說莊子“順應自然”的虛無主義對于實在的個體生命而言是最真實的,所以可被視作一種有意義的虛無,那么,盧梭“回歸自然”的理想主義對于現實的社會制度而言卻是最浪漫的,以至被看作一種消極浪漫主義。當然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說,無論“順應自然”還是“回歸自然”,都是不切實際、不可能真正實現的,但也許正因為如此,二者那里的“自然”反而具有更重要的文化意義與審美意義。
在莊子和盧梭那里,“自然”都具有一種返樸歸真、淡泊寧靜的意味,所以他們同樣將本真、素樸作為藝術審美的最高原則。如莊子強調“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刻意》)、“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天道》),倡導“無以人滅天”(《秋水》);而盧梭也認為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真正的美,是美在它本身能顯出奕奕的神采”[2](551)。相應的,他們也不約而同地貶抑人為造作的藝術美,如莊子指出“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扌麗工亻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月去篋》);盧梭則借以道德純樸著稱的法布里修斯之口呼吁:“趕快拆毀這些露天劇場,打碎這些大理石像,燒掉這些繪畫,趕走這些征服了你們并以他們那些害人的藝術腐化了你們的奴隸吧。”[9](36)在此,我們不能因為莊子和盧梭學說中的反文化傾向而簡單地加以否定,而應從他們批判的精神實質以及所構建的藝術理想中發掘某些新的文化與美學的內涵。
首先,就批判的精神實質而言,二者文藝批判的主要針對點仍是工具理性之運作。在莊子看來,巧智的行為只會淆亂人心、自絕于“道”;盧梭也認為,工具理性的濫用將導致人性的異化和生存環境的惡化。當然,由于他們身處不同的歷史語境,所以批判的具體所指亦不相同。莊子主要針對的是儒家的禮樂文化,認為“五色”、“五聲”、“五臭”、“五味”、“五趣”皆是“禮”的化身 ,它們皆使人“失性”,“皆生之害也”(《天地》)。由于人為法則只會讓文藝離“道”越來越遠,所以他提出“自適其適”與“滅文章,散五采”等。盧梭更多地站在民主、大眾的立場上,批判路易十五時代遍布法國的矯揉造作、賣弄式的貴族藝術。由于此類藝術滿足的是貴族階級的審美趣味和精神需求,所以在藝術內容方面主要表現上流社會及宮廷生活,而平民百姓則往往被排斥在外,“這種收費的現代的戲劇演出到處都助長財產不平等的增長”[10](116)。所以在盧梭看來,“藝術”是不平等的象征。
其次,雖然二者均以“自然”作為標準批判當時的藝術和審美觀念,然而他們在構建新的文藝理想時,又表現出極大的差異。莊子的藝術理想可謂“技進于道”,即像庖丁解牛那樣地“游刃有余”。最好的藝術不只是技術,更應以技彰道、順應自然,通過技藝的解放帶給人更多的自由感。這必然要求藝術主體“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庚桑楚》)。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無疑通向的是與道合一的“逍遙游”境界,即在簡單、質樸、自然中體驗生命的自由與解放。因此,有學者指出:“莊子所追求的道,與一個藝術家所呈現出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11](44)反觀盧梭,他一方面把情感視作文學藝術的本質,從而抓住了文藝區別于科學、哲學的獨特之處;另一方面又認為文藝除了自身形式上的純粹審美意義之外,還應具有作為升華人性、教化風俗的道德載體的價值。換句話說,盧梭始終站在一個道德家的立場上,把是否有助于促進人的幸福、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以及培養純樸的民風與自然的人性作為評價藝術價值的重要標準。所以他不會幻想通過藝術審美解決人性和社會問題,而是寄希望于通過政治、社會制度的變革解決藝術審美問題。總的來說,莊子與盧梭在審美態度上的不同表現為:前者是以“道”觀物,后者則是以“善”觀物;前者追求有大美而不言的天道與無為精神,后者追求個體情感的真實流露與主體精神;前者向往“乘物游心”的人生境界,更加接近純粹的文學藝術審美,后者主張美與善的結合,具有更強的社會功利目的。
綜上所述,莊子的自然觀念更多地指向一種道德虛無主義——當然,這里的“道德”與其說是倫理,毋寧說是人為,他的“自然”所包含和意味的種種非人為、反人為傾向,并未妨礙其關注個體的存在意義與生命價值,從這一意義上說,莊子的虛無主義自然觀指向一種有意義的虛無,可能暗示著某些極為深刻的人生價值規律;而盧梭的自然觀念更多地指向一種道德理想主義——只不過他的“自然”包含、意味著太過理想的道德設想和太過直接的功利目的,所以他實際上走向了文化浪漫主義,雖然于社會現實是最理想化、最不切實際的,但其在藝術審美領域中卻有著最積極、最發人深省的意義。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到:“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著文明產生的社會為自己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12](179)這就是人類社會歷史前進過程中文明與異化的二律背反。雖然文明進步對于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但它在給人類生活帶來巨大福祉的同時,也導致了如道德敗壞、人為物役、精神焦慮、生態危機等威脅人類自身生存的諸多問題。有學者指出:“盧梭提出的問題,是 18世紀思想生活的中心問題,也是19世紀哲學探索由此出發的理論前提。”[13](146)從文化價值層面上說,莊子的“順應自然”與盧梭的“回歸自然”在本質上都是尋求一種回歸,即共同呼喚人性與社會的返璞歸真,均將目光投向人類的前社會階段,希望恢復人與自然的和諧,并以此克服理性文明帶給人類社會的種種弊端。盡管他們身處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語境,對于如何實現目標的認識和手段亦有差異,卻都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價值秩序與理想追求,足以作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仍在檢討文明與異化問題,思考如何處理文明與自然的關系。可以肯定的是,人從自然中確立,既與自然對立,又與自然無限親近,這說明“作為自然的參與者,我們引起它的平衡和不平衡,我們是自然建筑的調節者和建設者”[14](286)。
[1][法 ]克洛德· 德爾馬:《歐洲文明》,鄭鹿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法 ]盧梭:《愛 彌兒》 (下卷 ),李 平漚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
[3][英 ]羅素:《西方哲學史》 (上卷 ),何兆武、李 約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
[4][法 ]盧梭:《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5][法 ]讓-雅克·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高煜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6][法 ]盧梭:《社會契約論》 ,何兆武譯 ,北京:商 務印書館,1980年。
[7][美 ]歐文· 白璧德:《盧梭與浪漫主義》,孫宜學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德 ]恩斯特· 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
[9][法 ]讓-雅克· 盧梭:《論科學與藝術》,何兆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法 ]盧梭:《盧梭論戲劇》(外一種 ),王子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11]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3]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14][法 ]塞爾日·莫斯科維奇:《反自然的社會》,黃玉蘭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