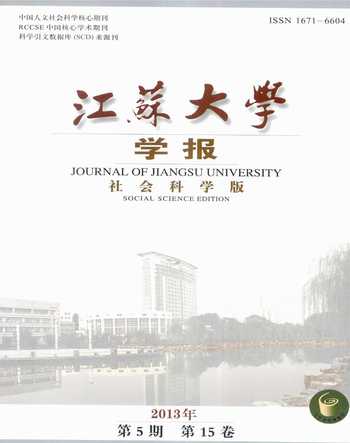分隔漸隱
史蒂芬·呂斯特 薩爾瑪·莫娜尼 侯嬌嬰
摘要:生態電影研究不僅簡單局限于直接傳遞環境意識信息的電影,而且也考量電影的維度。《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關注各種生態電影理論和不同體裁,并結合生態電影研究的歷史發展實踐,啟發我們應當將視線轉向該領域內理論創新動力的需求,同時模糊體裁關注中的歷史劃界。
關鍵詞:生態電影;生態批評;環境保護關注;自然;實踐
中圖分類號:1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13)05-0042-08
從生態批評的角度來說,環境不只是有機世界,或者是被康德施以人類理性的力量在自由的斗爭中所對抗的自然法則,抑或是馬克思認為我們為了生存而注定要去與之搏斗的大自然;環境其實就是圍繞著我們的整個棲息地,是物理世界與文化世界的交融。它是各種關系的生態,我們在其中談判妥協以獲取意義,實現生存。在這個棲息地中,電影也是一種協商,一種調節,是一種自我生態的存在,因為它吞噬著周遭這個交融的世界,因而,也在自我消耗。
盡管電影和媒介學者始終致力于研究電影的文化調節作用,但直至近期,生態批評的視角都還在學界基本處于缺失狀態。多少被大家忽視的一個方面是,從制作到發行到消費到循環流通,一部影片的歷程是不可避免地深深交織在生態網絡之中的。電影文本加之音頻一視頻手段所體現的個體及其生活場所,影響著我們對周圍世界的想象,從而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們對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除此之外,各種電影技術,從燈光到相機到碟片甚至到看似無形的因特網,都涉及地球上的物質資源,因而也宣告電影在轉變并影響我們生態系統過程中的直接作用。只是近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才逐漸有部分學者開始批判性地審視電影的生態維度,以及它們對人類和比人類所居住的世界更廣闊空間的影響。
《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便是有關此類生態批評審視的,匯集了該領域內領軍人物的觀點和思想,如肖恩·庫比特,大衛·英格拉姆和斯考特·麥克唐納;更收納了時下的聲音,如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和妮可·斯塔羅謝爾斯基等人,他們的文章體現著鼓舞人心的嶄新的學術研究方向。該書萌芽于學術會議中的對話,在網上的密切交流和“生態媒介研究”等網站的博客中得以孕育,因此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為了充分發揮這些對話的作用,《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一書致力于為日趨豐富的這一批評領域——生態電影研究——穿針引線。
一、對生態電影研究的定義和定位
《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在遴選文章時,要求投稿人思考當前電影研究和生態批評所關注的問題,并針對其中一個或多個問題撰文,這樣就可以從整體上呈現生態電影批評所涵蓋的大量電影和理論方法。結果證明,有的文章涉及我們通常認為屬于環境的話題和體裁,例如關于企鵝的野生動物紀錄片,但有的則屬于我們最初不會歸為環境范疇的問題,例如20世紀70年代的恐怖電影。總體來看,這些視角各異的文章限定了《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的目標,那就是要清楚表明生態電影研究不僅簡單局限于那些直接傳遞環境意識信息的電影,而且也考量電影的維度,從好萊塢的公司制作到獨立先鋒電影直至制片人、消費者和文本進行互動的擴張中的傳媒網站。
很多學者(和其他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人)或許對于生態電影究竟是什么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有些批評家,如寶拉·薇洛奎特一馬里康迪在《構建世界:生態批評和電影探討》一文中建議,某些獨立抒情和激進的紀錄片——而非商業(即好萊塢)電影——可以被視為生態電影,因為它們最能激發激進的生態政治探討和觀眾的行動。雖然有人指出,對于個體是如何被激發的,什么樣的電影可能激發他們,以及由此帶來的到底什么是生態電影的問題還存有更大爭議,但生態電影批評家們在幾個關鍵概念上普遍持一致觀點。首先,我們認同所有影片都毫無疑問有其文化和實質寓意。其次,無論我們個人的政治立場如何,我們都傾向于認為,主流的、消費主義的處事方法通常體現著不僅是在人類交往中而且在非人類世界里事務的紛繁狀態,電影提供的一扇窗則可以窺視我們對這種紛繁狀態的設想,以及我們順應或抵制這種狀態的方式。再次,正如肖恩·庫比特雄辯的論斷所言,“盡管可以斷定許多電影有關當下普遍的意識形態,包括自然的思想意識,但還有很多其實更富含矛盾對立,在倫理、情感和智力方面比大多被誤認為是生態政治的影片更令人滿意”。從本質上來說,我們有意贊同所有影片都呈現有效的生態批評探索,因此,細致的分析可以揭示看待電影與我們周圍世界的各種關系的有趣視角。《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所展示的當前生態電影研究的維度即印證了對所有電影所持的這種關注。
為了給如此寬泛的學術研究以秩序,《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以期同時反映并模糊迄今該領域中存在的界限。第一章“生態電影理論”,指出了困擾該領域的某些理論困境并提出了對生態和電影現實本質的嶄新見解,為全書設置了理論背景。第二章“生態電影實踐:野生生物和記錄影片”,聚焦大量生態電影論題,盡管這可能會與人們所劃定的野生生物影片或紀錄片界線有所沖突。在紀錄片常常因其蘊含的環境意識而備受稱贊的同時,第三章“生態電影實踐:好萊塢和虛構敘事電影”,將視線轉向主流影片,一方面對基于此類電影的大眾噱頭和商業意圖而推斷其無力推廣生態意識的假定提出了質疑,一方面突出了曾經被生態電影批評家忽視的門類和體裁。第四章“超越電影”,通過對環境電影節的考察提出了擴展該領域的范本,也更近距離審視了被科學家和電影工作者用以記錄、闡釋并呈現科學數據的形象化、聲像化手段的技術和審美屬性。
《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四個章節的構架,及對生態電影理論和不同體裁的關注,強調實踐,并體現生態電影研究的歷史發展。這也正是一本試圖側重該領域學科基礎的文集在認可其新興發展方向的同時不可忽視的。在學術研究歷史上,盡管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前就有零星文章出版(如堂娜·哈拉維1989年的著作《靈長目動物的視野: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中的某些章節,和芭芭拉·克勞瑟1994年的論文《走向對電視自然歷史節目的一種女性主義批評》),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生態電影批評蓬勃發展開始于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標志為五部長篇研究著作的發表,即詹·霍奇曼的《綠色文化研究:電影、小說和理論中的自然》(1998),格雷格·密特曼的《旋轉膠片中的自然:電影中的美國與野生動物浪漫史》(1999),德里克·博賽的《野生動物電影》(2000),大衛·英格拉姆的《綠色熒屏:環境保護主義與好萊塢電影》(2000),及斯考特·麥克唐納的《機械中的花園:獨立制作處所電影的田野指南》(2001)。
其中,密特曼和博賽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首個對野生生物自然電影的全面考察,英格拉姆的《綠色熒屏》是對好萊塢環保影片的首次全面探索,而麥克唐納將視線轉向先鋒電影。霍奇曼的《綠色文化研究》則是首批把文化研究的分析理論應用于電影的生態批評解讀的長篇著作之一。雖然發表時間相近,又出自擁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這五本書卻沒有直接相互參照。然而,因為每本書嘗試對一類影片進行探究——野生生物電影、好萊塢敘事電影或獨立制作先鋒電影——并且對很多影片采用了生態批評視角,對于有興趣研究電影如何塑造又如何與我們對物質環境的想象進行交互的學者來說,這些書可以作為及時有效的參考。同時,每一本書似乎也在清晰刻畫生態電影研究的分界線。例如,英格拉姆的《綠色熒屏》對好萊塢電影批評家們產生了深遠影響,催生出帕特·布里雷頓的《好萊塢烏托邦》(2005)和狄波拉·卡米歇爾選編的《好萊塢西部片之風景:美國電影門類中的生態批評》(2006)等書。博賽和密特曼的研究則成為像辛西婭·克里斯(《觀看野生生物》,2006)和路易·維萬科(如其2004年發表于《文化動力》的文章《電視影像探險時代的環保工程》)這樣的野生生物電影學者們的核心起點。
誠然,即便這五本書已經指向生態電影研究中的不同分支,有些學者進而開始嘗試積極打破由傳統的體裁關注所帶來的界定和假設。隨著這些電影種類所采用的制作、發行和接受方式之間的重疊和競爭不斷加深,它們所傳遞的環境保護信息(以及媒體對環保問題的廣泛關注)也逐漸增強,如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參見其2008年于《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中的文章《綠色電影批評及其前景》)和薇洛奎特-馬里康迪(《構建世界》)等學者以他們正在嶄露頭角的作品向我們證明,超越了好萊塢、野生動物和獨立先鋒電影界限的對話如何能夠豐富我們對所有影片都具有生態涵義的理解。與此同時,有關生態電影構成和生態電影批評家的職責、作用的更全面的思考對該學科領域自身和未來發展方向提出了重大問題。這也正是《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的意圖和價值所在,一方面將視線轉向該領域內理論創新動力的需求,一方面模糊了體裁關注中的歷史劃界,更為重要的是,在學科向前推進之際,引發讀者對伴隨生態電影研究各分支間此類分隔和消隱產生的分歧與潛能的思考。
二、生態電影的內涵及外延
《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以理論開篇,以便涵蓋生態電影批評家設定生態電影內涵時的視角和方式,以及學者如何可以拓展其外延。打頭陣的是斯考特·麥克唐納的《生態電影體驗》,也是他2004年《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期刊中《走向生態電影》一文的修訂擴充版。他在文章中首創了生態電影一詞,來描述那些提供“現代生活機器內的某種花園——一個逃離慣常消費主義的‘伊甸園似的臨時庇護所”的電影,“因為媒介組織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象征”。就像頌歌與激辯對人有所教益一樣,麥克唐納在此主張置身于長時間影片面前的觀眾同樣也會有所收獲,而類似安德雷·茲德拉維奇(Andrej·Zdravi)、詹姆斯·本寧(James Benning)及沙倫·洛克哈特(Sharon Lockhart)這樣的獨立電影制作者所使用的先鋒技術手段也可能發揮重塑感知的作用。在實際效果中,對先鋒電影的感受可以抵御商業媒體對精神和環境產生的破壞。
大衛·英格拉姆卻反對上述立場中的某些方面,在其《生態電影批評中的美學與倫理學》(The Aesthetics and Ethics of Eco—film Criticism)一文中反擊道,認知電影學理論為塑造近期生態電影研究成果的美學假定提供了有益的修正。為了強化他的例證,英格拉姆分析了三部審美風格截然不同的影片——《狂躁的夢》(吉德昂·科波爾,2008)(Gideon Koppel,Sleep Furiously),《陽光天堂》(約翰·塞萊斯,2002)(John Sayles,SunshineState)和《南方傳奇》(理查德,凱利,2008)(RichardKelly,Southland Tales)。每一部,他都認為既能夠激發觀眾去重塑他們的生態意識感知,又同時對此目標徹底無能為力,而這完全取決于觀眾先前的傾向和訓練。他把文章建構于使審美復雜化的三組對立概念之上以闡釋其觀點,謂之藝術與通俗電影,現實主義與情節劇,道德論與非道德論。
與英格拉姆一樣,安德魯·哈格曼也擔心在生態電影研究中采用教條的審美或道德方式無法成為批評家鑒別并分析所有電影內在沖突的有效工具。因此,他在《生態電影與意識形態:生態批評家夢想井井有條的綠色嗎?》(Ecocinema and Ideology:Do Ecocritics Dream of a Clockwork Green?)一文中,通過不同體裁但同樣描述玻利維亞科恰班巴城水資源私有化斗爭的影片——紀錄片《解構企業》(The Corporation)(2003),劇情片《雨水危機》(Tambien la Lluvia)(2010)和動畫短片《水的過去與未來》(Abuela Grillo)(2009),向我們表明所有影片中都存在意識形態的對立。他的論點即,恰是這些印證了我們以生態的方式進行思考和行動的能力有限的對立,警示我們在狹隘地定義生態電影時應該慎之又慎。
如果將生態電影理論化的嘗試大多都致力于甄別對電影的生態寓意的衡量,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對電影與世界關系的哲學領悟也應算是其中之一。在文章《流動影像的生態哲學:作為一部人類生物地理形態的裝置》(An Ecophilosophy of the Moving Image:Cinema as an Anthrobiogeo—morphic Machine)中,伊瓦克伊夫吸取阿甘本、皮爾士、懷特海、德勒茲、迦塔利和海德格爾思想之精髓,提出了電影的過程一關系理論。在這個模型中,電影成為一部推動我們沿著自然中情感的、敘事的且符號化的裝置,揭示著一個個人性、動物性和領地被置于其中并相互聯系的世界。通過描繪電影與地球世界中三個生態系統——物質、社會和感知系統——的復雜互動,伊瓦克伊夫呈現了與電影交互的一種不亞于整體論的方法。
以上理論探索并未在第二章“生態電影實踐:野生生物和記錄影片”中被遺忘,而是因路易·維萬科、詹妮弗·拉迪諾、妮可·斯塔羅謝爾斯基和克萊爾·莫莉的努力得以深化。他們參與到了當前對動物性與人性、野生與馴化以及我們與“他者”的電影表現的討論中來。盡管電影制作本質上講是人類活動,但正如文化、政治和經濟決定著我們把什么搬上熒幕,如何做到,又對這些影像作何反應,被很多電影試圖去展現的非人類世界其實也在發揮著決定作用。通過強調文化與物質之間的互動,并打亂那些意圖為先前有關所謂自然電影之探討而去定性的普遍假設,這幾篇文章提醒我們,人類與非人類世界之間的界線的確是流動的。
在《想起企鵝真好:野生動物電影、對自然的影像塑造,和環境政治》(Penguins are Good to Think With:Wildlife Films,the Imaginary Sha—ping of Nature,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一文中,維萬科稱,縱觀野生動物體裁電影的歷史就會發現,電影制作者和觀眾一直用企鵝來反映廣泛的政治問題,如艱苦環境中的生存、家庭關系、棲息地毀壞,以及近來的全球變暖。從它們本身來看,維萬科指出,想起的是企鵝,而不是野生動物電影中的其他主角并非更好或者更壞。然而,他卻由追尋銀幕中企鵝的足跡為未來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模型,去發現野生動物電影體裁的歷史演變如何展示更大范圍的文化關注。
詹妮弗·拉迪諾在《跟動物一起工作:關于紀錄片電影中的伴生種》(Working with Animals:Regarding Companion Species in Documentary Film)中拓展了對紀錄片電影中動物性的研究,利用堂娜·哈拉維頗具影響力的“伴生種”的概念考察了三部紀錄片:《又快又賤又失控(Fast,Cheap and out of Control)》(1997)、《灰熊人(Grizzly Man)》(2005)和《香草》(Sweetgrass)(2009)。拉迪諾說明了每部影片如何使一種人文主義(物種主義)的觀念去中心化,列舉了在工作中與非人類的動物“逐漸在一起”的方式,把非人類的動物作為在共享的環境中共同進化的成員。類似這樣自我反思性的紀錄片研究了一般的物種界限,對企圖仿制、客體化或邊緣化非人類動物的傾向提出挑戰,延伸了野生動物電影的范疇。
同樣是拓寬生態電影批評的疆域,妮可·斯塔羅謝爾斯基在《水流之上:水下電影文化史》(Beyond Fluidity:A Cultural History of Cinema under Water)中把我們的視線轉移至水下拍攝的影片。她采用歷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對1910到1960年的電影進行了考察,認為在早期的電影中,半水生區域就是少數他者的領地,而在50年代時這些地方變成了少數他者們領土爭端和互相取代的區域。到了60年代,電影和電視則依照太空時代的背景將海洋刻畫成要去殖民和馴化的地域。這些看似不著邊際的轉向其實引導著現代海洋生態電影的隱喻,至今還清晰可見的隱喻,比如在電影制作人詹姆斯·卡梅隆2012年潛入馬里亞納海溝時所拍攝的影像中。同時,這些早期水下電影也調和了美國作為海事主導力量的崛起,對于演化中的海洋政策也意義深遠。
克萊爾·莫莉對束縛電影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間廣泛的關系也同樣深感興趣。在文章《“自然書寫劇本”:商業野生動物電影與生態娛樂》(“Na—ture Writes the Screenplays”:Commercial Wild—life Films and Ecological Entertainment)中,莫莉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迪士尼自然”,迪士尼公司全新的獨立電影團隊。團隊秉承其早期《真實世界歷險記》中的精神,致力于制作、收購并傳播野生生物電影。她提出,迪士尼在環保主義者與普通大眾視野中的差異可以通過考察該公司對“綠色品牌”的打造進行解釋。在傳媒產業研究的理論視角下,該文聚焦當代企業環保語境中問題百出的自然,因而也順理成章過渡到了下一章節,在詳細研究商業、敘事電影中延伸這些討論。
在承認好萊塢電影制作存在生態方面問題的前提下,第三章“生態電影實踐:好萊塢和虛構敘事電影”著重于此類影片的潛力及其廣大的觀眾群體,以突顯主流社會一文化需求與焦慮。在《好萊塢與氣候變化》(Hollywood and Climate Change)一文中,史蒂芬·呂斯特堅定認為,像《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和《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nocent Truth)(2006)這樣反映氣候變化的電影已經通過把全球變暖的科學轉換成電影語言而在美國通行的環保語篇中引發了顯著的轉向。他的文章改編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提出了此類影片清晰呈現的一種“生態的文化邏輯”,而占主導地位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在其中既被看做是氣候變化的誘因,又是潛在的治理途徑。
在文章《戀之風景:<荒野生存>、<灰熊人>和<新海角樂園>所拍攝的自然》(Appreciating the Views:Filming Nature in Into the Wild,Griz—zly Man and Into the West)中,帕特·布里雷頓對商業電影采取了更為正面的觀點,探究了三部當代電影敘事作品。他認為這幾部影片對風景的獨特描繪體現了其在呈現自然的治愈形態時的積極主動。《荒野生存》(2007)追蹤了一心尋求冒險的年輕男主人公的生態心靈歷程,《灰熊人》(2005)審視了一位天真的自然主義者,他不接受荒野中有不應該被打破的界限的存在。而《新海角樂園》(1992)則集中表現了愛爾蘭鄉下所特有的自由與逃離中的幼稚浪漫與神話贊頌。在它們最后的場景中,布里雷頓指出,它們都可以被解讀為反文化與跨文化的生態公路電影,訴說著新一代人對親身體驗自然景色的渴求。
有別于布里雷頓借鑒浪漫主義在荒野自然中尋覓慰藉的傳統所選取的影片,卡特·索爾斯的《對魔鬼的同情:20世紀70年代鄉村殺人狂電影中的食人鄉巴佬》(Sympathy for the Devil:The Cannibalistic Hillbilly in 1970s Rural Slasher Films)一文側重展現并顛覆把荒野自然當成“恐怖、荒涼的曠野,滿是野獸和野人”的較古老的清教傳統。索爾斯指出,《德州電鋸殺人狂》(Texas Chainsaw Massacre)(1974)和《隔山有眼》(The Hills Have Eyes)(1977)等這些電影中的食人鄉巴佬形象,其實不過是城市觀眾投射他們對未知所懷恐懼的靶子。但是,與更早或較晚時期里把鄉下人表現成膽小惡棍的恐怖電影不同,20世紀70年代的鄉村殺人狂電影可以被理解為是對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社會與生態政治劇變做出的顛覆性(甚至或許是英勇的)回應,因為里面的“惡棍”可以被看做是系統性環境毀滅、自然資源逐漸減少,以及體制虐待勞動貧民情況下的受害者。
進行這類研究的學者為恐怖電影、公路電影、票房大片和其他門類體裁的商業制作影片提供了細致入微的閱讀,向我們表明生態電影無論如何不應被獨立制作圈定界線,因此,生態電影批評的視線還可以更加開闊。
在第四章“超越電影”中,薩爾瑪·莫娜尼和肖恩·庫比特把探索的目光越過了該學術領域內當下思考的界線。基于冉冉興起的電影節研究領域及其與公共領域理論的相互作用,薩爾瑪·莫娜尼的《環保電影藝術節:從電影節研究與生態批評研究的交界處開始探尋》(Environmental Film Festival:Beginning Explor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Film Festival Studies and Ecocritical Studies)一文提出,目前這些電影節的范疇受制于三種類型:官員公共領域、非官員公共領域和集團或商貿展覽領域。幾乎沒有哪個電影節只屬于其中單獨一類,但分析它們的身份構成可以揭示這些電影節如何在環境與媒介紛繁的大背景下為求生存而妥協的復雜方式,并為對生態電影這些獨特功能版塊的持續關注制造空間。
最后,肖恩·庫比特在《人人知道這什么都不是:數據視覺化和生態批評》(Everybody Knows This is Nowhere:Data Visualization and Ec—ocriticism)中說明,當電影批評家還在被現實影像困擾的時候,環境科學處理的是在實際中往往太無限,太緩慢,抑或又太分散以至于無法被成像以進行觀察的。為了向普通大眾和科學從業者展示這樣的數據,他提供了大量的數據視覺化策略。通過將視覺化置于其與民粹主義和人文主義論斷之間的關系中開展考察,庫比特提出,隨著圖表形式越來越多的在如《難以忽視的真相》一類的電影中得以應用,一股傾向于把世界歸為視覺數據的電影潮流隨之出現。這股潮流在羅蘭·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執導的一系列生態啟示電影中被賦予敘事形態,轉而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又在一組令人難忘的“虛構現實”電影中回歸,其中的現實自身被等同于它的數據形式。庫比特對經過電影改編的科學數據視覺化和聲像化的思考為生態電影批評打開了一扇超越照相現實影像繼續前進的大門,也為電影與媒介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三、天地交融:生態電影研究的未來走向
盡管《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選題寬泛,但文集中的幾個章節不可能妄圖包羅時下學術圈內所有現存的生態電影批評的方式方法,也不應該抱有這樣的幻想。在過去幾年里,因為越來越多的學者——常是在他們學生的啟發下——不斷開始關注生態問題,生態電影研究(以及普遍意義上的生態媒介研究)正以令人震驚的節奏成長壯大。伴隨該領域深入發展的,是學生與學者間通過課堂、會議、期刊和類似于《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這樣的文集展開合作的需求將會對我們在共享對話中的參與感至關重要。
雖然《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將焦點對準第一和第二電影(譯注:以好萊塢模式制作的電影稱為“第一電影”,歐洲式的藝術為“第二電影”)以求更加縱深地探究該領域發展問題中的關鍵思想。展望未來,我們發現生態電影研究中至少五處重疊交匯點,可以成為振奮人心的前進方向。第一,對第三電影(譯注:第三電影泛指第三世界電影工作者所制作的反帝、反殖民、反種族歧視、反剝削壓迫等主題的電影。本詞是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阿根廷制片人費南多·索拉納斯和屋大維·杰蒂諾在《邁向第三電影》中提出的)和第四電影(譯注:第四電影由導演巴利·巴克萊提出,代指少數人口的原住居民在主流文化中對自我表達的嘗試)的關注逐漸顯著,尤其因為它們亦屬于由跨國電影和媒體制作帶來的文化與環保問題。謝爾頓·陸和米佳燕選編的《中國的生態電影》(2010),和即將出版的由皮埃塔里·塔阿帕編寫的《跨國生態電影》便是近期在這一方向上的破冰之作。娜迪亞·波扎克與莎莉·漢朵芙在《銀幕足跡:燈光、相機、自然資源》(2012)中對因紐特電影制作者扎克拉爾斯·庫納克和伊蘇瑪電視臺的描寫,及《繪制美洲:當代本土文化的跨國政治學》(2009)分別對第四電影給予了亟需的關注。在深入研究這些課題之時,我們可以充分采納布里雷頓的認識,把浪漫主義的西部理想視為對此類電影所傳遞的生態信息的烘托,或者將某些概念改編應用于那些獨特地域性和全球化語境兼備的影片,如斯考特·麥克唐納“重塑感知”的理念,或史蒂芬·呂斯特提出的“生態的文化邏輯”。
第二,包含性別政治的電影也同樣值得重視,如在努爾·斯特金的著作《流行文化中的環境保護主義:性別、種族、性欲,和自然之物的政治學》(2009)中所展現的。針對該方向的最新文學生態批評——如以下三篇(部)2010年出版物:格瑞塔·伽德發表于《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中的《生態女性主義的新動向》,蒂莫西·莫頓發表于《現代語言學會會刊》的《怪異的生態》和斯泰西·阿萊莫的《肉體的本質:科學、環境,與物質自我》(2010)一書——都直指生態電影。在此方向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有效運用安德魯·哈格曼的意識形態批評模型、艾德里安·伊瓦克伊夫的哲學分析,或是路易·維萬科的歷史觀來展開對話。
第三,如果讀者在卡特·索爾斯對其環境正義的關注獨一無二的闡釋中找到靈感,可以參考薩爾瑪·莫娜尼,卡洛·阿里吉洛和貝琳達·趙合作編寫的《給環保鏡頭上色:電影、新媒體,與公平的可持續性》(Coloring the Environemental Lens:Cinema,New Media,and Just Sustain— ability)——《環境傳播:自然與文化學刊》(2011)的特刊,并將此作為鉆研性別、種族、民族,以及環境語境中地方與全球主動性的起點。同時,妮可·斯塔羅謝爾斯基的文章也在提醒我們,對環境正義的關注有助于在上述語境與后殖民主義的學科分歧間搭橋鋪路。我們誠邀有意拓展這一研究的生態電影批評家閱讀《環境正義讀本》(2002)、《窮人的環境保護主義》(2004),還有《后殖民生態批評》(2010)等書。詹妮弗·拉迪諾的文章同樣也可以作為把環境正義問題和個人探索融入批判性動物研究的一個有趣方向。進而,生態電影也會在對重要文本的持續發掘中得以升華,如《當物種相遇》(2008)及《動物與能動》(2009)。
第四,正如克萊爾·莫莉關于迪士尼自然的文章,薩爾瑪·莫娜尼對環保電影藝術節的研究,抑或大衛·英格拉姆采取的認知途徑,都表明對生態電影制作、發行和接受的開發還大有空間。在如此這般的探索中,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因為閱讀了即將面世的布朗·泰勒所編《化境與自然靈性》(2013)中針對讀者接受的文章,對肖恩·庫比特有關數據化論斷的研讀會被帶向怎樣深遠的思考;而如果再輔以那些探究通俗文化傳遞與環保立場形成過程中全球化作用的生態批評調查——例如烏蘇拉·海瑟2008年出版的《感知地點,感知地球:對世界的環保想象》——又會產生怎樣的思索。
第五,在全球對媒體的需求日漸膨脹的同時,電影與媒介的生態足跡也在累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加州政府于2006年共同開展了一項全面調查,其中把好萊塢電影產業列為全州污染大戶。正是一定程度上出于來自這項研究的啟迪,波扎克在《銀幕足跡》一書中追溯了被她稱為“碳氫化合物假想”的歷史。出于相似的視角,詹妮弗·蓋布瑞斯在《數字垃圾:電子產品的自然史》(2011)中就媒體的物質影響這一論題進行了考察,而托比·米勒和理查德·麥克斯韋爾將要出版的《讓媒體變綠》(2012)亦有異曲同工之處。無論大型電影制片廠近期為加強回收,購買混合動力車輛,以及聘用環保顧問所付出的努力是體現了他們邁向可持續性的積極一步,還是只不過是給企業披上了一件綠色的新衣,都必將是在未來幾年中激發辯論和持續調研的眾多論題之一。
總而言之,在構成生態電影研究的許多理論與實踐分支的重疊中,正在形成這樣一種認識,除去對電影生態足跡的某些擔憂,我們很多人一直喜愛觀看電影,恰恰是因著電影重新構建感知的能力。對生態電影批評家而言,電影與生態電影研究使我們能夠分辨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從人類中心的狹隘角度把個體的人本欲望置于道德宇宙的中心。正如《生態電影理論與實踐》封面出自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1979年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中的畫面所闡明的,非人類世界也許不會總以我們能夠理解的方式與我們交流,當來自荒野的犬科動物形象橫跨這片凄涼的人類荒地之際,觀眾的目光卻暫時從以胎兒姿勢臥于畫面底端的人類主人公形象身上脫離開去。畫面上下兩端的分隔讓人們的視線越過人類與非人類形象而飄向遠處波光粼粼的水面,沉湎在對天空的回憶中。孤立地對事物進行生態批評反思,已然成為電影這面朝向世界的鏡子中共有的回憶。
(責任編輯 潘亞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