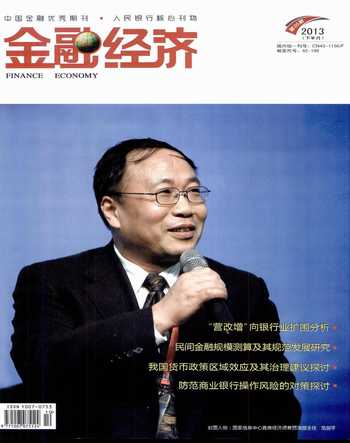基于聚類污染的“環境—貿易”庫茲涅茨理論及驗證:來自21個代表性國家的證據
蘭天 陳昊
摘要:近年來,收入的環境效應逐漸凸顯,國際貿易自由化亦已大勢所趨。關于貿易自由化所產生的環境后果等諸多問題的結論會直接影響一國環境、貿易政策的制定,進而在多國動態博弈條件下影響全球貿易格局,改變各國的貿易稟賦條件及相對比較優勢。本文首先在理論上分析了收入、貿易和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而后挖掘出21個國家的相關數據作為代表,運用聚類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綜合環境損害指標,在理論研究基礎上通過大量實證分析,研究貿易對環境損害的影響程度、路徑及現狀,以期在支撐理論結論的同時勾勒出全球范圍內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損害影響的概貌,為我國了解各國相關現狀,制定環境和貿易政策提供參考。研究結果表明:(1)污染水平隨收入水平以及貿易額增長先上升而后下降;(2)代表性國家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間具有關非常高的聯程度;(3)“惡化-頂端-改善”的倒U型路徑成為貿易增長對環境損害影響的主要路徑;(4)代表性國家中環境污染現狀趨于好轉的基本都為經濟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狀況仍在加劇的多為發展中國家。
關鍵詞:貿易增長;環境損害;相關性;現狀比較
一、引言
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研究始于上世紀70年代,目前學術界對貿易自由化所產生的環境后果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都是消極的,特別是對于欠發達國家而言,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將直接導致環境惡化。Copeland & Taylor(1994)的理論分析表明:自由貿易減輕了高收入國家的環境污染然而同時增加了低收入國家的環境污染。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當一國缺乏明晰的產權界定時,自由貿易對自然資源開采的影響,其結論是國際市場傳遞擴大了全球性公共資源的外部性,原本用于防止資源過度使用而設立的稅收政策很有可能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反而加劇資源的過度開采。Barrett(1994)認為,當環境政策的邊際損害很低時,生態傾銷會由于某些策略性戰略而出現。Dua & Esty ( 1997)以及 Esty & Geradin( 1997)都指出, 作為貿易自由化的結果, 各國會紛紛降低各自的環境質量標準以維持或增強競爭力, 出現所謂“ 向底線賽跑”,甚至出現阻撓環境立法等漠視環境管制的現象。與此同時,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貿易自由化盡管在短期內的環境效應是消極的,但是在長期自由貿易將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hagwati(1993)以及Grossman & Krueger(1995)的研究,他們把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分為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以及規模效應,他們認為,當收入達到某一水平時,技術效應和構成效應的加總將超過規模效應,貿易自由化得的發展將改善環境質量。Lopez(1994)也得到了基本類似的結果。經驗研究方面,Joseph C. H. Chai(2002)考察了中國自1979年之后20年伴隨貿易開放程度與制造業“三廢”排放量之間的關系,考察結果表明,規模效應巨大的負向作用完全抵消了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的正向作用,從而導致中國制造業整體污染排放增加。Qureshi(2004)對巴基斯坦的工業水污染惡化的問題研究中也證實了貿易開放加劇了環境污染。Maniagi(2004)使用63 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證明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而,Lucas 、Wheeler和Hettige(1992)采用了1960 年至1988 年間包括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內的80個國家的37個制造部門污染排放的面板數據,發現在貿易自由化的初級階段,毒性密度指標起初明顯上升,但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這一指標呈下降趨勢,即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整體環境的改善。Anderson(1992)通過對世界食品和煤碳行業的研究發現,煤碳和食品貿易的自由化減少了這些產品帶來的全球污染。 Dean(2002)用世界銀行關于中國1987~1995 年各省份水污染的相關數據,研究發現: 貿易自由化對環境質量的破壞具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并且這兩種效應在符號上是相反的,模擬結果表明貿易對環境正的技術效應抵消了負的結構效應,最終對環境凈效應是正的,貿易開放有益于環境的改善。綜合以上文獻,不難發現,關于自由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研究結論并不統一,而且這些研究所采用的數據大都較早,鮮有研究國際背景下綜合環境損害和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和實證文獻。因此,本文將試圖通過聚類因子分析方法試圖解決綜合環境損害指標的選取和構建,并通過大量相關性和多元回歸分析,盡可能地勾勒出全球范圍內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損害影響的概貌。本文第二部分以經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礎,借鑒McConnell(1996)模型,在對其進行簡化的同時,加入貿易額為效用函數的一個變量,在分析收入與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的同時加入了貿易與環境損害關系的分析;在第三部分,運用聚類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綜合環境損害指標,在理論研究基礎上通過大量實證分析,重點貿易增長對環境損害的影響程度、路徑及現狀;第四部分為結論。
二、理論模型
為簡化分析,我們主要考慮兩個要素:消費者對環境服務的需求和消費對污染排放的影響。這樣,人均收入,貿易自由化 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依賴于兩個命題。與第一個要素相聯系的命題是:環境所提供的服務,即環境舒適性,是一種奢侈品,也就是說,對環境舒適性的需求的收入彈性大于1。如果這一點成立,那么隨著人均收入及人均貿易額的增長,用收入換取環境舒適的意愿水平就會隨之上升。而對于后者也有一個相應的命題: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自由貿易的發展,消費對污染的負效應遞減。直觀地,因為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結構會發生變遷,從而生產和消費結構也會隨之變化。
這樣,我們同樣可以得到如下結論:污染水平隨貿易增長先上升而后下降。到這里,我們驚訝的發現,通過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似乎與經典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結論不謀而合,而且我們還得出一個結論:貿易增長和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同樣滿足庫茲涅茨曲線。
三、實證檢驗
(一)相關概念界定和數據說明
1、代表性國家的選取標準。為了使選取的二十一個代表性國家能夠反應全球貿易和環境損害關系的基本情況,本文以聯合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定義為標準 ,選取了十一個發達國家,十個發展中國家。在選取的的過程中,主要考慮:世界影響、地理位置、國家概況等三個方面的因素。2.貿易指標和環境損害單項指標的選取 。本文主要研究有可能導致本國環境損害的的那部分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之間的具體的關系,所以出口額無疑是和本國環境損害關系最為緊密的貿易指標。3.環境損害綜合評價指標的建立。通過對已有文獻梳理不難發現,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環境和貿易的現狀以及環境和貿易之間的關系都有著一定的差異;不同學者研究環境損害與經濟、貿易之間的關系時使用的污染指標也不盡相同。建立一個綜合的、相對全面的環境損害評價指標似乎就變得尤為重要,并且,這個綜合指標應考慮多個方面的污染,兼顧各個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內在關聯性。計量結果表明,各個國家構成W的因子至少都包含了所有污染指標90%以上的信息量,這種包含比重是可以用少數的因子來衡量整個的環境水平的。KMO-Measure值都大于0.5,說明所有國家的環境污染指標數據都適合使用因子分析法進行分析。
(二)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的相關性分析
借助之前構建的環境損害綜合評價指標,本文通過灰色關聯分析研究代表性國家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的相關關系。 貿易指標數據來源于WTO公開數據庫,使用的污染指標數據是經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公開數據計算而得。使用灰色系統理論建模軟件(GTM)來進行灰色關聯分析的計算。最后的灰色相對關聯度分析的結果如表2所示:相對關聯度在0.5以上的序列數據一般認為表現出比較顯著的趨同性,通過對表4-2的觀察可以明顯的發現,所有二十一個代表性國家貿易和環境損害之間的相對關聯度都在0.5以上,除了丹麥和越南分別為0.5351和0.5705以外,別的國家貿易和環境污染的關聯度都在0.6以上,超過0.8的有十三個國家。由此可以判斷,代表性國家的貿易和環境損害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中國0.60,挪威0.78,冰島0.87,加拿大0.95,英國0.85,法國0.77,德國0.88,葡萄牙0.83,日本0.80,丹麥0.54,巴西0.96,阿根廷0.97,美國0.87,澳大利亞0.91,土耳其0.75,越南0.76,南非0.75,巴基斯坦0.98,印尼0.90,印度0.71,俄羅斯0.92)
(三)代表性國家貿易、收入與環境損害關聯路徑實證檢驗
下面我們通過代表性國家的數據來對這一理論命題進行實證檢驗。我們希望通過分析,在驗證貿易,收入與環境損害具體關聯路徑性態的同時,能夠描述目前全球經濟、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關系現狀,通過代表性國家當前在長期EKC曲線上的位置來估計未來環境和貿易關系的發展趨勢。
實證結果與比較。觀察圖1,有九個國家人均GDP和出口貿易額與環境損害評價指標擬合的回歸方程的形態是一致的。短期來看,所有的回歸方程中有十五個為線性形態,十三個為N型形態,有十一個為倒U型形態,有兩個為U型形態,一個回歸方程無法擬合。長期來看,有十二個國家目前經濟、貿易和環境污染的狀況處在長期曲線的左端,四個國家當前經濟、貿易和環境污染的狀況處在長期曲線的頂端,有五個國家處在長期倒U型曲線的右端。分析圖1,不難發現,代表性國家中環境污染現狀趨于好轉的基本都為經濟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狀況仍在加劇的多為發展中國家。通過代表性國家經濟、貿易與環境現狀在曲線上的位置可以判斷,處于頂端或者右側的九個國家中有八個為經濟發達國家,處在左側的十二個國家中,只有三個為經濟發達國家,其余都是發展中國家。此外,通過觀察曲線的形狀可以發現,幾乎所有(英國除外)環境損害有所改善的國家,收入、貿易對環境的影響路徑都是一個先導致環境惡化之后到達頂端,然后使環境狀況有所改善的路徑。
四、結論
本文以經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礎,在對McConnell(1996)模型行簡化的同時,加入貿易額為效用函數的一個變量,在分析收入與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的同時加入了貿易與環境損害關系的分析。而后運用聚類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綜合環境損害指標,在理論研究基礎上通過大量實證分析,研究貿易對環境損害的影響程度、路徑及現狀,實證結果在很好地支撐理論結論的同時基本勾勒出全球范圍內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損害影響的概貌。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通過理論分析,我們認為,污染水平隨收入水平以及貿易額增長先上升而后下降。這一理論結論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結論相符。通過對代表性國家貿易增長和環境損害進行灰色關聯分析,我們發現21個代表性國家中有19個國家的灰色關聯度在0.6以上,代表性國家自由貿易對環境損害的影響關聯程度非常高。通過具體影響路徑的實證檢驗,我們認為“惡化-頂端-改善”的倒U型路徑成為貿易增長對環境損害影響的主要路徑,這一實證結論很好的支撐了第一部分的理論分析。從影響現狀上看,代表性國家中環境污染現狀趨于好轉的基本都為經濟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狀況仍在加劇的多為發展中國家,這一實證結果充分證明了理論分析中環境污染水平以貿易額或者人均收入特定值為拐點的正確性。
參考文獻:
[1]Copeland, B. R. and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3, 1994, pp.755-787
[2]Chichilnisky, G. “Global Environment and North South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994, pp851-874
[3]Barrett , S.“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4, 1994b, pp. 325- 338.
基金項目:中國外貿增長引致環境損害的沖突與協調研究06XJL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