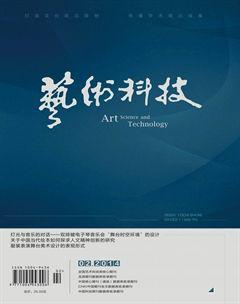生態文明視域中的內蒙古文學
吳玉英
摘 要:內蒙古的很多文學自覺不自覺地潛伏著一股生態主義的潮流。因此,生態批評不僅是內蒙古文學研究的新的突破口,也是內蒙古文學發展的助推器,還是內蒙古生態文明建設的精神支撐。
關鍵詞:內蒙古;文學;生態文明;批評
21世紀是一個人類生態學的時代,所有的學科都無法回避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內蒙古的文學研究也應該緊跟時代和現實的需要,認真貫徹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的重要思想,針對內蒙古民族地區的文學創作實際,整理、發掘其中具有生態傾向的創作,考察內蒙古文學中蘊含的豐富生態智慧,為內蒙古文學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1 生態批評是內蒙古文學研究的新的突破口
“生態批評”作為在生態危機的特殊語境下誕生的一種新的綠色文學批評,其實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在英國美國嶄露頭角,從此之后發展迅猛,現在已成為很多國家文學批評領域中具有重大影響的流派之一。如今的生態批評在國際上已逐步成為“顯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也逐漸成為我國文學領域中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理論形態,愈來愈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與重視,學人們陸續組織召開了生態批評的相關學術會議,各種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相關論文,數量也是極為可觀的,與此同時還涌現出了一批代表性理論專著。事實證明,這些研究都是我國新時期學科建設的重要收獲,但是這些成果多是就其理論形成的現實可能性、學理上的合法性等問題展開研討,截至目前為止我國的生態文藝學研究與文學實際創作結合得還遠遠不夠,生態批評發展不甚理想,與國際差距較大,在目前的形勢下已不能完全滿足生態文明的需要。
內蒙古作為一個特殊的生態“區域”,由于傳統和地域的原因保留著親近自然的天性,生活在這里的作家們,不論是蒙古族還是漢族,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態文學”的情況下,只是用語言文字把他們對生態的關心與焦慮形象地表現出來,成為我國文壇中較早關注生態、并至今還執于表現生態的重要群體,在他們的很多作品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生態資源信息,自覺不自覺地潛伏著一股生態主義的潮流,這些理應成為生態批評發展的實踐基礎。黑格爾說:“在文明初啟時代,我們更常會碰見哲學與一般文化生活混雜在一起的情形”。[1]內蒙古文學中呈現的生態觀正是如此,雖然缺乏理論性、系統性的概括,但它以更為直接的方式蘊涵在作品中。但由于歷史的現實的原因,我們對于內蒙古文學的傳統研究更多強調的是其民族特色。文學的民族性特征,一直以來都是內蒙古文學研究的重要話題,備受各個歷史時期作家和學者們的共同重視。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同志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曾針對文學的民族性問題做出明確指示,并強調其對于內蒙古地區文學的繁榮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于是,文學創作的民族特征、民族風格便成為內蒙古作家們自覺訴求。內蒙古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審美形態,集中表現神秘奇特的異域風情,瑰麗震撼的自然景觀,別具一格的精神信仰等“民族”特征成為人們對其的思維定式認同,而作品中不自覺流露出的生態思想則長期被評論界和讀者所忽視。對內蒙古文學做集中的生態聚焦,較之于以往學界對內蒙古文學的民族性、地區性研究,無疑是新的拓展和補充,但是從內蒙古生態文學批評的發展水平來看,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目前都相對滯后、薄弱,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文學中大量存在的豐富生態審美智慧缺乏全面系統地發掘、整理。
2 生態批評是內蒙古文學發展的助推器
(1)弘揚內蒙古的民族文學。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版圖中,主流敘事基本是圍繞漢民族的歷史變遷、社會變革以及生活脈流展開的。漢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經驗、價值觀念、信仰態度占據了文學的大壁江山。雖然各少數民族地區的作家作品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擁有自己的重要位置,但是由于地處邊緣,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或者由于自身文化存在不足等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的作家作品遠遠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幾乎未被完整地納入到主流文學的視域。這種狀況導致的結果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學研究所占據的微小比例與我國少數民族種類的多樣和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多彩并不相稱。對于急需找到發展出路的民族文學來說,生態文學研究可以提供一個使其走出傳統、走出邊緣、走向現代的契機,內蒙古文學研究應該朝著這個更有生命力的方向發展道路。但遺憾的是,當內蒙古大量的作家致力于對生態問題的探索及表達時,并沒有得到讀者和批評家認真的響應,而及時地對作品加以生態批評,對于提升作家創作水平、促進文學繁榮發展有著不容輕視的作用。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對不被廣大讀者熟知的內蒙古文學進行生態研究,使更多的人了解內蒙古文學的真實面貌,使之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中不可忽視的一道獨特的文學景觀,進而豐富現當代文學的品格和內涵。
(2)發展內蒙古的生態文學。雖然我國的文學創作呈現出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局面,生態文學研究在眾多學者們的不懈努力下發展迅速,收獲喜人,但其中真正能從生態學立場出發進行生態解讀的作品屈指可數,盡管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生態文學創作日趨繁榮,但表現生態題材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報告文學、電視專題片等文藝作品也只是散見于文壇。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創作,以及分析解讀現有作品中蘊含的生態智慧,在文學的整體研究中還相當滯后,與生態批評理論的發展不同步。因此,文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應該肩負起推動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發展的重要責任。
以“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為核心理念的蒙古族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受其影響,內蒙古的文學也是如此。獨特的地域自然條件和民族信仰催生了內蒙古文學藝術家的生態創作,使他們的創作進入到詩意棲居與美好生存的現實關懷。20世紀60年代云照光編劇的故事影片《鄂爾多斯風暴》、70年代扎拉嘎胡創作的長篇小說《嘎達梅林傳奇》,分別是以20世紀20、30年代的民族英雄席尼拉瑪和嘎達梅林領導的鄂爾多斯“獨貴龍”運動和哲理木草原牧民反抗王爺與封建軍閥相勾結墾荒種地、破壞草原為題材的作品,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老一輩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敖德斯爾等創作的小說,納·賽朝克圖、巴·布林貝赫、賈漫、周雨明等創作的詩歌,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保護牧區草場的問題。進入新時期以來,特別是在當代草原生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生態平衡問題突顯出來,一批反映生態的作品也應運而生,如烏熱爾圖、滿都麥的小說,寧才導演的故事影片,尚貴榮的散文等,都深刻反映了生態破壞造成的災難,深情呼喚人們保護大自然。肖亦農、布仁巴雅爾、薩仁托婭分別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等,則反映了一批綠色人物創造的真實的綠色故事,譜寫了一曲曲感天動地的綠色壯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我們欣喜地看到,在當今多樣化的寫作中,這些作家已經成為中國生態寫作領域的開拓者和領跑者,并已真正地進入了理性的思考狀態,形象化地把這種對于生態環境的憂患流注于筆端,而且相當一部分作品的思想性是深刻而耐人尋味的。對此,內蒙古的文學批評不能漠視社會現實所發生的變化而固守舊有的文學批評模式,也要發出自己獨特的引人注目的聲音,為中國和世界的生態批評注入民族性、地區性的元素與資源,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