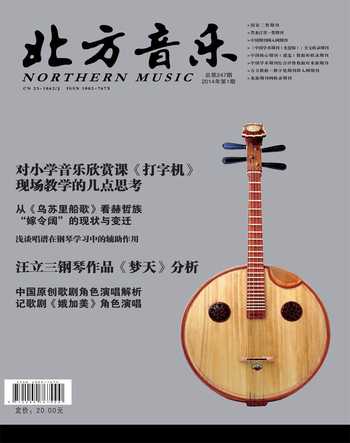淺談音樂刨作的形態類別
雷士奇
音樂創作這一人類高級精神活動,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即伴隨著人類文明的產生、發展與成熟。音樂創作中,到底有多少基本形態以構成其總體形態的全部?一般約定俗成的觀念是:和聲、復調、曲體、配器,俗稱“四大件”。其實這只是從練習音樂寫作技術角度的表層類分。如果我們從音樂創作整體構成的角度來探尋其形態類別,它應包含有五類:旋律學、多聲部學、結構學、織體學、載體學。
一、旋律學
旋律,音樂表現手段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建立于音階、調式、節奏、節拍、結構之綜合統一。旋律就其定義而言,有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是指建立在由音階、調式、節奏等元素組成的基礎上的一條具體的、含有表情意義的樂音線條。廣義的則是指一種一般為旋律所特別具有的表情因素。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歷史的、社會的原因,旋律往往被誤認為是音樂表現手段的“惟一”。及至20世紀現代派興起,又因其過時而將其廢人“冷宮”!應該說,兩種極端都不客觀:我們既不能將其視為“惟一”,亦不應貶其為“過時”。我們知道,在人類音樂創作發展過程中,不論在西方或東方,旋律均有過、并仍然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只是到20世紀近現代音樂思潮興起,它才被十二音體系“瓦解”,被無調性所“淹沒”,在西方專業音樂創作中有意無意地被貶為保守而故意回避。
然而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在民間音樂原始生態保持較為完好的環太平洋——亞非拉地區,旋律在音樂創作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大批作曲家在實踐中對其不斷開拓創新,一些理論家則高舉“旋律學”的旗幟,從理論上、技術上、功能上對其進行全面的論述。
二、多聲部學
多聲部寫作,是音樂創作不斷進步、脫離原始的單聲部寫作后的發展之必然。多聲部寫作包含兩大部分:縱向的——和聲寫作,橫向的——復調寫作。前者更多地考慮和弦、和音的縱向音響構成,后者則著重安排音序、音列的橫向線條連接。在實際創作中,兩者是不可能截然分割的;然而,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品又有不同的側重。因此,我們既從總體的形態類別上稱其為“多聲部學”,又要明確其實際上涵蓋著兩個不同部分:和聲學、復調學。
多聲部形態的最大特征是,它脫離了樂思。平面的單一原始陳述,進入到樂思立體的多樣展開與多層交織;不可否認,這是音樂創作從低級向高級、從業余向專業不斷進步發展的標志;也是不斷提高音樂創作技藝,擴展音樂創作深度、廣度的必須。
多聲部寫作要求于作曲家的,不僅要有經過嚴格訓練的聲部寫作技術,而且要有自幼培養的敏銳精確的“心耳”。兩者缺一不可。前者完成體現“心耳”的音響想像,后者則控制著寫作技術的熟練與精確。
三、結構學
結構學是音樂形態學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樂思發展的形式邏輯,它包含著一部作品由核心形成到發展完成的全過程中的每一節框架,每一種手段,猶如大廈的鋼筋、人體的骨架,結構決定著樂曲的基本全貌。
誠然,一部樂曲的構成包含著很多的純技術成分,但也必須看到,樂思的發展總是帶有強烈的文化傳統影響:一個民族固有的思維模式、欣賞習慣、陳述方式等,都會極自然地滲透到作曲家的美學觀中,形成其本民族獨有的樂思發展邏輯和手段。但人類的音樂思維又畢竟還有許多共性。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從結構學的觀點來看,人類既有其樂思發展的共有規律,又有其基于不同美學理念的不同的具體思維習慣、發展手法,這應該是我們從宏觀上要把握的一個主要點。把握住它,我們就能清楚地了解“結構形態”在東西方音樂創作中的共性與個性。從而能在音樂創作中更為自覺地選擇、運用,進入到一個“自由王國”。
四、織體學
織體作為樂曲中的一種形態,作曲樂思的一部分,自多聲部音樂形成起即已存在。主調音樂的織體,常獨立于旋律線條之外,但又依附、襯托著旋律。復調音樂的織體則常與旋律形成多線條伴隨性的對比與模仿。
近現代專業寫作發展迅猛,織體寫作在繼承古典傳統基礎上,已有大量質的突破。它更具有獨立的表情意義,結構意義。因此,將其列為一種單獨的音樂形態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不同的寫作手段,不同的織體,又往往是不同的創作方法的體現:點描織體、微分音織體、超音距織體等等。還要指出的是很多初學者,一般易從總譜視覺上來分析織體的功效。其實,更應從聽覺上予以感受。有時往往總譜上非常華麗、壯觀,而實際音響則被重疊、覆蓋,反顯單調。
五、載體學
音樂創作不同于其他藝術創作,作者的樂思不能直接、必須通過中間載體傳達于受眾。
音樂創作的中間載體包括三種形態:器樂一管弦樂、聲樂一人聲、電子樂——電聲。
應當指出,在音樂創作的實際運用中,以上三種載體可單獨出現,亦可交織運用,形態多樣,聲響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