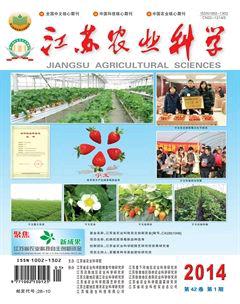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構建
尹珂 肖軼
摘要:基于multi-agent system建立了土地利用研究體系,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將multi-agent技術與GIS技術、數學模型方法結合起來,最終實現智能獲取土地利用優化方案。
關鍵詞:土地規劃;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multi-agent System
中圖分類號: F301.24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2-1302(2014)01-0379-04
收稿日期:2013-06-12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41201597);重慶市基礎與前沿研究項目(編號:cstc2013jcyjA0583)。
作者簡介:尹珂(1981—),男,重慶人,博士,從事土地利用與生態過程研究。E-mail: knomi@qq.com。19世紀80年代末,學者們圍繞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開始展開辯論,與此同時,土地利用可持續性開始受到人們關注。土地利用規劃是對一定區域內未來土地利用超前性的計劃、安排,是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土地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的綜合措施。尋求符合區域特點、實現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土地利用決策方案是土地利用規劃的主要內容,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是在保證其效率最大化的前提下解決土地供需平衡的有效途徑[1]。土地利用的實質是土地自然生態子系統、土地社會經濟子系統以人口子系統為紐帶耦合形成了土地生態經濟系統[2],土地利用結構是該系統的核心,只有用地結構合理,才能保持土地利用系統良性循環,利用較少的消耗或投入取得較高的效益[3-4]。因此,必須用系統觀念來指導土地利用、制定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方案、實現綜合效益最大化。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在一定區域內,為了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效益最優,依據土地資源的自身特性、土地適宜性評價,合理安排區域內各種土地利用類型,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維持土地生態系統相對平衡,實現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5]。近年來,很多學者在土地利用與環境變化、土地利用規劃模式、可持續土地評價等方面開展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這些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研究內容上多側重于土地利用結構的監測、分析、模擬[6];空間尺度上多側重于全球大區域或國家尺度的研究[7-9];研究方法上趨向于構建大量模型深入研究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的驅動力、影響因子[10-12];對土地利用系統要素、結構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或采用建模方法并結合GIS技術對單一土地利用系統進行模擬、分析[13],對區域土地利用結構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見。由于土地的固定性、自然性,區域的自然、社會條件存在差異,決定了土地屬性、土地利用方式存在區位差異,表現為土地質量、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特點、土地利用方向不同[14],然而這些屬性在一定范圍內又具有相對一致性。土地利用分區是在綜合研究土地綜合體的各種組成要素基礎上,考慮土地利用現狀特點及其歷史,以最大限度發揮土地生產潛力及改善土地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為出發點,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用地結構、形式等在空間上進行分區[15]。因此,應當根據不同區域的特點,確定土地利用方向,有效利用土地資源,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發揮區域優勢,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土地利用規劃是為協調人地矛盾而改變并控制土地利用方向,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布局,提高土地產出率,依據社會發展要求和當地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在時空上合理分配組織一定區域內未來土地利用的綜合技術措施。系統控制是土地利用規劃的本質,人地矛盾協調是系統控制的目標,控制、平衡、優化是實現協調的手段[16]。本研究擬構建一個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旨在為制定土地政策提供依據。
1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定位
構建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并掌握其可能發揮的作用需要仔細分析土地資源利用政策的制定過程。有學者提出一種高度模式化的土地利用規劃制定過程,如圖1所示,利益因素是制定重點,這樣可以避免政策的主觀性。政策制定過程的不同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信息,這些信息來源于不同的土地利用分析、建模方法。有學者認為,相對于政策的社會接受性、經濟可行性,應該優先考慮土地資源系統擁有的潛力、缺陷。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如果在土地利用政策制定的最初階段就強調政策杠桿的作用,容易使決策者忽略土地資源系統本身的自然屬性。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在土地利用政策制定的最初階段就充分考慮政策的指向性。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構建遵循前一種觀點,也就是說只有確定行政目標以及技術上可行的方案以后,才考慮具體政策及其實施。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目標是應用定量的系統分析方法,探索土地利用模式。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目標:(1)確認城鄉發展與土地資源利用目標間的潛在沖突;(2)探尋最能滿足城鄉發展目標(即技術可行、經濟可行、環境無害)的土地利用模式;(3)采用利益因素替代利益群體,從而將影響土地利用系統的各利益群體融入定量模型中,創建更加透明的決策過程。
2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構建
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是在村、鎮、區(縣)3個尺度下使用不同的技術方法探索土地利用模式,然后以此為基礎加
入各尺度下不同的利益群體,評價并討論方案,以建立整個區域的土地利用體系。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運行結構主要包括3個組成部分:(1)土地利用數據與社會經濟數據的收集與處理;(2)根據政策目標與開發計劃在各尺度下進行土地利用優化配置;(3)運用multi-agent system(MAS)實現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由于不同尺度下土地利用優化配置是整個系統的關鍵部分,所以應該與各利益相關者進行交流,介紹擬采用的優化方法以及相關案例,然后共同對方案進行協商討論。因此,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研究步驟如下:(1)掌握研究區各種可行的土地利用形式以及各種自然的、社會經濟的限制條件,探索土地利用優化方法;(2)理清影響研究區發展的利益群體,找出具有代表性的相關利益因素;(3)構建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endprint
2.1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形式
圖2演示了不同利益相關群體在各個階段的參與情況。第一步,研究人員與各尺度利益相關者(包括農戶)進行協商討論,以便定義要解決的土地利用問題并了解當前土地利用特點;第二步,確定不同尺度土地利用目標并量化其過程,討論哪些利益相關因素適宜代表利益相關者加入模型中,然后研究人員與利益相關者審查模型、數據,探討相關利益因素的選取是否合理,從而改進模型、填補數據空白,制定土地利用方案;第三步,討論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能力、局限性以及需要改進的步驟。
2.2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框架
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是將優化模型放入系統分析框架,以建立土地利用優化運作體系。由于該體系涉及3種尺度,因而在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尺度效應。因此,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強調反復性(圖3),即不斷協商各尺度土地利用方案,使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尺度推演得以順利完成。 MAS是一種十分適用于參與性分析的系統。MAS中 Agent 有自己的標準、行為規則,它可能是社會群體,也可能是一種制度,甚至可能是一種主張。為了實現前述尺度推演過程,本研究提出基于利益相關者Agent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框架。
2.2.1MAS中利益相關者Agent分析基于MAS構建多尺度土地利用系統,利益相關者的識別、選擇是設定Agent標準、行為準則的關鍵。構建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需要利益相關者的參與,該過程很大程度上受研究區域本身社會、經濟、生態屬性的限制,不同區域研究過程中的參與因素有所不同,所構建的系統也有所差異。對于這些相關利益因素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來加以分析:(1)不管是上述開發步驟中的哪一步,相關利益因素的“徹底性”都至關重要。所謂“徹底”即相關利益因素及時并且持續地參與整個過程。決定其參與性質時必須明確分離決策因素、土地利用因素、執行因素,所選擇的因素必須有適當介紹、解釋,比如某一利益因素是數據
提供源,或者是技術工具的執行關鍵等。(2)必須提升反饋效率,在利益相關者與研究者之間形成相互依存關系,這是參與式研究的必要條件,更是產生創新的基礎。原因包括如下幾點:可以對復雜新穎的研究概念、研究方法加深理解;可以提高相關利益因素的反饋速度;可以增強相關利益因素在整個過程中的參與持續性。(3)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的目的是探索、開發土地資源利用戰略,相關利益因素反映較短時間內的情況。
2.2.2基于MAS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在前述分析基礎上構建基于MAS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圖4)。MAS的組織結構是Agent個體之間互動框架,由Agent個體、Agent組及Agent域3級組織構成。Agent組是MAS的基本組成單位,是由多個相對簡單的Agent個體組成的、關系較為密切的一種多Agent結構類型[17]。本研究中,Agent個體就是政府、農戶、科研工作者等,他們共同組成了利益相關者 Agent 組。Agent域一般是將地理上緊密相鄰的一個或多個 Agent 組劃分為1個集團,稱為1個域。將Agent組進入并產生交流的區域稱為Agent域。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最核心的部分是圖中的三角形區域,該區域有3個主要組成部分:理論概念域、實證分析域、模型方法域。在實證分析域中利益相關者通過訪問交流的形式進入,收集并分析數據、意見(半結構式訪談、GIS空間疊加分析等),而模型方法域則以利益相關因素的形式進入,進行計算模擬(聚類分析法、模擬退火算法、多目標線性規劃法等)。為了使實證分析域、模型方法域有明確的目標、指導思想,筆者引入了理論概念域。在理論概念域中各利益相關者對土地利用目標進行分析(條件價值評估法、空間自相關分析等)。模型方法域靠實證分析域進行計算、校準,反過來實證分析域也可以驗證模型方法域的結果,理論概念域則指導數據收集、模型構建,實證分析域、模型方法域也反過來影響理論概念域。Agent個體之上有“組” “域”2級管理協作機構,可以有效減少系統的內部沖突,具有更強的問題求解能力,提高交流效率。“組” “域”是開放、動
態的概念,其中的成員數目是動態變化的,成員可以動態地加入或退出。這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可視為Agent隨環境及目標需求的不斷變化,連續進行協作關系的適應性調整過程。在這樣的系統中探尋土地利用優化方案,可以有效調動利益相關者,確保各尺度的土地利用優化方案都是經過利益相關者反復交流的結果,制定過程上一改往日“由上而下”的規劃體系,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參與式規劃。Agent組是1個數據庫,可以采用人們易于操作的圖形用戶界面進行管理,然后利用GIS技術實現圖形與數學方法的有機結合,最終實現研究目的。可以看出基于Multi-Agent的土地利用研究體系遠比其他體系復雜,將Multi-Agent技術與GIS技術、數學模型方法結合起來,最終實現智能化獲取土地利用優化方案。
3結論與討論
3.1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在政策制定中的潛在作用
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是針對土地利用分析、政策制定的某一特定方面,即揭示戰略性土地資源利用沖突以及各種替代性土地資源利用方案的可行性。從概念上講,要決策者考慮得更長遠似乎很困難,但是通過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可以提供戰略思維。由于這些問題都具有不可預見性,所以在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中的模型函數以及替代性土地利用方案中都應有所體現。在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中加入了環境目標。對于土地規劃的工作者來說,既要揭示土地本身的規律,還必須指出存在的不確定因素。此外,還要對方案的靈活性、限制性進行探討,比如方案的成本。土地利用優化過程中使用量化的模型方法增強了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尺度結合的能力,所以決策者可以通過系統的預測能力評估可能的或可行的土地利用變化,這將提高系統的政策設計能力,從而評價政策在既定目標下的有效性。
3.2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中相關利益因素的信息反饋endprint
在以模型為基礎的土地利用研究中,利用可量化相關因素配以利益相關者的互動目前較為少見,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利益相關者與研究者的互動改變了舊的模式,在研究者與利益相關群體之間建立并保持一種相互依存的可持續發展關系。研究者應當深入了解實際規劃過程,清楚所需要的信息,從而知道哪些是關鍵的參與者。優先確定利益相關者在整個規劃過程中的確切作用,然后選擇適當的人參與其中。只有在各利益相關者對問題有足夠的共同認識并且需要解決方案的前提下,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才能執行成功。一旦該系統可以成功開發出簡單且明確的操作界面,就能夠成為揭示土地利用的潛在沖突、展現土地資源的戰略使用方案以及促進不同利益群體間交流的強大工具。
3.3研究展望
多尺度土地利用優化系統利用量化方法洞察土地利用的優勢與局限,而系統本身的預測性使其不僅能夠探索新的或正在出現的土地資源利用問題,還可以獲取沖突目標之間的妥協方案。利益相關者與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能產生大量信息并回饋到模型中,修正初步結果。將計算機智能模擬應用到社會科學問題研究中有利于理論模型的實際應用。
參考文獻:
[1]Loevinsohna M E,Berdegue J A,Guijt I. Deepening the basis of rural resource management:learning processes and decision support[J]. Agricultural Systems,2002,73(1):3-22.
[2]王萬茂,韓桐魁.土地利用規劃學[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44.
[3]黃進良,饒鳴,張宇賓. 湖北土地利用區劃與可持續利用區域模式[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36(4):521-525.
[4]嚴金明. 土地利用結構的系統分析與優化設計——以南京市為例[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1996,19(2):88-95.
[5]劉榮霞,薛安,韓鵬,等. 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法述評[J]. 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41(4):655-662.
[6]陳書卿,刁承泰. 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用地結構變化及演變趨勢——以重慶市梁平縣為例[J]. 水土保持通報,2009,29(5):160-164,173.
[7]Huang S C,Hesse C,Krysanova V,et al. From meso-to macro-scale dynamic water quality modelling for the assessment of land use change scenarios[J]. Ecological Modelling,2009,220(19):2543-2558.
[8]Schmidt T G,Franko U,Meissner R. Uncertainties in large-scal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A case study for simulation of nitrate leaching[J]. Ecological Modelling,2008,217(1/2):174-180.
[9]Chen S Y,Liu Y L,Chen C F. Evaluation of land-use efficiency based on regional scale:a case study in Zhanjiang,Guangdong province[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2007,17(2):215-219.
[10]Long H L,Tang G P,Li X B,et al.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of land-use change in Kunshan,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rea of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7,83(3):351-364.
[11]Serra P,Pons X,Saurí D. Land-cover and land-use change in a mediterranean landscape:A spatial analysis of driving forces integrating biophysical and human factors[J]. Applied Geography,2008,28(3):189-209.
[12]何祖慰,楊忠,羅輯. 西藏昌都地區土地利用結構熵值時序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7,16(2):192-195.
[13]陸汝成,黃賢金,左天惠,等. 基于CLUE-S和Markov復合模型的土地利用情景模擬研究——以江蘇省環太湖地區為例[J]. 地理科學,2009,29(4):577-581.
[14]Roetter R P,Hoanhb C T,Laborteb A G,et al. Integration of systems network(SysNet) tools for regional land use scenario analysis in Asia[J].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2005,20(3):291-307.
[15]張元玲,任學慧,鈔錦龍. 遼寧省土地利用綜合分區研究[J]. 資源與產業,2009,11(4):46-50.
[16]溫占軍,晏曉紅,耿馮康,等. FAO可持續土地資源管理綜合規劃指南及啟示[J]. 農業工程學報,2005,21(增刊):142-145.
[17]馬守明,程顯毅,徐照財. 基于Agent圖的三級多Agent系統組織模型[J]. 計算機應用與軟件,2008,25(4):22-24.高云,陳偉忠,詹慧龍,等. 現代農業示范區農業產業集群發展分析[J]. 江蘇農業科學,2014,42(1):383-38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