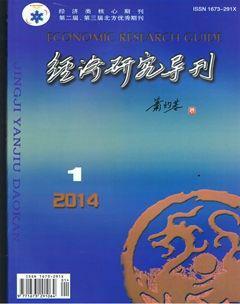翻譯中的隱喻認知與跨文化交際意識研究
閆愛靜
摘 要:隱喻現象作為語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最常用和最有力的認知世界、表述觀點與情感的手段。作為譯者,能夠充分洞悉隱喻現象的認知異同,是實現在譯出語和譯入語之間準確、有效翻譯,并實現跨文化交際的前提條件和成熟標志。在前人的理論基礎上對隱喻思維的形成及文化認知相似性和差異性加以闡述,從而提出以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為目標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隱喻;認知;跨文化交際
中圖分類號:H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1-0210-02
前言
語際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之間的譯介與對話。隱喻現象作為語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最常用和最有力的認知世界、表述觀點與情感的手段。英國修辭學家里查茲曾(Richards)說過:“我們日常會話中幾乎每三句話中就有可能出現一個隱喻。”[1] 作為外語翻譯人才,能夠充分洞悉隱喻現象的認知異同,是在譯出語(source language)和譯入語(target language)之間進行準確、有效轉換,從而實現跨文化交際的前條件和成熟標志,因此翻譯教學必須引導學生加強對隱喻現象的語言及文化認知并進行實踐訓練,最終實現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一、隱喻概念的理論溯源
隱喻在西方自從20世紀70年代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開始興起了隱喻研究熱。隱喻,最初是作為修辭的手段提出的,它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修辭學》,他認為隱喻是一種修辭手段,主要用于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歌中想象方面的運用。所以作為修辭的隱喻是語言的一種附加和修飾而不是絕對的必需。而本文中的新視角下的隱喻卻是人們認識事物的一種普遍的認知手段和思維方式。人類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復雜,新生事物也越來越多,雖然詞典盡量為每種事物給出定義,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卻很少用詞典里的定義來解釋或理解尤其是一些抽象的事物,而且詞典也無法給它因不同經歷、不同感受所產生的不同涵義的全面解釋。因此隱喻成了人們有意無意都會用到的普遍的認識事物的一種手段,隱喻成為頭腦中的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
把隱喻作為認知過程較早地、成系統地進行研究的人應該是“相互作用理論”的創始人I.A.Richards(1936)。他認為:“人類認知體系是一個隱喻性的結構系統。為了深刻認識和理解周圍世界,人們本能地要尋求不同概念的相似點,從而創造隱喻,發展語言。”關于隱喻的概念,他提出:“當人們使用隱喻時,把表示兩個不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這兩個思想活躍地相互作用,其結果就是隱喻的意義”,并認為,隱喻是“人類語言無所不在的原理”(Richards,1936)。萊考夫和約翰遜也認為隱喻在日常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不但在語言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并提出“概念隱喻”和“跨概念域的對應理論”。他們認為:人們借助一個領域概念結構去理解另一個不同的領域概念結構,這就是隱喻的過程(Lakoff,G.&Johnson,1980)。
二、認知領域內的隱喻分析
(一)隱喻作為認知方式的形成過程
隱喻包含兩個組成部分,即本體和喻體(修辭概念),相當于Richards提出的要旨和媒介,以及Lakoff 和Johnson的目的域和源域。它們是分別來自不同的領域的兩個概念,說話人以獲得這兩個概念的相似點的聯想為基礎,把一個概念的顯著特征映射到另一概念上,實現語義轉移。也可以說是用一個領域的概念去解釋另一領域的概念。這是簡單的表面過程,但在人腦中的過程要比這復雜得多。在思維過程中不僅僅要考慮到找尋兩個不同領域的相似點,同時更少不了二者之間的差別在此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兩領域差別的前提下人的思維會主動地介入,讓不同的兩領域相互作用,從而發現或創造出二者的相似點及聯系。隱喻的形成過程包括說話者的大腦中的思維構建過程也包括聽者的大腦中的識別和推斷過程。雙方的思維過程不完全相同。如果說話者想要運用隱喻這一手段來表達某事物(本體),他首先要確定其對該事物的某一重大特征的理解和感悟,然后用自己所經歷的非常熟悉的、同本體有著極大相似點的另一事物(喻體)來表達,于是便產生了隱喻含義;對于聽者,這一過程要更為復雜一些,聽者在聽到最基本、最典型的A是B時,首先要確定的是喻體的可能含義值,然后要轉到主體上,觀察其當時的特征,之后再返回到喻體上去推斷并選擇最合適的一項或幾項語義可能值。在說話人的主觀認知參與下,雙方不斷地相互作用,最后完成隱喻的推斷和選擇。兩方面的隱喻形成和識別過程雖然復雜,但大腦的高級的運作機能會使其在瞬間內完成。
(二)通過對隱喻形成過程的分析,總結出隱喻形成的重要的“前提”和“條件”
1.“前提”是人類必須有關于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具體的、熟悉的、原始的經驗積累和概念積累,以此作為可供選擇的龐大的喻體語料庫。而且,按一般的規律,人類已有的積累是由具體、簡單、形象的較為低級的經驗和概念向抽象、復雜、高級的經驗和概念發展。因此,隱喻也通常是用熟悉的、簡單的、形象的事物來理解未知的、復雜的、抽象的事物,這一理解順序不能逆轉。請看下面的一組例句:
a.Life is a journey.
b.Life is a stage.
內涵豐富的概念“生活”用人們熟知的不同的事物來解釋和認識它的不同層面的含義,這是合理且合情的認知。而順序顛倒的隱喻,即,“A journey is life.”“ A stage is life.”“ 一團麻是生活。”作為隱喻是無法讓人理解和接受的。
2.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語境。現代語言學對于語言的研究是對使用中的、活的語言的研究,因此隱喻的形成和推理就離不開對語境的理解。語境就是隱喻產生過程中與說話者和聽者相關的主、客觀因素,如時間、地點、場合、文化歷史背景、個人的教育背景、心態、意圖、情緒等。上述“某人是豬”以及關于“生活”的各種隱喻,正是說話人對周圍世界及個人經歷的獨特理解和感悟所產生的,以及聽者根據當時語境的線索推斷出來的關于主體某一層面的特征。當然,語境對于不同隱喻的約束力的強度是不一樣的。endprint
三、人類文化對于隱喻認知的影響及翻譯策略
首先,由于人類作為生物界最高物種,有著共同的生存、發展規律,對自然界和自身的生理機制、心理因素有著共同的基本的認知和經歷,所以隱喻的認知具有一定共性。如,不同的英漢民族對太陽東升西落的事實卻有著共同的認知,因此隱喻“太陽從西邊出來”無論對操漢語的人還是操英語的人都表示“不可能發生”,因此從理解和翻譯策略上可以采取直譯法。類似的例子還有:英語習語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可以直接譯成漢語的習語“趁熱打鐵”;Put down in black and white譯成“白紙黑字寫下來”;Its good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直譯成“渾水摸魚”。
其次,隱喻在有著相同的文化認知的同時還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即民族性。就翻譯而言,對于隱喻的認知差異,譯者應準確地把握隱喻特點,選擇適當的翻譯方法,盡量縮小認知差異以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
首先,由于人類的生存自然環境不同,定居的區域分散,具體的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不同,導致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不同,因此,譯出語和譯入語之間會出現某些隱喻喻體的空缺,即,某一語言文化中常見事物,相對于其他文化來說卻是唯一的,這時不能采用直譯法,需要替換喻體,如漢語成語“班門弄斧”原意指在魯班門前舞弄斧頭,比喻指在行家面前賣弄本領,不自量力。可是魯班作為中國傳說中的人物,對于西方人來說,毫無意義,因此翻譯時需要改換為西方人熟知的喻體,如teach fish to swim,這樣即容易被西方文化所接受,又符合習語簡潔、富有智慧的語言要求。不過近年來,隨著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許多東西方文化獨特的負載意義已被彼此所熟知,這時可以用直譯法,例如:“crocodile tears”直譯為“鱷魚的眼淚”,中國讀者都能領會其含義,這樣不僅達到了交際目的,而且有利于文化交流。英語的“hippe”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社會文化的獨有產物,漢語沒有對應的詞語,故音譯為“嬉皮士”,漢語的“餃子”、“功夫”等分別音譯為“jiaozi”、“Kungfu”等。
其次,兩種文化雖然都存在相同的事物,但隱喻的文化認知卻是有著極大的差異,如馬和牛都是英漢民族所熟悉的家畜,但在英美等國,牛多用來產奶、食肉,而馬曾是主要的生產和運輸勞力;在農耕文化為主的漢文化中,黃牛和水牛是重要的犁地幫手,因此便有了含義相同、喻體卻不同的隱喻,所以翻譯時我們需要適當地喻體替換:He is a willing horse.——他俯首甘為孺子牛。 He likes talking horse.——他喜歡吹牛。另外關于狗的文化認知,東西方存在巨大差異:西方文化認為狗是人類的忠實朋友,愛護有加,因此英語中與狗有關的隱喻多為褒義,如You are a lucky dog.He worked like a dog.Love me,1ove my dog.而在中國人對狗沒有西方人那種情感,漢語中與狗有關的隱喻大多含有貶義,如走狗、喪家犬、狗仗人勢、狗急跳墻等。所以翻譯漢語時就不能再出現“狗”的字樣,反倒采取意譯或替換喻體會更加恰當,即,你真幸運;他工作很努力;愛屋及烏。
結語
隱喻作為一種認知手段和思維方式,它普遍存在而且必不可少。隱喻的文化認知的相似性表明各民族有能夠溝通和交往的基礎;而差異性或民族性,即體現了人類不同文化的豐富性,又說明各民族之間有互相了解和尊重的必要性。作為優秀的譯者,必須熟知目的語和源語的隱喻的文化認知,尤其是差異性,才能保證翻譯過程的準確、恰當,減少誤解和障礙,最終實現成功的跨文化交際。
參考文獻:
[1] Richards,L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2] 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 徐宜良.隱喻、認知與文化[J].安徽工業大學學報,2007,(1).
[4] 嚴世清.隱喻理論史探[J].外國語,1995,(5).
[5] 曹艷春.英漢隱喻認知對比研究與實踐[J].沈陽工程學院學報,2012,(4).
[6] 束定芳.隱喻學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 安世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