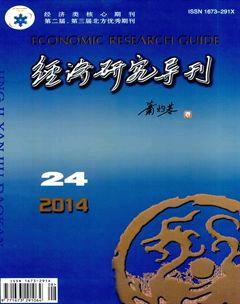論清末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轉型和啟示
陳昊
摘 要:在清末變法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傳統(tǒng)司法體制弊端重重,傳統(tǒng)經濟結構的解體和新教育新思潮的興起最終導致清末中國司法體制的劇烈轉型變革。清末司法體制的轉型變革既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又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總結其成敗得失將會給當前的司法體制改革以深刻的歷史啟示。
關鍵詞:清末;司法體制變革;啟示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4-0300-02
一、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歷史背景
(一)傳統(tǒng)司法體制的弊端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內在原因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所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顯示出巨大的優(yōu)越性,而中國固有的專制主義法制卻弊端重重,陳腐落后。通過研究對比對中西方法律制度,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清末時期司法制度曝露出極大的弊端,已經嚴重阻礙當時經濟社會發(fā)展,表現(xiàn)如下:第一,晚清司法體制司法不獨立,未設立獨立的司法機關,行政兼理司法致使審判不公,尤其刑名幕友助為審理,冤假錯案層出不窮;第二,審級繁多,審判權限混亂;刑部雖是最高審判機關,但往往也是行政權力的延伸和附屬;第三,民刑不分、實體與程序不分,沒有制定專門的訴訟法律和法院組織法來規(guī)定審判制度,以刑律包括所有的訴訟程序;第四,無確定的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兼管審查、逮捕和審判,刑訊逼供盛行。由此可見,中國傳統(tǒng)司法體制已經明顯地落后于時代,嚴重地妨礙了社會的發(fā)展。
(二)傳統(tǒng)經濟結構的解體和新教育新思潮的興起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外部條件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失敗以后,西方列強在經濟上加緊掠奪中國。一方面從中國輸入工業(yè)原料及勞動力,另一方面又以工業(yè)產品傾銷中國市場,使中國傳統(tǒng)手工業(yè)破產,清末傳統(tǒng)社會經濟結構逐漸解體,舊的司法體制所賴以生存的合法基礎逐漸動搖,同時為新的司法制度的誕生創(chuàng)造條件。伴隨著傳統(tǒng)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中國社會也開始發(fā)生由農本社會向現(xiàn)代工商社會的轉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在沿海地區(qū)緩慢而頑強地生長著,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近代工廠開始出現(xiàn),商業(yè)行會發(fā)展迅速。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逐步深入到晚清社會,傳統(tǒng)的生產生活方式和道德理想價值觀念漸漸為時代拋棄,新的西方法治思想理念越來越多地被國人所接受。傳統(tǒng)的司法體制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急劇變化的經濟關系和新的社會形態(tài)。
(三)治外法權的收回是司法體制變革的直接動力
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的門戶,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索取種種特權,其中就以領事裁判權為最。到19世紀60年代,領事裁判權的適用范圍越來越大,列強相繼取得觀審、會審以及會審公廨中的司法審判權,在中國出現(xiàn)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就外國之裁判”的反常現(xiàn)象,至此,中國的司法主權遭到了嚴重的踐踏。領事裁判權不僅削弱了中國的司法主權,而且使民教相仇,激起內外矛盾。帝國主義侵略國為了獲得更大的侵略利益拋出可以有條件地放棄治外法權的誘耳,1902年9月,中英續(xù)議《通商行船條約》,英國作出愿意撤廢領事裁判權的附條件承諾。領事裁判權猶如一把雙刃劍,在侵害中國司法主權的同時,也似一貼猛烈的催化劑,促使清政府在司法領域革故求新,從某種程度而言,列強允諾放棄領事裁判權成為晚清司法現(xiàn)代化的直接動因。
二、清末中國司法體制轉型的體現(xiàn)
(一)由傳統(tǒng)官審制向獨立審判制的轉型
中國傳統(tǒng)法制即是司法與行政不分,到了清朝末年,隨著先進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影響,清政府開始制定法律、頒布命令,以促使司法權與行政權相分離,實行司法獨立。一方面,廢除“三法司”制度,構建新的司法機構體系。1907年法部呈奏的《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草案》和1910年頒行的《法院編制法》對原有的司法機構做出了重大改革,設立審判衙門,實行四級三審制,初步形成司審判權和行政權相分離、審判權和檢察權相分離的局面,結束了中國長期的司法和行政不分的舊的司法體制。另一方面,加強對司法人員職業(yè)素質培養(yǎng),實施法官職業(yè)化道路。在清政府公布的《法官考試任用章程》等法律文件中,規(guī)定凡推事及檢察官都必須經過專業(yè)學習,首次考試合格后有一年的見習期,期滿后再進行第二次考試,這從制度上保障了司法人員的職業(yè)素質,為司法獨立原則的落實創(chuàng)造了“人”的條件。
(二)由控審不分向控審分離的轉型
清末政府仿照國外資本主義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體制,在各級審判機關內部設立檢察廳專門負責刑事案件的偵察和起訴。按照《大理院審判編制法》規(guī)定,審判機構內部分設總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地方檢察廳和初級檢察廳。作為一種司法審判的監(jiān)督和制約機關,它的出現(xiàn)和存在,開創(chuàng)了在中國司法體制上實行控審分離的先河。從此,資本主義的檢察制度在中國開始逐步建立。清末實行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檢察機關主要行使偵查起訴的職權,有權收受訴訟請求預審及公判,指揮司法警察官逮捕犯罪者,調查事實,匯集證據(jù)。另外,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還包括民事保護公益陳述意見,監(jiān)督審判并糾正其違誤,監(jiān)視判決至執(zhí)行,查核審判統(tǒng)計表等。
(三)由程序實體法不分、民刑不分向程序法的建立、民刑有別的轉型
中國傳統(tǒng)的訴訟審判機制無明確的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區(qū)分,訴訟制度往往混雜于刑律之中,且內容簡單、粗略,遠遠落后于世界各國。在清末變法過程中,沈家本通過考察和研究東西方各國的法律制度,提出首先要區(qū)分民訴、刑訴的主張。1906年,清政府頒布中國歷史上編訂了第一部訴訟法典草案:《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該法典草案吸收確立了律師制度、陪審員制度、證人制度和異財別籍等制度,并廢除了比附斷案的制度和刑訊逼供的制度。雖未區(qū)分刑事民事訴訟,但當時的這些舉措是對傳統(tǒng)法制進行的重大改革,是中國傳統(tǒng)法制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一大進步。后因仿行立憲的需要,又將訴訟法分為刑事、民事兩種。沈家本的主持下,1911年1月相繼編成《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以上兩部訴訟律草案上奏清廷未及核議頒行,清朝即被推翻,但其內容和體例,為后來民國時期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提供了參照的依據(jù)。
(四)由皇權無限向有限皇權的轉型
1905年清政府相繼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資政院院章》、《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等憲法性法律文件。《資政院院章》明確規(guī)定資政院是正式召開國會前的議會性質的機構,由“欽定議員”和“民選議員”組成,主要負責起草議決憲法、議決歲入歲出、預算決算、法典朝章、公債積率等。《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明文規(guī)定:皇帝權力以憲法規(guī)定者為限,皇帝繼承順序也以憲法規(guī)定,皇族不得擔任內閣成員,這些機構的出現(xiàn),至少是從形式上對至高無上的皇權進行了挑戰(zhàn),是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皇帝無限制權力的否定。清末法制改革過程中建立的以君主立憲為政體、以議院為立法機構、以選舉制和地方自治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雛形,在客觀上限制了專治皇權,在立法理念上實現(xiàn)了從皇權無限到皇權有限的轉型。
三、清末司法體制改革的歷史啟示
(一)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前提
首先,司法改革必須在政治改革的總體格局下進行。司法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改革制約和影響著司法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在一種腐敗的政治體制和制度下,試圖通過司法改革解決腐敗的問題,只會使新鮮的東西腐敗。其次,將司法改革作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是一種假象和錯覺。由于司法改革風險相對較小,清廷對此的限制較少,司法改革因此成為當時新政的重點。實際上,司法的救濟性、補償性功能決定了其只能是一種后繼性的改革,是從屬于經濟、政治等項改革之后的回應性改革。因此,在政治體制改革未進行或沒有結果之前,將司法改革作為改革之首是有悖邏輯因而也是難以奏效的。再次,法制并非萬能的。實踐表明,對于司法以外的問題,司法無能為力,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遠非修律和司法改革所能解決,而需借助司法以外的方法,因此,司法改革的完善和實施依賴于政治制度的更新。
(二)政府的推動是司法改革的保障
司法改革沒有政府的推動是難以進行的。首先,從立憲入手。在司法改革中,注意從憲法入手,通過立憲,確立司法改革的內容、原則、目標等,“以憲治國”。1906年,清廷發(fā)布了“仿行憲政”上諭,為立憲的進行開始改革官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司法改革。其次,通過部門法確立司法改革的具體內容。清廷不僅建立了系統(tǒng)的法律體系,而且制定了詳備的部門法和具體的法律條文。對司法機關的定位、職權配置、運作程序、相互關系等作出了全面的規(guī)定,以防權力借司法改革超越法律或濫用。對司法改革的情況予以公開。清末司法改革不僅見諸于頒布的法律,而且,從改革的整體設計到具體措施對社會的公開程度不可謂不高。經費的支持更是司法改革得以進行的經濟基礎,“一切院廳設備、官吏俸胥,無非出自公家”。清政府在財政及其困難的情況下,想方設法籌集經費用于新式司法機構的運轉,為清末司法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
(三)科學的理論是司法改革的指導
清末司法改革以“中體西用”為指導必然與傳統(tǒng)的封建禮教為核心的法制相沖突。1906 年,《刑事民事訴訟法》采用西方律師、陪審等制度,對此,各省督撫紛紛簽駁,責其“襲西俗產業(yè)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圣賢修齊之教”,該法因此胎死腹中。1907 年,《大清新刑律草案》又因“內亂罪不處唯一死刑”和“無和奸無夫婦女治罪明文”,被保守派攻擊敗壞禮教,蔑棄綱常。清末之時,雖然西方文化沖擊著中國,但封建專制的根基沒有被動搖,傳統(tǒng)的禮制和習俗依舊發(fā)揮著作用,并抵御外來的文化。上述禮法之爭中法理派的最終妥協(xié)表明,在舊有的倫常理念尚未破除,新的法制觀念尚未形成的情況下,新的規(guī)定雖然具有文明的浪漫,但也僅僅是一種浪漫,任何新制度的建立都意味著對統(tǒng)治者既有利益和制度的觸動。同時,它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清末司法改革對制度的革新比較重視,而對理論的更新不足。
[責任編輯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