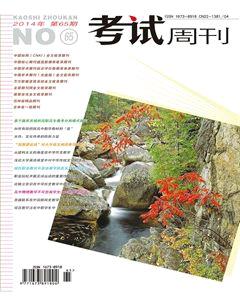“意圖謬誤說”對大學語文閱讀教學的啟示
楊清艷
摘 要: 新批評代表人物威姆薩特和比爾茲認為文學研究的對象是一種無作者的文學,提出了著名的“意圖謬誤說”。這一重要文論對大學語文閱讀教學有重要的啟示:在大學語文閱讀教學中避免進入“作者中心論”的理論誤區,引導學生進行個性化閱讀。
關鍵詞: 意圖謬誤說 大學語文閱讀教學 啟示
傳統大學語文閱讀教學方法往往以作者為中心,在引導學生閱讀一篇課文時,往往會先介紹作者情況、寫作背景,然后根據作者的創作意圖及生活背景理解作品的內容及意義。這樣的教學方法對學生理解文學作品不得不說是一個局限,值得認真思考。本文就“意圖謬誤說”對大學語文閱讀教學的啟示作簡要論述。
一、對“意圖謬誤說”理解
“意圖謬誤說”(intentional fallacy)是著名的新批評代表人物威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提出來的,他們認為:作品的意義與作者的意圖是兩碼事。研究作品,沒有必要研究作者,作品總是受到作家以外一些因素的制約,按作者的意圖或聲明確定作品的意義,便混淆詩和詩的來源,是“意圖謬誤”。所謂“意圖”,便是作者心目中的藍圖或計劃,“把作者的構思或意圖當作判斷文學藝術作品成功與否的標準:既不可行亦不足取”[1]。此理論的依據有三:“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找到的;其次,就是可以找到作者意圖的地方,如作者的直接陳述,意圖也不可能僅從表面價值上理解;最后,淺薄的作品較容易受作者的控制,而偉大的藝術往往超出作者主觀意圖的羈絆。像但丁、托爾斯泰那樣的大家盡管有意要宣揚一套宗教或道德的哲學,然而他們的作品恰恰沖破了意圖的束縛而成為偉大的藝術。他們反對將詩和詩的生產過程相混淆。”[2]新批評理論家堅決反對把文學作品的研究變成作家的傳記研究,把作品意義等同于作者的某種“意圖”。比爾茲利指出:讀者在理解作者所說的話時,也不知道作者真正想表達的是什么意思。例如:“比起我的妻子來,我更愛我的女秘書。”“你的意思是說你愛你的女秘書超過了對自己妻子的愛?”“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說與我老婆對我女秘書的愛相比,我對這位女秘書的愛更甚些。”講話人的意思與聽話人的理解往往會不一致。因此,把文學作品的意義等同于作者的創作意圖,文學作品將失去其審美的豐富性。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任何一件藝術品可能涉及的要素有四個,即世界、作品、藝術家和藝術欣賞者[3]。文學作品解讀中一直有一個以何者為中心的問題,通常讀者在解讀文學作品時,往往是先查一查作者的生平紀事,做到知人論事,希望有助于對作品的把握和理解。實際上,由于作者先入為主地進入讀者的大腦,在某種程度上會形成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讀者在欣賞文學作品時會受到作者思想或創作意圖的影響,無法有更多的想象和創造空間。過多地關注作者的創作意圖,勢必會走向“作者中心論”一端。所謂“作者中心論”,其最基本的觀點就是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是由作者賦予的,一部作品的意義,就是作者寄予作品的意義,而一種閱讀的理想形態,就是讀者在閱讀中“原封不動”地領會作者賦予作品的“意義”。這種所謂“作者中心論”其實可以分解出三層意思:其一,一部作品的意義總是由作者賦予的;其二,這個“意義”應當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其意義也就相應完成,它不會隨歷史、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換言之,一部作品總有一個獨立于理解之外、先于理解而存在的意義;其三,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僅是由作者賦予的,而且這個意義是獨一無二的,就是說,文學作品的意義只能來自作者,任何其他來源的意義都不具有合法性。總之,這種觀點帶有鮮明的“本質論”特點,就是它不考慮一個事物在形成過程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急切地把作者的“原意”想象成為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事實上,這種思想方法本身就帶有明顯的認識論的謬誤。受“作者中心論”的影響,在19世紀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西方的文學批評就是忙于在作品中尋找作者賦予其中的“原意”,在作者的出身、經歷與思想中尋找文學作品意義“真正”的源頭。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知人論世”表達了與西方“作者中心論”相似的看法[4]。
二、“意圖謬誤說”對大學語文閱讀教學的啟示
(一)在大學語文閱讀教學中避免進入“作者中心論”的理論誤區
在傳統語文教學中,教師往往要做到“知人論世”,在閱讀教學過程中,教師習慣以作者為中心、以作者所生活的社會歷史環境為中心理解文學作品。教師在給學生進行文學文本解讀的時候,通常先介紹,在了解作家的性格、生平經歷、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文學文本進行解讀。例如,在《長恨歌》教學中,教師會介紹作者的相關信息:首先是白居易先生的簡介,包括生平履歷、愛情婚姻、文學成就、代表作品、思想狀況等,其次是創作背景的介紹,《長恨歌》寫于公園806年,即唐憲宗元和元年,作者當時35歲,任周至縣尉。此詩是作者借對歷史人物的詠嘆寄托自己的情感之作。據說由于門第觀念和社會風尚的阻礙,詩人年輕時有過一段沒有結局的愛情,還在分手時寫了“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彼此甘心無后期”的沉痛詩句。《長恨歌》寫于作者婚前幾個月,詩人為有情人終不能成為眷屬而痛苦,“在天愿做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正是作者借前代帝妃的悲劇,抒發自己的痛苦與深情。由于老師再三強調,在解讀這首詩歌時,一定要和作者的生活經歷和寫作背景聯系起來,限制了學生的多維閱讀視野,學生的思想被限制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里。在解讀《長恨歌》的主題時,學生更多想到的是愛情主題,以愛情悲劇為主線分析,描寫帝妃的愛情悲劇,進而表現詩人感情的不幸遭遇。從這個角度解讀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這篇詩作的主題應該是多元的,例如歌頌愛情、諷刺荒淫、雙重主題說等。
又如,《荷塘月色》本來是一篇寫景的散文,事實上,由于受“作者中心論”的影響,學生很少關注作品中的景物描寫,即便關注,也必須把景物描寫和作者的某種感受、思想聯系起來,追求作者寫作的“原意”。即使有人認為,這篇散文中確實有作者寄予其中的某種思想、情緒或感受,確實有某種“原意”存在,它寓于作品中,就像一個案件的真相,值得研究者不懈地去追蹤。而實際上,按照西方現代文學理論的理解,這個所謂作者的“原意”根本就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幻象,是在“作者中心論”基礎上捏造出來的一個思想的“烏托邦”[5]。因此,在大學語文閱讀教學中,應該放棄傳統的“作者中心論”,從單一的追尋作者“意圖”的模式中解脫出來,將對作品的解讀變成一種真正的文學鑒賞活動。endprint
(二)引導學生進行個性化閱讀
個性化閱讀,即學生進行自主性閱讀,這是學生進行自主實踐的一個活動,在不受干擾的狀態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探索,從閱讀中汲取自己需要的養分。在閱讀的同時,學生和作者產生思想上的碰撞,可以自由地抒發感受,大膽發表感想和見解。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要取代學生的主體地位,應該讓學生積極地思考,根據自己的想法分析和把握作品。學生的自主活動是真正的閱讀活動開展的前提和重要因素。在閱讀過程中,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思想、文化素養、生活閱歷及審美情趣對文本進行自我解讀,重新構建作品。在文學作品中,學生閱讀文本,根據自己的思想深度、文化水準、人生經驗、審美水平對文本進行個性化解讀,對作品進行重新構建。與此同時,閱讀作品中還包含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作品之中還有很大思考空間,學生可以在閱讀中將自己的感悟融入作品中,根據個性進行創造性的填補。例如,在《荷塘月色》中,“裊娜”的解釋在詞典中為細長柔軟,有讀者在閱讀時腦海中會浮現出少女翩翩起舞的形象,也有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想到楊柳依依的形象。因此,不同的讀者,由于生活經驗及文化素養不同,閱讀之后所產生的創造性的理解有所差異。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道:“誠實的批評和敏感的鑒賞,并不注意詩人,而注意詩。”艾略特認為用藝術形式表達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套客觀物,一個場景,一串事件”,當它們呈現出來時,相應的“感情立即被激起”。他要求把批評者的目光引向文本呈現的物體,而不是作者的意圖,讓其更自由地實現審美的豐富性。即,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應該有獨特的體驗,而不是把作品的一切意義都看成是作者的創作意圖。
在大學語文閱讀教學中,不應該一味追求作者的創作意圖。傳統語文閱讀教學,教師在引導學生閱讀文學作品時,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課文背景的講述、作者的生平介紹及繁復的課文分析上,導致學生自主閱讀的時間少之又少。相對高中生而言,大學生有更多的時間、空間,有更豐富的生活體驗,不受教學大綱的限制和升學考試壓力的影響,因此,教師可以利用這些優勢,在閱讀教學中引導學生從多角度理解文學作品。作家通過某一文本表達思想的時候,對文本的理解,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看法。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是文本與讀者互動的產物,單一的文本僅僅是一種召喚結構,是一個物理層面上的印刷品,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必須經過閱讀才能實現,文學作品的意義是讀者在文本的基礎上通過閱讀實現的。正如伊瑟爾所說:“一部藝術作品需要一個外在于它的動因,這就是一位觀賞者。……藝術作品是藝術家有目的活動的產品,作品的‘具體化不僅是觀賞者進行的‘重建活動,也是作品本身的完成及潛在要素的實現。所以,從某種角度來看,作品是藝術家和觀賞者的共同產品。”在大學生積累一定量的閱讀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完全有必要進行個性化閱讀。
語文閱讀教學的任務不應是只規范學生思維,而應把先進的思想滲透給學生,培養學生創造性理解和掌握先進的思想,使之認識紛繁復雜的社會、透視形形色色的人生;教給鑒賞和創作文學作品的基本方法,培養學生初步的文學鑒賞能力乃至文學創作的能力;引領學生感悟文本語言魅力,培養學生創造性掌握和運用語言工具的能力。“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強調的是閱讀的個性差異。教師應該充分注重學生的主體性,根據學生的閱讀基礎留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引導他們正確閱讀,幫助他們提高閱讀水平。
參考文獻:
[1]568W.K.威姆薩特.M.C.比爾茲利.意圖說的謬誤[M].戴維·洛奇編.20世紀文學評論(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2]林樹明.意圖謬誤說與性別創作主體[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2).
[3][美]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M].北京大學出版社,1953.
[4][5]張衛中.《荷塘月色》解讀中的“意圖謬誤”[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