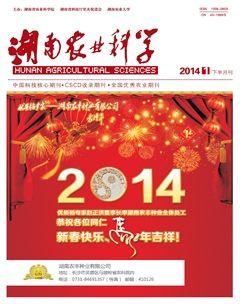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差異及其影響因素
陶姝沅 李瓊 林敏
摘 ? 要:選取1995、2000、2005、2010年4 個代表年份浙江省69個縣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截面數據對浙江省農民收入空間格局變化,進行了縣域尺度上的空間自相關分析,同時確定驅動農民收入分異的主要因素。結果表明:①1995~2010年,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差異逐漸減少,空間自相關性逐漸增強,低收入縣區和高收入縣區均呈現出空間聚集態勢。具體表現為低收入縣區在浙江西南部聚集,而高收入縣區在浙江東北部聚集。②自然環境、經濟地理區位條件和對外開放程度是影響浙江農民收入空間格局變化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農民收入;區域差異;空間自相關;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0X(2014)02-0085-03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come of Peasa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AO Shu-yuan, LI Qiong, LIN Min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PRC)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 data of per capita pure income of peasants in 69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1995, 2000, 2005 and 2000,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in income of peasa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t county level; meanwhil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income of peasants had been determin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From 1995 to 2010,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come of peasa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reduced gradually, and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gradually strengthened, so the low-income counties and high-income counties tended to a trend of spatial aggregation, which expressed as low-income counties gathered in southwest Zhejiang, and high-income counties gathered in the northeast. (2)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conomic geography conditions, industrial and urban-rural structures, and opening degree we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changes in spatial pattern of peasants income in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 income of peasants; regional differenc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當前我國農村人口仍占到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這部分群體的收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是實現我國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1]。農民收入水平受到歷史、自然環境、人口狀況、產業結構、政策管理和經濟文化等眾多要素的影響,但這些要素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不同區域農村居民收入的差異[2]。區域發展不均衡導致農村居民收入差異越來越顯著,因此受到越來越多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國內外學者采用多種指標和方法對我國農民收入的差異程度、演變趨勢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指出我國農民收入地區間的差距在不斷擴大[3-4],改革與發展諸多因素交織作用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而增加非農的就業利于減少農村貧困,縮小收入差距。國內學者主要從收入結構的視角探討地區間農民收入區域差異的演變及構成。從區域尺度看,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對省際間農民收入差異格局的分析,少有對省內縣市間農民收入區域差異及影響因素的探討[5];從研究方法看,多采用數理統計方法從來源結構和區域結構對農民收入差異格局進行解析,鮮有綜合運用數理統計和空間統計分析對農民收入格局的時空演變進行研究。因此,以浙江省為研究對象,選取1995、2000、2005、2010年4 a浙江省69個縣區農民人均純收入截面數據,綜合采用空間自相關方法,研究了浙江省縣域農民收入的區域格局及演變態勢并深入剖析其影響因素。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資料來源
數據均源于《浙江統計年鑒(1996、2001、2006、2011年)》和《浙江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空間分析尺度使用的是浙江省69個縣市行政區劃,縣域行政邊界數據取自《浙江省地圖集2010》中的政區圖,經掃描后進行跟蹤矢量化得到。
1.2 研究方法
空間自相關分析可檢驗某一要素屬性值與其相鄰空間要素上的屬性值是否顯著關聯,用來發現空間的異質性和空間聚集,包括全局自相關和局部自相關。全局空間自相關中Moran指數是用來度量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標。全局空間自相關忽略了空間過程的潛在不穩定問題,為了研究是否存在觀測值的高值或低值的局部空間集聚,采用局部空間自相關可掌握空間異質性特征。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包括3種: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G統計、Moran散點圖。本文選用LISA和Moran散點圖這兩種方法。對于Moran指數可以用標準化統計量Z來檢驗,z(d)=[I(d)-E(I)]/。有關空間自相關的研究較多,計算公式如下[6-8]:
Global Marans I指數:
(1)
Local MoranI 指數:
(2)
2 結果與分析
2.1 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差異變化分析
1995年以來,浙江農民收入增長取得了進步。從全省平均水平看,1995年該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僅2 966元,到2010年已達到11 303元,是1995年的3.81倍。在收入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地區差異在不斷變小。從絕對總量看,199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嵊泗縣為4 658元,是收入最低的慶元縣(676元)的6.89倍;而到2010年,收入最高的為紹興縣,達16 685元,是最低的泰順縣(6 010元)的2.78倍。從變異系數的角度看,1995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變異系數為33.67%,2000年減少到33.05%,2005年減少到29.27%,2010年更是降到了28.71%,在15 a間變異系數絕對水平減少了4.96個百分點,農民收入的區域差異呈縮小態勢。為更好地考察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格局變化規律,引入空間相關分析。
2.1.1 全域空間自相關分析 為了進一步了解浙江省10 a間農民收入的區域差異及其空間演變,基于ArcGIS、GeoDA等軟件,對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4個代表年份的浙江省鄉村收入截面數據做全局Morans I統計檢驗,結果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4 a的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Global Morans I指數均在0.65以上,Z值也都在0.05以上,存在顯著空間自相關。表明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存在顯著的、正的空間自相關特征,即各縣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空間分布并不是完全的隨機分布,相反地表現出相似的觀測值趨于空間集聚,具有較強的空間異質性。從整體上講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存在空間上明顯的集聚現象,且這種集聚趨勢還在逐步增強。區域間存在收入水平高值和低值集聚分布的現象。
2.1.2 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 全域自相關只能從總體上來表現研究區域各單元的聚集情況,但它所反映的空間聚集格局并未經過顯著性檢驗,因此采用局域自相關分析做深入分析。采用GeoDA軟件,計算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Local Morans I值及其顯著性,利用Arcgis9.3繪制縣域尺度上的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空間分異狀態的Moran散點圖(圖1)和LISA集聚圖(圖2)。
由圖1可知:(1)整體上看:1995~2010年全域Moran值由0.612下降到0.566后上升到0.716,,呈波動上升的趨勢,表明15 a間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在全省尺度上存在明顯的空間自相關,且自相關程度不斷提高。具體表現為圖中第1和第3象限高-高聚集縣區和低-低聚集縣區數量上的變化,即農民收入水平高的縣區和低的縣區均趨向于空間上的集中分布。(2)從第1象限(高-高聚集地區)變化看,1995年,該象限的32個縣區主要聚集在浙江的東北地區,錢塘江兩岸以及太湖周邊的格局,從2000年開始向南邊紹興地區和東邊舟山地區拓展,但是該象限的縣區個數沒有明顯的變化,一直保持在30個。(3)從第3象限(低-低聚集地區)看,1995年5個縣區主要集中在浙江的西南地區,2000年增加到8個,2005年減少到7個,2010年減少到6個,范圍仍然集中在西南地區。
基于正態分布假設檢驗的全局空間自相關和LISA相對應,結果更具穩定性,由此得到浙江省1995、2000、2005、2010年縣域尺度上局域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分布圖,圖中LL部分表示低-低聚集區域,HH部分表示高-高聚集區域。
由圖2可知:(1)高-高聚集區域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浙江農民收入保持穩定且呈現出高度集聚的空間特征,主要分布在東北部的杭州、寧波、紹興和嘉興等縣區,長期以來是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快速發展,浙江塊狀經濟模式取得顯著成效,使農民受益匪淺。隨著時間的推進,這些縣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相繼變高,使該地區的聚集度越來越高。(2)農民收入低-低聚集地區集中在麗水、衢州等地區。自1995年該地區的縣區個數沒有大變化,該地區落后的局面未改變。由于地形的原因,杭州等長三角城市對該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有限,該地區經濟發展基礎條件差,工業化水平低。(3)低-高聚集地區重要分布在東南和西北地區。舟山及附近地區發生了波動性增長,進入高-高聚集地區。自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地區開始“溫州模式”,經濟日趨增強;隨著臺州、舟山縣區出臺各種政策,以及高速公路、高鐵的建設,東北地區的縣市對該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逐步增強。富陽、臨安因為歸入杭州的行政版圖,受到杭州的帶動作用退出該類型進入高-高聚集地區的范圍。(4)從各類型區的分布看,浙江省農民收入水平空間格局大體上呈現自東北向西南遞減的空間格局,各類型區在空間上集聚分布態勢,南北兩極分化趨勢依然顯著。
綜上所述,浙江省農民收入不僅存在區域分異,而且存在空間關聯,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以高-高、低-低聚集為關聯類型的縣區在區域上呈現聚集形態。這說明浙江省各縣市農民收入水平在空間上并非是隨機分布,而是呈現一定的規律,表現為以空間鄰近為基礎的同類型聚集的空間格局,并且這種集聚的空間格局呈現增強態勢。
2.2 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分異影響因素
已有研究指出,自然地理環境、資源要素稟賦、經濟地理區位、社會經濟結構、政策因素及外部環境等均會造成農民的收入差異[9],對浙江而言,自然地理環境存在不同,農業生產條件相差大,因此下文主要從自然環境、經濟地理區位條件和對外開放等方面分析其對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差異時空格局的影響。
2.2.1 自然環境條件 浙江省的地形特征是西南部以山地丘陵為主,東北部以平原為主,地勢呈西南高東北低。這與農民收入的低-低區與高-高區的分布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自然環境對農民收入的區域格局存在一定的影響。
2.2.2 經濟地理區位條件 農業收入在收入來源中的比重逐漸降低,非農收入逐步成為浙江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民的非農就業是影響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10]。靠近中心城市的距離越近,非農就業的機會就越大,工資在收入中的比例就越高。浙江東北地區是浙江省經濟發達、城市化水平高,鄰近我國經濟中心上海,極大地促進了該地區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較高;而西南地區城市化水平低,經濟欠發達,城市輻射農村的功能較小,制約了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較低。
2.2.3 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 改革開發以來,長三角成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浙江東北地區因完善的基礎設施、雄厚的經濟基礎、發達的公路交通網絡和便利的出海條件、較高的科技創新能力及熟練的勞動力等,對外資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該地區的農村人口就業,工資性收入增加。而浙江西南地區遠離海洋,地理區位條件差,外資投入少,農民的非農業收入較低。
3 小結與討論
采用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對浙江省農民收入空間格局變化進行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農民收入格局演變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浙江省農民收入區域絕對差異呈迅速增大的趨勢,而相對差異緩慢減小;從全局來看:農民收入呈高度空間正相關,收入水平相似的地區在空間上集聚分布,農民收入高的在浙江的東北地區聚集,而收入低的在西南地區集聚;從局部來看,農民收入與區域經濟,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自然地形表現出較強的空間耦合特征。
對于農民收入水平較高的浙江東北地區應繼續發揮區位條件和經濟實力強的優勢,充分依托大中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統籌城鄉發展,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帶動周邊農村發展;農村地區應當開發面向城市的特色旅游,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增加農民的非農經營收入;加快推進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
浙中和浙西南地區應積極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深入推進對外開放和產業園區建設,加快推進縣域產業結構升級,改善務工環境,發揮縣域經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帶動作用;依托浙中和西南地區豐富的旅游資源,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此外,推動農業商品化,加快實現農業規模化、產業化和現代化,提高農業附加值,增加農民的農業經營性收入。
參考文獻:
[1] 劉純陽. 農民收入區域差異及其原因分析[J]. 科技導報,2004,(5):28-30.
[2] 胡 兵,喬 晶. 農民收入區域差異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與判斷[J]. 社會科學研究,2005,(5):76-80.
[3] 陳英乾. 中國農民收人的地區性差異及對比分析[J]. 農村經濟,2004,(12):68-70.
[4] Gustafsson B Li.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9):179 - 204.
[5] 杜姍姍,蔡建明,劉彥隨. 河南省縣域農民純收入增長差異及其演進格局分析[J]. 經濟地理,2010,30(12):2091-2096.
[6] 徐建華. 計量地理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20-126.
[7] 靳 誠,陸玉麒. 基于縣域單元的江蘇省經濟空間格局演化[J]. 地理學報,2009,64(6):713-724.
[8] 姜海寧,谷人旭,李廣斌. 中國制造業企業500 強總部空間格局及區位選擇[J]. 經濟地理,2011,31(10):1666-1673
[9] Wan G,Zhou Z.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using household data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9(1):107-120.
[10] 孫 虎,劉彥隨. 山東鄉村居民收入地域差異及其形成機制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1,30(2):69-72.
(責任編輯:盧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