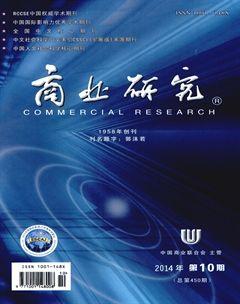智力資本意蘊:認知派與行為派的論爭
?だ罹?路
摘要:本文從哲學的本體論角度來探索智力資本概念,并在探析智力資本與智力資產之間關系的基礎上,著重在智力資本的構成因素、智力資本的運作、智力資本與企業價值的關聯程度以及智力資本轉化為企業價值方面對比分析認知派和行為派兩種流派的不同觀點,認為行為派將智力資本理解成為一個表征概念比認知派將其理解為先驗模型更為合理,其關于智力資本如何運作以及智力資本怎樣轉化為企業價值的研究更有意義。
關鍵詞:智力資本;本體論;認知派;行為派
中圖分類號:F234文獻標識碼:A
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和知識越來越成為影響企業利潤、決定企業存在的重要變量,已成為企業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Tseng and Goo,2005)。作為異質性的企業,智力資本是其核心競爭力的載體(李經路,2014)。大多學者認為智力資本有三個要素: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表現為員工擁有的知識、技能、經驗、工作動機等;結構資本(structural capital)表現為組織的方法、能力、慣例、程序等因素;關系資本(relational capital)是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供應商、中間商、競爭者、政府機構、員工等)為了實現其目標而建立、維持與發展關系并進行投資所形成的資本或者關系價值。
一、智力資本與智力資產的關系
與智力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簡稱IC)相近的還有一個智力資產(Intellectual Assets,簡稱IAs)概念,這兩個概念僅有一字之差,在使用時經常出現互換的混用現象(Andriessen,2004)。本文認為有必要界定其外延,以框定其范圍。兩個概念的區別在于“資本”與“資產”的本質區別。智力資產是現在或者未來能夠產生現金流的資源(Berle and Means,1991;Manton,2006);智力資本表現為組織的一種潛能,由智力資產轉化而來(Bounfour and Edvisson,2005)。如果智力資產能有效利用并帶來更多財富(未來經濟利益),那么智力資產就轉化為了智力資本。智力資本(IC)是企業或者組織所擁有或控制的資本,表現為組織的知識或者組織的集體能力(collective ability),該能力是組織通過學習,將組織知識轉化為組織行為(organization action )而形成的(Reinhardt et al.,2001;Roos et al.,1997)。
資產要帶來預期經濟利益,必須依賴資產主體擁有的智慧水平,因而從邏輯上講,資產只是未來經濟利益產生的必要條件,而資產擁有主體的智慧水平則是資產產生未來經濟利益的充分條件,二者缺一不可。這就說明投資者為什么愿意把資產投向有前途的企業,尤其愿意向每股市價高于每股賬面價值的企業進行投資,因為他們相信智力資本將創造出較高的價值①。由此可知,智力資本是一個動態概念,強調通過運行而逐漸積累價值的過程,更加關注企業(組織)中的運營與管理;智力資產是個靜態概念,它并不一定就是智力資本,只有投入到企業生產運營中并具有流動性和增值性的智力資產才能轉化為智力資本。這表明智力資產的外延大于智力資本的外延。智力資本與智力資產之間的邏輯關系如圖1所示。
在圖1中,智力資本對應著智力資產的幾部分內容,它們分別是商標價值、知識產權價值、創新組合價值、組織資源價值、人力資源價值、顧客價值、伙伴價值等構成要素。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智力資本與智力資產的關系上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但在智力資本本體論方面的認識上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二、認知派和行為派的理論分歧
雖然智力資本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進展,但是智力資本本體論(ontological proposition for the IC)認識的局限性還依舊是智力資本理論發展的羈絆,如果能從本體論中解脫出來,那么智力資本理論將得到較快地發展。下文以本體論的視角對比了智力資本的兩種流派——認知派和行為派的探究分歧,認為行為派能夠進行細致入微的探索,考慮了智力資本參與組織的復雜情況,為智力資本過程導向的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礎,但是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
目前智力資本還沒有穩定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范式,這種狀況對于智力資本管理、智力資本報告都是不利的(Abeysekera,2006; Bontis, 2001; Canibano et al., 2000; Petty and Guthrie,2000;Roslender and Fincham,2001、2003)。Marr et al.(2003)在對智力資本研究狀況的全面回顧和深刻反思后,指出現有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智力資本理論研究缺乏嚴謹性;二是智力資本研究的重點應是測度智力資本如何驅動企業的績效,但大多研究仍處在理論構建階段,理論很少得到計量驗證。如果研究者不能檢驗他們所提出的理論,不能深度挖掘理論或者構建理論,智力資本研究可能面臨失信的危險,我們也將不能超越現在的研究狀況——僅假設智力資本測度是值得研究的這一階段。
在此背景下,Marr 、Andriessen和Bontis率先關注智力資本研究連貫性和質量問題。Andriessen (2004)指出“一些主要的研究者是實戰家而不是科研人員”,言外之意,現有研究很有必要澄清智力資本觀念,探析智力資本的投資動機和探討智力資本的研究方法;智力資本有待深度挖掘,而不是僅停留于表面的探索。簡言之,當前智力資本定義不夠深刻,智力資本運營機理的認識簡單化了,有待深入研究,但因智力資本與實務之間復雜深奧的關系,智力資本的研究擱置了。相比而言,智力資本的規范研究比較冷清,而智力資本的實證研究較為熱火。實證研究是有貢獻的,但實證研究能超越所有認為智力資本值得測度的假設嗎?實證研究能夠驗證智力資本構成要素如何貢獻其財務價值嗎?實證研究假定企業智力資本三因素與組織決策或者與企業市場行為具有穩定的關系,但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關系尚無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