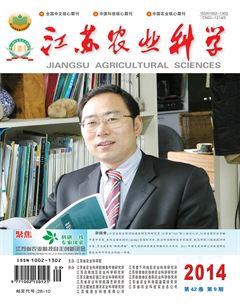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知和心態分析及政策啟示
陳品
摘要:采用問卷調查法調查了江蘇省淮北地區的東海、泗洪、響水和阜寧等4縣476位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知和心態,結果表明,一半以上被調查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識比較片面,近2/3被調查農民進行種植結構調整的原因主要是來自外部的影響;對種植結構調整有信心的只有1/4左右;面對種植結構調整中的市場風險近1/2的被調查農民選擇徘徊觀望,被調查農民普遍認識到市場和技術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的重要作用,渴望政府能加強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建設和協調農產品銷售。
關鍵詞:種植結構調整;農民;認知;心態
中圖分類號: F304.5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2-1302(2014)09-0482-02
調整和優化種植結構始終是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內容。進一步促進我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是多年來各級政府和農民尤為關心的問題,但要避免政府的盲目引導就必須弄清影響種植結構調整的主要決定因素。對種植結構變化的決定因素,人們在宏觀層面上認識比較一致,認為國內外市場需求或價格、各種作物的相對比較優勢和國家支持政策等因素是影響種植業生產結構調整的主要因素[1]。在微觀層面上,人們對基層村莊和農戶的種植結構調整的決定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地理區位[2]、市場基礎設施和交通設施[1,3]、土地細碎化[4]、農民素質[5-6]等視角,而對種植結構調整的主體——農民自身的認知、心態與行為的研究相對較少。農民種植行為的選擇與調整是種植結構調整的微觀基礎[5,7],研究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知和心態對于揭示種植結構調整的微觀機制、制定區域種植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1材料與方法
江蘇省淮北地區是我國東部沿海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和種植結構調整潛力相對較大的地區。為把握該地區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知和心態,推進該區域種植結構的科學調整,選擇了該地區的東海、泗洪、響水和阜寧等4縣種植業生產的農民進行實地問卷調查。調查內容主要包括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識、農民如何進行種植結構調整和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的期盼等。調查有效問卷為476份,其中東海縣131份、泗洪縣110份、響水縣128份、阜寧縣107份。
2結果與分析
2.1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知分析
48.74%的被調查農民認為種植結構調整就是大力發展一個地區的特色產業,表明大多數農民對于種植結構有較深的認識,能夠正確理解種植結構的含義,但也有部分農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比較膚淺,8.40%的認為種植結構調整就是政府號召種什么就種什么,20.16%的認為種植結構調整就是市場上什么好賣就種什么,15.13%的認為種植結構調整就是少種糧食,多種瓜果蔬菜,甚至有7.56%的認為種植結構調整就是鄉村干部窮折騰,搞表面文章。
56.72%的被調查農民認為種植結構調整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市場,39.92%的農民認為關鍵在于技術,表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通過近幾年種植結構調整的實踐,大部分農民已體會到市場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的重要性,在他們心目中市場因素的重要性已經超過技術因素。
經多年結構調整的實踐,65.13%的被調查農民體會到種植結構調整需要自己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有效結合,而只有14.71%、12.60%的被調查農民認為主要靠自己的努力或政府的支持。進一步分析發現,選擇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努力與政府的支持相結合”的基本是文化水平較高或能力較強的農民,選擇主要靠“政府的支持”和“說不清楚”的農民往往是文化水平較低或者能力較弱的農民。
當農民被問及“你對當前自家種植結構滿意嗎?”時,回答“滿意”和“基本滿意”的分別占13.44%和45.38%,合計為58.82%。對當前自家種植結構滿意和基本滿意的農民中,67.86%的被調查農民進行了種植結構的調整后感到滿意或基本滿意,32.14%的被調查農民并沒有進行實質性的結構調整而對傳統的種植結構表示滿意。回答“不滿意”的占4118%,對當前自家種植 結構不滿意的農民中,93.88%的被調查農民不知道如何進行調整,而只有6.12%的被調查農民近期準備調整。在對當前種植結構不滿意的196位農民調查發現,只有25.51%的被調查農民對種植結構的調整有信心,而選擇“沒有信心”或“說不清楚”的分別為28.58%和45.91%。
2.2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意愿分析
當農民被問及“你是怎樣對種植結構進行調整的?”,選擇“減少了旱地作物種植面積,發展水稻”的為53.78%,主要由于水稻近年來種植效益相對較高,隨著農田水利條件的改善,農民選擇了“旱改水”;選擇“增加了瓜果、蔬菜的種植面積”占42.86%;選擇“種植稀罕作物”占7.98%;選擇“挖田種植水生植物、養殖水產”為10.50%,主要由于近年來淺水藕等水生植物種植和水產養殖的比較效益較高,農民將一些原來的低洼地和部分水稻田進行開挖整理而“退耕還水”。
36.97%的被調查農民由于目前的種植結構效益差,自己探索,從而開展了種植結構的調整;30.25%的被調查農民由于政府號召而調整種植結構,表明政府在種植結構調整中做了一定有效的宣傳、引導工作;26.05%的被調查農民看到別人調整的效果好后跟著調整,只有6.72%的被調查農民從報紙、電視和廣播中得到消息后調整,反映了充分利用媒體來宣傳并引導農民進行種植結構調整具有較大的潛力。
當被問及“在安排作物時,你首先考慮的因素是什么?”時,44.53%的被調查農民回答是自家生活需要,而首先考慮市場行情的為32.77%,這表明被調查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確保口糧的自給仍然是一個主要目標。
當被問及“如果去年市場上的西瓜是1元/kg,今年你家種了西瓜,但今年西瓜只有0.2元/kg,種西瓜還不如種水稻收入高,明年你還打算種西瓜嗎?”時,回答打算先出去跑跑看看行情,看能否找到銷路,到時再作決定的占30.25%,這部分農民已經比較理性和主動;但也有21.01%的回答不種了,還是種水稻保險一點,這部分農民在結構調整的風險面前,膽子較小,自信心不足;回答繼續種香一年臭一年嘛,估計明年價格還會漲上去和再種一年看看的分別占2521%和21.01%,這反映了農民在調整種植結構中與市場進行初步博弈后所表現出的觀望心理。
2.3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的期盼分析
61.34%的被調查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最需要得到的服務是機械化或省力的種植技術,50.42%最需要技術培訓,47.05%最需要農產品營銷信息,這些結果基本符合該地區當前結構調整中農民的實際心態。隨著該地區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加快,在農村直接務農的中青壯年勞動力日趨減少,機械化或省工省力的種植技術成為農民在發展種植業過程中最需要的技術,而仍滯留在農村的農民,有著強烈的致富渴望,希望能種上新的作物,增加家庭收入,相應地迫切需要生產新技術培訓和產品銷售等方面的服務。
在回答“在種植結構調整中,你希望政府干什么?”時,71.43%的被調查農民選擇了協調農產品銷售和希望政府健全農業技術服務體系的占59.66%,希望聯系專家到農村指導的為43.69%,希望政府辦好種植結構示范點的為1932%,這同樣反映了農民在結構調整中對先進的農業技術、可靠的市場信息和廣闊的產后銷路的迫切需求。
綜上發現:(1)經過多年來的種植結構調整,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識有了提高,近一半的被調查農民認為種植結構調整就是發展一個地區的特色產業,但不容樂觀的是還有一半以上的被調查農民對種植結構調整的認識比較片面;(2)近2/3被調查農民進行種植結構調整的原因主要是來自外部的影響,如政府的號召、樣板的示范以及媒體的介紹等等,只有1/3的農民是自己主動探索而進行調整的,對種植結構調整有信心的只有1/4左右;(3)面對種植結構調整中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收益風險,近1/3的被調查農民能主動而又理性地面對,1/5左右的被調查農民小心退縮,近1/2的被調查農民徘徊觀望;(4)被調查農民普遍認識到市場和技術在結構調整中的關鍵作用,他們中絕大多數目前在結構調整中最需要得到的服務也是技術和市場,他們渴望政府能協調農產品的銷售和加強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建設。
3討論
我國自1999年開始啟動了包括種植結構調整在內的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十多年來各地在具體操作上有一些值得思考甚至需要反思的地方。在對實踐的深刻反思中,逐漸意識到農民心態的轉變是種植結構調整的關鍵[8]。調整種植結構,在不少地方被簡單地理解為增加或削減某些作物的種植面積,而忽視了農民這一最重要的“慢變量”在調整中的主體作用。因而,在種植結構調整中更多是直接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而忽略了如何為調整主體農民創造條件[9]。我國農民素質較低特別是市場經濟意識薄弱和農民組織化程度等客觀現實,決定了種植結構調整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目前,人們普遍認同并強調了我國種植結構調整所面臨的資源和市場兩大約束,但對農民素質約束的認識還不夠到位。
由于我國農業長期處于封閉狀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思想根深蒂固,建國后長期的計劃經濟思維與農民求穩的心態結合成了一種僵化的種植習慣。因此,種植結構調整的核心不是作物種植種類和面積調整,而是農民的認知、心態和能力的調整。調查結果啟示,當前各級政府和部門要進一步加強種植結構調整的宣傳引導和服務支持,特別要加強農產品銷售和農業技術推廣等服務體系的建設,為發揮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當前江蘇省淮北地區農民在種植結構調整中的心態表現出“多態性”,大體上可分為自主型(積極主動地進行調整)、跟隨型(根據行政指令或者跟在其他人后面,沒有自己的主見)、徘徊型(想調又不敢調,不知如何調)和保守型(沿襲種植習慣不調整)等四種類型。因此,各地引導和促進種植結構調整的措施不能一刀切,需要針對不同農民的心態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采取有針對性的引導和服務措施。只有實實在在地重視農民的主體性,認識到種植結構調整的根本前提是農民心態的調整和能力的轉變與提高,才能因“農民”制宜地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從而更好地發揮種植結構調整在我國現代農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黃季焜,牛先芳,智華勇,等. 蔬菜生產和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因素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2007,28(7):4-10.
[2]劉良燦. 試析杜能的區位理論在我國農村城鎮化建設中的應用[J]. 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3(1):120-122.
[3]董曉霞,黃季焜,Rozelle S,等. 地理區位、交通基礎設施與種植業結構調整研究[J]. 管理世界,2006(9):59-63,79.
[4]劉乃全,劉學華.學界動態勞動力流動、農業種植結構調整與糧食安全——基于“良田種樹風”的一個分析[J]. 南方經濟,2009(6):15-24.
[5]王娟,吳普特,王玉寶,等. 農戶對節水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意愿的量化分析——以黑河干流中游為例[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2,20(8):1105-1112.
[6]張玉啟,張文霞,陳國惠. 種植制度調整與農民增收問題的調查分析和政策建議——以對豫東地區種植結構調整的調查為例[J]. 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4):55-59.
[7]熊曉山,謝德體,宋光煜. 基于參與性調查的農業結構調整中小農戶種植行為的選擇與調控[J]. 中國農學通報,2006,22(3):430-434.
[8]黃毅.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重在調整農民心態[J]. 老區建設,2001(4):43-44.
[9]黃祖輝,胡豹,黃莉莉. 誰是農業結構調整的主體? [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張水玲. 外源推動與內源驅動整合:農業科技推廣模式創新機制研究[J]. 江蘇農業科學,2014,42(9):484-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