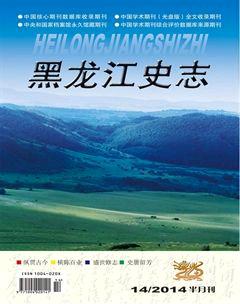論莎士比亞戲劇中李爾王的形象
[摘 要]通過多方面不同角度的分析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的《李爾王》中主要人物李爾的形象,探討李爾作為君主和父親雙重身份的豐富形象內涵,并結合情節的發展透析李爾的表現、經歷、結局以及對于現實的創新意義。
[關鍵詞]李爾;莎士比亞;戲劇;形象
一、導言
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戲劇家和詩人。他的創作主要是用無韻體的戲劇三十七部,囊括了喜劇、悲劇、歷史劇、冒險劇、愛情故事與童話,從文學的每道門登堂入室,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特色。四百年來,這些故事在全世界各地一再上演,受歡迎程度至今沒有一位作家可以超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悲劇作品[1]有《哈姆雷特》、《李爾王》、《奧塞羅》、《麥克白》和《羅密歐與朱麗葉》。在20世紀,《李爾王》[2]逐漸取代了《哈姆雷特》的地位,被公認為是莎士比亞最偉大的悲劇。它以無窮的魅力吸引著眾多專家學者去探索其豐富而又復雜的內涵。
二、李爾形象的豐富內涵
(一)雙重身份,自身缺陷極大
李爾,是古代大不列顛王國的君主,雖處于等級森嚴的社會時代,但赤裸裸的金錢力量對整個社會的人倫關系造成了深重破壞。所謂公爵,公主一個都是寡廉鮮恥,無惡不作之徒。在他們眼里,既沒有父親,也沒有兄弟;在權力、財富面前,一切人間的倫理,道德原則皆可踏而過之,他在位時唯我獨尊,專制獨裁,無視人民疾苦。在他統治下的英國“愛情冷卻,友誼疏遠,兄弟分裂;城市發生暴動,國家發生內亂,宮廷發生叛逆,父子關系崩裂”(第一幕,第二場)。由于自負和固執,李爾荒謬地設計了一場所謂的“愛的測試”,將國家作為獎賞,“看看誰最有孝心,最有賢德,我就給他最大的恩惠”,這輕率的決定從此揭開了悲劇的序幕。
李爾也是一家之主,作為父親,他不善于和自己的兒女溝通,無法同女兒們建立一個彼此信任了解的橋梁。長期的身居高位養尊處優的習慣,使他變得剛愎自用、虛榮心級強。李爾王雖然愛著自己的女兒們,但本質上仍有著他的怎么的一面。而這種怎么的本質也是時代和其地位賦予給他的。他生活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的利已主義的惡勢力就像洪水猛獸一樣橫行于世,作為封建時代的君主,他自以為君臨一切。而俗話說,有其父秘有其女,也正是他的錯庸專制——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培養出那兩位慣于以阿庾奉承墳父王歡心來換取權勢的見利忘義的不孝女兒。當大女兒和二女兒用阿庾的、娓娓動聽的孝順之詞虛偽表達自己對父親的愛時,他心花怒放,糊涂的李爾看不秀她們蓄謀已久、覬覦王位、財產的貪婪狠毒之心。并且多年的阿諛之詞蒙蔽了他的雙耳,聽慣了贊美之言的李爾,聽不慣小女兒最簡單卻是樸實、趨勢的心底話。自在顯赫尊貴之巔的李爾,無法分辨真情也謊言,忠誠與奉陷害,在付諸行動的真摯的情感與華麗曼妙的言語之間,他偏愛后者。當李爾希望從考狄麗來那兒得到他想象中的更甜美的奉承時,誠摯的考狄麗亞堅定的話語:“我愛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第一幕,第一場)卻被李爾看作是沒良心。不知道不善言辭的考狄麗亞將對父親的愛藏于心底,他的怒氣勃然而起:“好,那么讓你的踏實作你的嫁妝去吧”。(第一幕,第一場)高納里爾和里根一旦有了權力和國土,對待父親越來越無禮。
美好幻想破滅后的李爾開始面對真實的世界,開始了自我認識的歷程。李爾由此產生了認同危機,他對自己的國王和父親身份提出質疑。對自己由此產生了眼睛和智力提出質疑:“這里有誰認識我嗎?這不是李爾。是李爾在走路嗎?在說話嗎?他的眼睛呢?他的知覺迷亂了嗎?他的神志麻木了嗎?嘿!他醒著嗎?沒有的事。誰能夠告訴我,我是什么人?”(第一幕,第五場)他認識到考狄麗亞是愛他的,但是他依然歸咎于她,認為自己當初那樣粗暴對待她首先是因為她太驕傲,不肯當眾表白她的孝順之心:“啊!考狄麗亞不過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怎么在我的眼睛里卻變得這樣丑惡!它像一座酷虐的刑具,扭曲了我的天性,抽干了我心里的慈愛,把苦味的怨恨灌了進去”(第一幕,第五場)。李爾并不能認識到是自己釀成了如今的苦果。飽受痛苦的李爾在暴風雨中把個人的滿腔憤怒指向人類社會、大自然和天神。他質疑人世間和上天是否有正義,呼喚迅疾的雷電擊碎人的頭顱,然后干脆責罵上天支配的風雨雷電是“卑鄙的幫兇”(第三幕,第二場),因為它們也像他的兩個女兒一樣毫無心肝,攻擊他這樣可憐的老人。他之所以如此憤怒,首先還是由于高納里爾和里根對他的虐待;但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看不到自己的錯處,認識不到應當對自己的境遇負相當的責任。羅伯特·奧恩斯坦也注意到,“李爾在某種意義上是莎士比亞劇中最自相矛盾的主角——他自己不公正卻又相信宇宙秩序的公正,作為國王和父親,他的行為有違自然法則,卻又相信理性的自然法則的存在。”[3]267。李爾覺得一貫公正的神明居然讓自己如此受苦,實在難以理解。
(二)正面因素和悲劇毀滅中令人同情的成分
在《李爾王》一劇中,李爾由一位國王落魄到一位無家可歸的指乞丐。莎士比亞要顯示的不僅是一位父親被兒女所拋棄的一般悲劇,還要顯示一位身份徒降的國王的悲劇;作品所表現的是一個在國家中放棄王位,而非在家庭中放棄父權的個人悲劇。這幕悲劇引起的美感是在喚起人們“憐憫”的同情。在莎士比亞的筆下,李爾王仍然應該是一個正面形象,因為他追求的理想有著人文主義的進步因素,有強烈的正義感,盡管他有脫離群眾等嚴重缺陷,雖有意驅逐黑暗勢力,可為強大的惡勢力所阻撓,不能實現以至受打擊而失敗。作為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歷史人物,歷史的運轉決定了李爾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李爾的毀滅,又是值得同情的。
李爾顯然并不是高納里爾與里根奉承的那樣“在沒有黑須之前,就已經有了白須”的人,而是哪弄人所言“你應該懂得些世故呀”。他懷著一種老小兒的天真心理認為,“國土”、“威力”、“特權”和一切君主的尊榮交出去以后,女兒們因此更愛他;更加致命的錯誤是:他認為自己如同上帝具有指稱善惡的權利,哪個女兒迎合他那不可一世、樂聽奉承話的心理,哪個是忠誠、孝順、體貼的女兒。考狄麗亞因拒絕參與敬神的儀式,一轉眼間,她在李爾王心中便從“眼中的珍寶,贊美的題目,老年的安慰,最好的,最心愛的人兒”,變成了“比啖食自己兒女的生番更令我憎惡”(第一章,第一場)的人。然而,有誰會因此減少對他的同情呢?雖然李爾聲名顯赫,但他的內心是惶恐而焦慮的。他明了已到暮年的自己需要的是新情的呵護以及愛的保障,他以為可以將國土作為籌碼換得女兒對他的愛,自己亦可安享晚年。然而,他不知道這場所謂的“愛的測試”實質上是對考狄麗亞和她兩個姐姐的侮辱,更是對愛的褻瀆。
李爾被兩個女兒趕出家門,流浪荒野,考狄麗亞得悉祖國變故,領兵來攻,失敗被俘,在英軍營地父女會面時,李爾向考狄麗亞說道:讓我們到監牢里去,我們兩人將像籠中之鳥一般歌唱,當你求我為你祝福的時候,我要跪下來求你饒恕。(第五幕,第三場)而此時的考狄麗亞,在他心中美如上帝的天使(連同他自己)。但是他很快便知道,他心中的理想只能成為光景,因為考狄麗亞被縊死。當考狄麗亞被縊死之后,李爾連聲哀號,指責其它的人說:“你們都是一些石頭人,并且說道:“要是我有了你們的那些舌頭和眼睛,我要用我的眼淚和哭聲震撼蒼穹”。(第五幕,第三場)他本知道女兒“像泥土一樣的死去”但他卻祈求道:“要是她還有活命,那么我一切悲哀都可以消逝了”。(第五幕,第三場)在推動了一切之后,李爾的理智被撕成了碎片,是考狄麗亞的愛治愈了他的瘋癲。悲劇在此達到高潮。李爾抱著考狄麗亞的尸體哀聲慟哭,老淚縱橫;他“要用他(我)的眼淚和哭聲震撼蒼穹”。死了扼殺這種寶號情感的劊子手,但這還是沒有給他繼續活下去的勇氣,他和考狄麗亞——他最終的精神歸宿倒在了一起。李爾最終明白了何為真愛,他終于找到了不依附于外在的財富權勢便可擁有的真愛,這是他當年為王為政時無法明白、無法看清的。
李爾是個凡人,但有著比神所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驕傲。他在遭受背叛與侮辱時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在命運巨變時表現出了狂烈的激情,這些盡管表明了他作為一個國王所具有的非凡氣魄和威嚴,但他仍然是作為一個有缺陷的凡人形象而出現的。他自詡有神的權威和魅力,實際卻并非如此,他的力量來自世俗的權力,一旦他交出王冠,他就一文不值了。“他的自我崇拜終于越出一切常識的范圍:他把由于自己的地位而享受到的一切光榮,一切尊嚴,都歸之于自己個人,他決定拋棄他的權力,他相信,這樣以后,人們仍繼續會對他表示敬畏。李爾視自己為宇宙的中心、英明的統治者,在一個絕對理性的世界上充當賞罰分明的法官,但一個比他更大的宇宙——“命運”擊垮了他,這使他得以看見過去一直審美觀點遮蔽住的東西[4]321。他從一個君臨天下的國王變成一個“可憐的,衰弱的,無力的,遭人賤視的國王”,他從自己的痛苦中終于體察到別人的痛苦:“衣不蔽體,不幸的人們,無論你們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著這樣無情的暴風雨的襲擊,你們頭上沒有片瓦遮身,你們腹中饑腸轆轆,你們的衣服千瘡百孔,怎么抵御得了這樣氣候呢?啊!我一向太沒有想到這種事情了。安享榮華的人們啊,掙開你們的眼睛來,到外面來體味一下窮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們享用不了的福澤給他們,讓上天知道你們不是全無心肝的人吧!”(第三幕,第四場)
三、結語
李爾的王朝在時代的動蕩與社會的災難中搖搖欲墜,然而李爾久居高位而喪失理智,變得剛愎自用,任性專橫,長年為詆諂媚奉迎所包圍,使其行為處事隨心所欲,這是釀造他性格悲劇的主要原因,李爾悲劇的個人因素在于其父愛與君主權威的顯赫,造成的仁慈與專橫之間不可避免的悲劇,他對子女有愛的要求,但在表達愛時又不可能擺脫君主的專橫與權威的顯赫,以至于對兒女如同對臣仆,以她們對自己的曲意奉承的程度來決定恩賜給她們的財產,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形成的自我中心主義造成了李爾性格上的剛愎自用,而他的兩位女兒正好利用他的這一性格來獲取其歡心,滿足他的所謂尊榮來威嚴,達到掠走他全部財產與權益的目的,因而他自身的性格的悲劇因素為其掘下一條毀滅之路。
而艾略特曾說過:“談到像莎士比亞這樣偉大的人物,也許我們永遠不能正確認識他的真相,那么我們最好每隔一段時間就變換一下我們的假說。”[5]281。莎士比亞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偽善的人倫關系,肯定了同情、博愛的道德原則。李爾的形象飽滿、真實,數百年來對它的探索從未停頓過,解釋也層出不窮,如同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它承受了各種褒貶,相互矛盾的闡釋,對于后人來說,仍然是一座充滿誘惑的迷宮。
參考文獻:
[1]朱生豪等譯,莎士比亞命令[M].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2]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李爾王》[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3]Robert Ornstein,“Shakespeare”,The Moral Visionof Jacobean Tragedy[M],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0.
[4]之琳,莎士比亞悲劇論痕[M].北京:三聯書店,1989.
[5]Harris,Laurie Lanzen.Shakespeare Criticism(2)[M].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84.
作者簡介:陸巧玲(1992-),女,瑤族,貴州凱里人,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0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