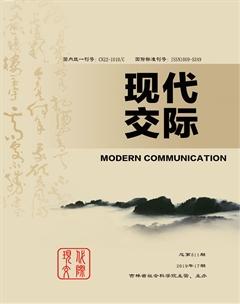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教學現狀與應對策略
郭闖 賀寬軍
摘要:本科畢業論文是高校本科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實現本科培養目標、衡量本科教學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對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寫作現狀的分析,從提高宣傳力度、加強監督管理和檢查、加大經費的投入、提高本科生導師制培養實效性和改變畢業論文時間安排及形式幾方面提出了提高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一些應對策略,以期改善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教學現狀。
關鍵詞:民族院校 本科畢業論文 現狀 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G65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17—0208—02
本科畢業論文是高校本科教學計劃的重要環節,是大學四年最后一學期在老師指導下學生獨立完成的學術性論文。本科畢業論文是對學生掌握的基礎理論知識、實踐技能和綜合能力的檢驗,也是學生首次運用所學知識進行科學研究。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高低,不僅反映了學生大學的學習質量,同時也反映了高校本科教學水平。因此,教育部對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時,本科畢業論文是評估的重要內容之一。[1]筆者在民族院校從事本科論文指導實踐多年,分析了民族院校的畢業論文教學現狀,提出了改善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教學現狀的一些策略。
一、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的教學現狀分析
各個高校十分重視畢業論文工作,出臺了一系列舉措確保其質量。然而,由于高校擴招,教師指導的學生人數也逐年增多。此外,大四下半學期學生忙于考研、就業,沒法集中精力,再加上缺乏有效激勵和監督機制等因素,導致很多學生對畢業論文不夠重視,畢業論文的完成質量較低。民族院校大都位于經濟比較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辦學經費緊張,實驗儀器設備相對較少,學生的實踐場地缺乏,畢業論文經費投入不足。同時,民族院校的學生大多來自于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學生的能力差異較大,學習成績也參差不齊。這就造成了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在選題、文獻檢索與整理、論證、結構、表達、格式規范等方面存在嚴重欠缺,也存在著抄襲、拼湊、做假甚至買賣論文等學術不端現象。因此,改變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教學現狀,提高本科畢業論文的教學質量,已成為當前民族院校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
1.學生層面
盡管畢業論文是高校本科教學計劃的重要環節,但不少學生對其不夠重視。不少學生認為,大學四年所學課程考試都通過了,畢業論文不過是走走形式,不重視畢業論文的寫作。再加上做畢業論文的時間與考研復試或各種就業招聘的時間相沖突,這就導致一部分學生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考研或就業中,不能集中精力完成畢業論文。此外,民族院校學生的能力高低不齊,一部分學生獲取研究資料能力不強,實驗操作和寫作能力低下,這樣完成的畢業論文總體質量不高,甚至有抄襲、拼湊及粗制濫造等現象。
2.指導教師層面
眾所周知,指導教師在本科畢業論文寫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民族院校因師資力量匱乏,科研水平總體不強。另外,每位教師都需要指導一定數量的本科生,每年指導6—8名本科生是常事,有的教師甚至指導10多名或更多學生。再加上教師本身繁重的教學任務和科研工作,每年需要完成各種考核任務,還要準備職稱晉級,部分老師還需要指導研究生由于時間和精力有限等原因,很難保證指導質量。另外,有的指導教師責任心不強,再加上科研水平不高,很難給學生作出有效的指導。學生完成論文后,也不用心幫助學生修改和完善。上述這些原因,直接影響了學生畢業論文的總體質量。
3.學校、學院層面
民族院校大都地處少數民族地區,國家下撥的經費有限,而學生學費的收費標準普遍較低,且學生欠繳學費情況相對普遍,這就造成了民族院校辦學經費緊張的被動局面。民族院校學生完成畢業論文所需的實驗設備缺乏,實驗場地緊張,且畢業論文所需經費投入嚴重不足,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本科畢業論文的完成質量。此外,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質量不高的現狀也與對畢業論文的監督、管理和檢查等程序執行不到位有關。畢業論文的寫作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每個階段、各個環節嚴抓細管。學校從宏觀層面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來保證畢業論文質量,但具體落實需要靠學院去執行,只有把工作落實到位,才能夠保障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但是,有些學院不重視本科生畢業論文管理工作,學校制定的畢業論文有關規定執行不徹底,畢業論文管理混亂,對畢業論文質量把控不嚴。
二、提高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應對策略
1.加大宣傳力度,強調畢業論文的重要性
畢業論文的質量不僅是學生綜合素質的反映,體現出指導教師的科研能力,同時也反映了學校的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高低。[2]因此,一定要讓學校管理者、教師和學生都認識到畢業論文的重要性,重視畢業論文。
2.加強監督、管理和檢查,把好畢業論文質量關
學校應成立專門工作小組對畢業論文這項工作進行監督、管理和檢查。二級學院應根據自身院系的專業特點,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畢業論文標準與檢查進度安排等。初期選題應符合人才培養方案目標,有一定的科學性與創新性。中期應對畢業論文開展檢查,以便及時發現問題,及時整改。[3]后期,要認真組織答辯,嚴格遵照答辯要求,對畢業論文不符合要求的學生,應不予通過答辯。答辯工作結束后,應對通過答辯的畢業論文進行抽查,分析問題所在,并通報各院系。
3.加大畢業論文經費的投入
民族院校要想提高畢業論文的質量,必須加大經費投入,不能因為經費緊張,導致畢業論文縮水、大打折扣。,應該充分考慮專業特點,不同的專業完成畢業論文所需經費也各不相同,像理工科等專業,應給予較大力度的經費支持。
4.提高本科生導師制培養實效性
本科生導師制在民族院校的實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學生,在低年級的時候就跟導師在實驗室里查資料、做實驗,能夠較早地開展科研,為畢業論文的順利完成打下扎實的基礎。但也有指導教師不負責任,很少對學生進行指導,對學生不管不問。本科生導師制培養實效性還有提升空間。學校需要加大對本科生導師制工作的扶持力度,制定獎懲制度,提高本科生導師制培養實效性。
5.改變畢業論文時間安排及形式
畢業論文的完成,可不只限于第八學期。適當改變畢業論文的完成時間,有利于緩解學生考研和就業造成的畢業論文質量下降問題。[3]在指導教師的督促下,學生可以在大二或大三時提前完成部分畢業論文撰寫任務。此外,提交畢業論文的形式可以靈活多樣,形式上不局限于畢業論文。這樣更有利于調動學生的科研積極性,有利于創新能力的培養。
三、結語
畢業論文是高校本科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實現本科培養目標,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環節。畢業論文的完成涉及學校、院系、班級、教師和學生多個層面,需要每個層面各負其責、通力合作,才能使學生保質保量地完成畢業論文。鑒于民族院校自身的特點,盡管學生畢業論文完成中存在不少問題的,但是只要學校重視,學校和院系敢于改革和創新,學生積極主動,加上指導教師認真負責,相信畢業論文質量一定會得到不斷提升。
參考文獻:
[1]喬軍,孟慶玲.提高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幾點思考[J].教育探索,2011(9):46—47.
[2]王又容,方華.本科畢業論文現狀與思考[J].教育教學論壇,2017(39):243—244.
[3]田志環,焦傳珍.生物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J].教育教學論壇,2018(14):101—102.
責任編輯: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