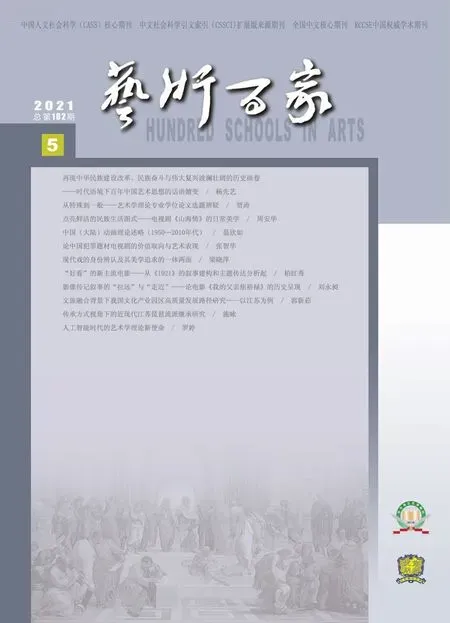古琴非遺保護傳承現狀調查的新收獲
秦序
摘要:施詠的《弦外之音——當代古琴文化傳承實錄》分為“實踐調查”與“理論思考”上下篇兩大部分。調查了各琴社的生態發展環境、運行機制、相關流派琴樂的保護現狀;以及相關琴人的琴樂理念、保護實踐措施等。從理論層面對當代古琴的傳播(類別、功能、特點、偏誤)、傳承(方式、組織結構、對象、技巧)、保護(問題與對策)以及發展四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探討。這一研究不僅體現了他的學力、才華,也的確實體現了施詠先生的敏銳觀察力,體現了他獨到的學術眼光新穎的學術見識。
關鍵詞:音樂藝術;古琴;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理論;現狀;調查
中圖分類號:J60文獻標識碼:A
施詠教授的《弦外之音——當代古琴文化傳承實錄》就要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公開出版了,這是他在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后”工作期間取得的豐碩學術成果,也是2003年中國“古琴藝術”成功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以來,又一部有關古琴文化傳承及現狀的有價值的調查研究專著。我認為這是近年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建設方面一項重要收獲。所以,不揣自己對古琴藝術的無知,不顧忌自己對當今古琴傳承保護缺少調查研究,仍非常高興給這部專著寫幾句感想。
本來古琴藝術申遺成功,已經大大推動了社會方方面面對古琴的關注,推動了琴樂的表演、傳播,也有力推進了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相關書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陸續出版了介紹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種教材,出版了有關古琴歷史、文化的多種研究成果,以及吳文光先生《神奇秘譜樂詮》這樣的古琴曲打譜釋讀的專著,還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種譜集所見載琴曲譜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資料匯編,也終于由中華書局出齊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藝術方方面面的申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而言,僅我近年有幸審讀或應邀參與相關答辯問題的,就有十幾篇近20篇,可見青年一代投向古琴的學術目光之殷切,他們的成就也頗令人欣喜。可以說,我國古琴藝術的發展和保護、傳承,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令人振奮的階段。
施詠先生的研究,也許屬于姍姍稍后來者,但在這百花競放的場景中,卻因別具風致,一定能夠脫穎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蘇徐州中國中國礦業大學舉行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上,我初次聽到施詠教授介紹他有關古琴藝術保護的部分研究成果,當即感到非常有價值。例如,他從傳播學出發,探討了古琴在中國古典小說、當代武俠小說中的文學傳播,探討了古琴在唱片、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中的傳播及所產生的偏誤現象,他既探討了古琴的網絡傳播概況和特點、古琴網站的類別與功能,還總結了琴樂傳播的“模糊性、反傳播性與多層綜合性”三大特點,還提出多種傳播手段相互交織相融、多層綜合、多元并存,成為當前琴樂傳播的發展趨勢,共同推動古琴文化在當代的傳播和發展。
盡管只是簡短的介紹,但讓人立馬感到他的研究視角非常新穎,體現出他研究意識的獨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學界劉知幾有關史學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幾項重要條件的闡述。按劉知幾字子玄,著有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代表作《史通》,他提出從事史學研究的人,必須具有“才”、“學”、“識”這三種基本條件,即所謂的史家“三長”。
據《舊唐書》劉知幾本傳記載: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左木右便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①
這里所說的“才、學、識”應如何理解?今人張岱年、方克立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認為:所謂“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歷史編纂和文字表達方面的才華和能力。所謂“史學”,指占有史料和掌握歷史,要能搜集、鑒別和運用史料,要有廣博豐富的知識,還要深思明辨,擇善而從。所謂“史識”,是指史家的歷史見識、見解、眼光、膽識,即觀點和筆法,包括“善惡必書”的直筆論,也包括其他的歷史觀點。②
也有的學者認為“才、學、識”,其實大體相當于人們常說的文、史、哲學,是從事史學以及其他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必備的基本素養。
“才、學、識”三者,雖各有作用,但相互聯系非常緊密。也有很多學者認為,三才之中,識尤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學家鄭樵便在《通志·總序》中強調:“夫學術造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續詩品三十二首·尚識》也說:“學如弓弩,才如箭簇,識以領之,方能中鵠。”
當代著名學者錢鐘書先生,認為識不可無,認為識也是才、學并重或相輔,因為識力就是洞察力、鑒賞力、判斷力的別名,是以“學力”為其根本的。但他在《談藝錄》五一《七律杜詳》中,還是強調指出:“識”固為先,“識曲聽真”,方得為“具眼”。認為它首先表現為一種“發覆破的”的洞察力、鑒別力。
當今盛行的史學理論中,也有類似的強調。學者們指出,雖然史料或史實在史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實的史料當然是歷史學能夠成為一門科學的前提,所以史料對歷史學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學便是史料學”③的說法。但是,史料或事實本身,畢竟并不能自行給出一幅歷史學家所懸之為鵠的歷史構圖,也不能自行給出任何理論來。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乃是(或者至少應該是)一幅歷史構圖,但這幅圖畫最后是由歷史學家的思維和想象所構造出來的,任何理論也總歸是人的思想的產品。如果同樣的史料和史實就能自行得出同樣的結論,那么只要根據一致同意的史料,歷史學家就不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了,也不會一代一代的學者們來重新認識、研究歷史,重新寫作新的歷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對歷史學的形成(即根據史料形成為一幅歷史構圖)而言,更具決定性的因素乃是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積累。④
西方現代史學理論中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等觀點,也正體現著對歷史研究者“識”的強調。endprint
我認為,才、學、識不僅是歷史研究者的基本條件,也可以說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識”既是認識、辨識、識別、認知的能力,也是見識、理解、洞察、意識,是研究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具體體現。“識”包含著康德所說人類認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過程,也貫穿在人類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再到實踐無數往返的全過程。以歷史研究為例子,從具體史料的選擇、辨識,到史料確認后對它們做出的解釋,對史料所反映的史實的認知,都離不開“識”。這些工作,有的是純科學的,或“完全科學的”,或是技術性的,但有的則僅有科學態度和方法是不夠的,還需要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貫徹始終。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指出,歷史學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人性學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學和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外,還有“第三個方面”即史家對人性的探微,這也是一種史家應該具備的見識和意識。⑤
由此看來,史家和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研究者所應具備的“識”內容是非常非常豐富、廣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斷進行的歷史研究、學術研究,某種意義上講,則是一代一代人認識不斷發展不斷提升的結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斷獲得新的認知和新的體會的結晶。
這樣說,并不是否認才、學的重要。推動史學進步的力量來自四方八面,史學大師王國維就認為學術史上的新突破,往往來源于新的發現,新材料。但甲骨文等這些導致學術突破的新材料,其價值和意義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國維先生那樣的遠見卓識,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蘊涵的重要價值嗎?
施詠教授在其古琴調查的課題研究中,反映了他尤為突出的“才”、“學”、“識”三者的良好結合。正是很好地結合了傳播學和歷史學方法,又迅速網羅捕捉了許多新的傳媒,以及網絡上出現新動向,為我們考察研究古琴藝術遺產的保護傳承,提供了富于啟迪意義的新視角。
全書分為“實踐調查”與“理論思考”上下篇兩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調查報告組成,通過對梅庵、廣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個琴派下的近三十個琴社、琴館的古琴保護傳承現狀的實地考查,逐一調查了各琴社的生態發展環境、運行機制、相關流派琴樂的保護現狀;以及相關琴人的琴樂理念、保護實踐措施等。下篇則從理論層面對當代古琴的傳播(類別、功能、特點、偏誤)、傳承(方式、組織結構、對象、技巧)、保護(問題與對策)以及發展四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探討。
這一研究不僅體現了他的學力、才華,也的確體現了施詠教授的敏銳觀察力,體現了他獨到的學術眼光新穎的學術見識,由此我們看到一個青年學者已經具備了今后不斷取得學術進展和突破的各種有利條件。
“山僧未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雖然未及從容細讀施詠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沒有那么廣泛的學識來評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過對他的研究課題的點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擁有的分量和價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間合作教師劉承華教授的身影。相信廣大讀者,尤其是廣大青年認真閱讀本書,一定大有收益,能夠得到種種啟示。同時,加深自己對古琴藝術這一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全面立體的了解認知。
著名學人費孝通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覺”的重要思想。他認為21世紀是“文化自覺”的世紀,指出我們已經錯過來自西方啟蒙時期“人的自覺”,不能再錯過當今全球一體化浪潮沖擊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覺”。我們每一個中華文化的傳人,有必要不斷提升自己文化自覺意識,積極參與中華優秀文化藝術傳統的傳承弘揚,為中華文化復興的事業,多一分擔負,多一份貢獻。施詠教授的努力,也為我們做出了一個好的范例。
施詠教授正“富于春秋”。作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經獲得各級學位,并被南京藝術學院聘為正教授——他已經建筑起了繼續前進的堅實的學術基礎。因此,衷心祝賀他已取得的豐碩成果即將出版問世,同時也期待他今后不斷超越自己,不斷創造更新的業績。(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新唐書》本傳則簡稱劉知幾云:“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頁。
③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④何兆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歷史與歷史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
⑤同④,第5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