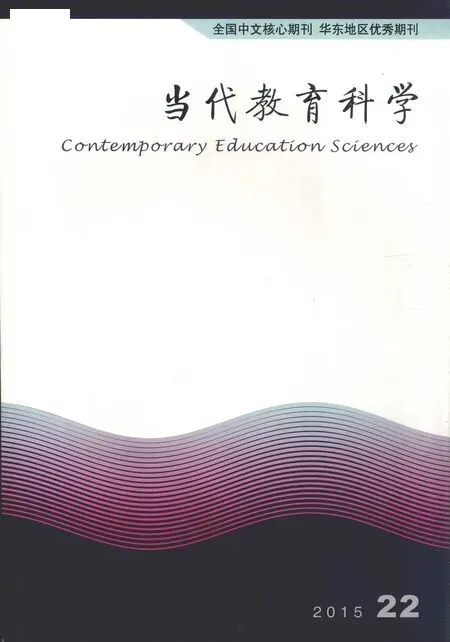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
●段會冬
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的現實困境與理論反思*
●段會冬
近年來,在民族文化遺產傳承面臨危機、學者對教育國家過度整合的擔憂以及學校知識觀的后現代轉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具備了理論基礎和現實需求。然而,在教育一線關于地方性知識進入學校的意義和可操作性仍然存在較大的質疑。問題的關鍵在于將“地方的知識”簡單地混同于“地方性知識”。要改變這種狀況,既要正視作為知識觀的“地方性知識”促進學校知識觀的轉變,也要意識到學校傳承方式的有限性,力爭實現地方性知識的活態傳承。
地方性知識;學校;文化傳承
近年來,在文化傳承領域的研究與實踐中,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學校傳承引起了眾多的關注。盡管一些反映地方文化的地方教材與校本教材已然躍入眾人的視線,但與此同時,對于這一做法的爭議也不絕于耳。弄清楚究竟是政策上的欠缺所導致的操作中的問題,還是從根本上就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是地方性知識通過學校傳承能否走出質疑與困境的關鍵。
一、問題的提出
(一)民族文化遺產傳承危機四伏
在全球化、市場化的沖擊下,一些文化占據了主流文化陣地的同時,另一些文化卻逐漸喪失了原有的生存空間,成為瀕危甚至已然消亡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多樣化的迅速削減成為了20世紀后半段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核心話題。從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伊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繼發布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書》(1989)、《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2001)、《伊斯坦布爾宣言》(2002)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等重要的宣言和報告,使得國際社會對于諸多地域色彩鮮明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的意義與傳承的危機有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民族文化瀕臨消亡的現實危機意味著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解釋那些即將消亡甚至已然消亡的文化事項的文化意涵之上。尋求切實可行的傳承方式,成為破解這一危機的關鍵性問題。自近代教育體系確立以來,學校成為了無可爭議的教育活動的主渠道。這不僅因為個體自進入學校起,在學校的時間甚至遠遠超過家庭,更為重要的是學校代表著國家對于未來民眾的基本要求。科恩(Y.Cohen)認為,“國家或社會建立學校,是要通過始終如一地向兒童灌輸有關國家的教義、象征物以及觀念來確保現行制度的存在。”[1]因此,作為主渠道的學校教育勢必在民族文化的傳承中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這些文化的傳承恰恰是塑造未來國民的最為寶貴的資源。
基于此,國務院2005年出臺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教育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要逐步將優秀的、體現民族精神與民間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編入有關教材,開展教學活動。”有學者還進一步指出,“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應肩負起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保存、傳承和創新的歷史使命。”[2]在這個過程中,傳承民族文化成為學校不容忽視的重要職責,諸如民族民間舞蹈、織錦、飲食文化等方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以地方性知識的姿態借助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的平臺進入學校教育體系。當統一的課程體系中逐漸滲入了地方文化的色彩,學校教育也更加貼近地方的歷史與文化。
(二)警惕對學校國家整合功能的過分強調
如果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導使得更多文化遺產以地方文化的形態進入學校課程體系,那么,一些學者對于過分強調學校國家整合功能的擔憂則從另一個側面促成了地方性知識與學校之間的聯系。自近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框架與認識體系以來,學校作為國家設立的教育機構就肩負著培育國家主義認同的重要功能。特別是對于那些經歷了殖民主義侵略者欺壓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培育對于本國的認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抗擊西方普遍話語的地方性策略。然而,由于國家內部各民族、階層等方面的差異普遍存在,這也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對于國家的認同往往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教育還必須想方設法實現國家的內部整合。“教育有上層建筑的性質。國家整合就體現了這種上層建筑國家主義的概念。教育是一個工具,它通過國家、通過這套意識形態,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灌輸公民教育這套思想體系,使社會實現整合。”[3]
教育的國家整合是以“主流社會”需求為基礎來進行設計的,在這個“主流社會”中,有一套可以暢行無阻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而其文化載體也被打上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烙印。學校教育作為傳遞具有適應主流社會需求的普適知識的場所,成為普通百姓子女通往“主流社會”的一種有效途徑,也因此增強了其吸引力,并且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成為“跳農門”、“跳窮門”等改變命運的康莊大道。
然而,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具備“主流社會”的特征。倘若將“主流社會”的觀點簡單地視為國家整合所追求的觀點,那么,此時的國家整合極易消減文化的多樣性,使得原來具有多樣性的個體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特色,進而使整個文化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受到損害。在由于教育過度國家整合而抽離了原本鮮活的多樣性之后,學校教育脫離社區而被“真空”包圍起來,而從這樣的學校教育體系中走出來的人,便會出現“干活不如老子,燒飯不如嫂子;當頂門杠嫌短,當燒火棍嫌長”的局面。[4]在教育領域中,對于地方性知識的關注便源于對于教育過度“國家整合”的擔憂。
當然,那些擔憂這一問題的學者并不否認教育的國家整合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只不過認為“過度”整合所招致的問題同樣令人擔憂。尋求國家整合與個人生存和社區生存的契合成為解決當前過度整合出現的主要問題的關鍵所在。基于此,有學者提出“在主導性的公民教育中添加地方性教育知識”,[5]從而使得地方性知識通過課程的形式呈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性知識在促進教育的國家整合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作為一種知識觀和方法論,成為溝通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族群的中介和橋梁;它兼具認識論意義和實踐論意義,提供了從一個地方理解另一個地方,從一個地方進入到另一個地方的轉化系統,通過“譯釋”,使得地方與地方之間、國家與地方之間能夠有溝通和交流的平臺。
(三)反思學校中理性主義知識觀
作為知識傳遞最為重要的渠道之一,學校教育深受理性主義知識觀的影響。理性主義知識觀執著于對客觀性、普遍性和規律性的尋求,試圖為人類生存立命尋求確定性之基。在其看來,知識是純粹經驗和理智的產物,只與認識對象的客觀屬性和認識主體的認識能力有關,是價值中立的,具有超越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特點。
然而,理性主義知識觀真的能夠完整地反映人類對于知識的認識嗎?知識真的是價值中立的嗎?知識的生成真的可以脫離情境嗎?諸如此類的問題直指現代知識觀成立的根本性問題。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過程中,“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以現代知識觀的批判者姿態走上歷史舞臺。如果說現代知識觀只不過是借助全球化(globalize)力圖將世界文明納入統一的發展進程,那么后現代思想家則試圖用地方化(localize)來對抗全球化(globalize),重塑知識的情境性、開放性和多樣性,破除科學知識確定性的神話,將知識引向不確定性和地方性。
可以說,后現代知識觀在對批判現代性的基礎上將知識的境域性、生成性、開放性和多樣性凸顯在世人面前,文化的、區域的和價值的因素成為知識合理構成不可或缺的部分。基于這種認識,所謂“科學知識”無論從其產生還是應用來說,都離不開特定的、局部的、情境化的場合,“放之四海而皆準”是科學知識假借普遍性和客觀性的神圣外衣,去地方性之后的結果。也許“根本不存在普遍性知識,一切知識包括科學知識都是地方性知識,科學知識在本性上就是地方性的。……走向所謂的普遍性是科學家轉譯的結果。”[6]
面對知識觀的后現代轉換,建立在知識確定性、客觀性與普適性基礎之上的學校教育也必須相應做出調整。如果知識不再是確定無疑的答案,學校又該如何給學生一個答案?如果任何知識的生成都帶有鮮明的地方性,那么我們是否還要繼續尋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如果知識不再是客觀的,那么我們又如何看待不同的個體所持有的主觀性?諸如此類問題的答案都與地方性知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引導學生關注知識生成的情境性,反思舊有知識觀的弊端,是學校教育在后現代知識觀質疑聲中不得不做出的回應。
二、雙重質疑: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的現實困境
盡管學校實現其文化傳承功能有著深刻的思想基礎與迫切的現實需求,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各方面在這個問題上已然達成共識。實際上,一直以來,關于地方性知識進入學校都存有“價值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兩個方面的質疑。兩方面質疑的存在直接影響著地方性知識進入學校的傳承效果。
(一)“價值合理性”質疑
所謂“價值合理性”質疑指的是對學校傳承民族文化究竟意義何在的困擾。那些倡導民族文化進入學校的地方行政人員和教育工作者自身的言行不一,加之文化持有者對自身文化傳承的復雜態度,使得民族文化進學校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般理所應當。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許多地區的行政人員一面在公開場合,作為地方性知識的倡導者與捍衛者大聲疾呼要保護和傳承地方性知識。尤其是在一些民族地區和農村地區存在的民族學校、鄉鎮學校中,通過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傳承地方文化似乎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然而,這些大聲疾呼者卻往往并未將自己的子女送進地方性知識色彩鮮明的學校(如民族語授課的學校)。在他們看來,孩子學漢語更利于其今后的發展,而學習民族語只能在當地使用,孩子的發展必然受到限制。但為了迎合國家對于地方性知識傳承的關注,這些地方行政人員又不得不在公開場合大肆宣傳地方性知識的重要價值。矛盾的心態導致了他們矛盾的行為。
此類現象絕非偶然。在海南瓊北瓊東一代廣泛流傳著一種名為“軍坡節”的民俗節日,這個節日源自海南民間對于南北朝時期嶺南圣母冼夫人紀念。“軍坡”兩字正式源自對于冼夫人率軍出征的模仿。文革期間,“軍坡節”因為其中帶有的些許宗教和迷信色彩的民俗活動被當作“四舊”終止。而文革結束后,當地民眾自發籌資又重修了冼夫人廟宇并且恢復了“軍坡節”的諸多民俗活動。如此,每逢“軍坡節”,家家戶戶齊聚一堂擺宴慶賀,即便是那些過往的從未相識的行人也會被熱情相邀。而路邊的各種攤位早就在“軍坡節”前三天便陸續擺開了,來自周圍各村各鎮的民眾蜂擁而至,熱鬧的場面不亞于一場盛大的廟會。這些細節足見“軍坡節”在當地所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多年來,海南東北部D縣的文教部門一直致力于推動當地的“軍坡節”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然而,他們卻并未積極推進“軍坡節”進入學校之中。一方面大力宣傳“軍坡節”的文化意義,另一方面卻無視其這種文化在學校課程之中的缺位,兩者之間的反差表面看起來是教師“屈服了”來自考試制度的壓力,實則反映出他們并沒有堅定地認可作為地方性知識的“軍坡節”的文化意義與教育價值。
如果說,那些倡導者對地方文化的言行不一還在預料之中的話,文化持有者對于自身文化傳承的消極態度可能會超出許多人的預期。正如有的學者所言:“誰需要地方性知識和地方性課程?從文化持有者的眼光看,是作為地方性知識擁有者的‘我們’,還是雖有課程決策權但實為‘局外人’的‘你們’?”[7]如果說,吉爾茨提出“地方性知識”這一概念的重要意義在于“像他人看我們一樣審視自身”,[8]即“從被觀察的非西方人角度看西方人自身”,[9]那么所謂地方性知識的價值則未必是相對于地方性知識的持有者而言。對于他們而言,若要加深對自己的認識,更應當尋求異于自己的“他者”的文化,以此作為參照,而不是僅僅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不斷地、無意識地重復著所謂的“地方性知識”。當有些學者提出要正視“鄉村地域文化中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傳統”、“鄉村生活現實中原本就存在的許多合理的文化因素”[10]等文化事項時,我們也許還應清醒地意識到也許持有這些文化的人并不希望在學校中傳承這些文化。
筆者并非否定這些地方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只是希望指出一種張力的存在:局外人看到了這些“地方性知識”對于認識自己甚至關照人類的重要價值,而這些知識的持有者往往更為看重通過學校教育實現階層、空間流動,二者的矛盾并不能用孰對孰錯來評判,但這種張力的存在的確影響了地方性知識的學校傳承,尤其是學校教育中知識與文化的選擇。學校教育是為當地人開辦的,核心目的是使他們能夠通過教育更好地獲得發展,而這種目的的實現如何能夠脫離當地人的需求與期許?
(二)“可操作性”質疑
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不僅面對價值合理性的質疑,在實踐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也頗為令人困擾。“可操作性”質疑指向的正是地方性知識進入學校究竟是否具有現實且持久的可操作性。經費支持不足和時間有限是最為常見的兩種質疑的理由。
盡管新課程改革已經為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預留了空間,然而,一些一線教師對于此種改革的態度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一致擁護。許多教師迫于上級的壓力而不得不開設這些傳承地方性知識的課程,實際心里并不情愿。更何況,三級課程體系原本就沒有規定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必須講授地方文化類課程,因此,許多地方打著地方課程或校本課程的旗號實則教授傳統的“主科課程”的做法便屢見不鮮了。在總體時間固定的情況下,增加地方文化課程本就意味著要“擠占”主科課程的時間。在升學考試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面前,利用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時間開設“主科課程”往往被視為一種應然的選擇。
從某種程度上講,一些曾經在地方性知識傳承上的樣板學校近年來出現的“倒退”現象,也是考試壓力面前學校的無奈選擇。在項目建設初期,經費支持到位,項目評估的壓力往往能夠促成學校完成某項地方文化類課程的建設。然而,隨著項目經費的終止,課程往往就難以為繼了。表面看起來,這只是經費不足造成的問題,實際上,仍舊是在考試壓力面前,學校對于開設地方文化類校本課程興致不高、動力不足所致。有老師無奈地說:“過去有項目支持的時候,大家為了能夠評估通過,確實下了不少力氣整這個教材。現在評估過了,家長看得還是學生的升學率,那些教材整得再好也不能提升學生的升學率。所以現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弄了。就保留了一兩節課講講教材,有的時候還會被其他老師占用。”
在升學考試占據統治地位的學校教育體系中(至少在很多一線教師眼中情況如此),考核和評價教師主要圍繞著教育效果展開,而所謂的“教育效果”又與“考什么”和“怎么考”密切相關。至于其他內容都屬于邊緣境地。可以說,在升學考試的問題上,人們似乎并不重視地方性知識,這也是很多一線教師對于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心存抵觸的原因。
教育是傳遞生產生活經驗、傳承社會文化的社會活動。[11]對學生而言,教育過程中無論是內容選擇與教授,還是目標的設定,甚至教師的體態、動作、穿著打扮等都是一種文化影響。因此,教育過程本身就是文化傳承過程。然而,教育在文化傳承功能的同時,還有“隱含的功能,就是選拔篩選功能”。[12]這意味著教育系統在傳承知識與文化的同時,還肩負著人才的選拔。每一次升學考試都是一次選拔和篩選的過程,通過這種選拔和篩選,個體實現了階層、地域的流動,人群分化成結構性階層樣態。地方的行政領導不愿讓自己的子女學習本地區或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教師不愿讓考試不考的民族文化內容過多占據學校教育的時間,背后的原因便在于對文化傳承和選拔篩選功能之間沖突的擔憂。問題是個體為了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況和階層地位,試圖通過教育的選拔實現階層和空間的流動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本身無可非議,我們又憑借什么質疑那些認為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并不具有持續的可操作性的觀點?
三、從“地方的知識”到“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困境的超越
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困境的出現表明人們并未就“什么是地方性知識”這一看似簡單實則復雜且根本的問題達成共識。“地方性知識”不同于“地方的知識”,后者作為一種顯見的地方性知識的載體并不等同于地方性知識本身。地方性知識的核心價值在于給予我們一種新的知識觀,而不僅是一種現實的文化形態。更加偏重于從知識觀的角度理解地方性知識,既明確了學校改革的關鍵不必執著于某個具體文化事項是否能夠躋身進入學校,也認識到地方性因素在知識生成中的重要意義,進而明確學校傳承不能脫離知識生成的生態環境。正是這種知識觀的存在使得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困境的超越具有了明確的思路。
(一)促進學校知識觀的轉變
許多人認為在學校教育之中應當教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有廣泛遷移性、具有普適意義的知識,而地方性知識只是“存于斯,長于斯”的知識。這些知識在此處有用,離開了“地方”便未必有用,而在有限的時空范圍內,學校教育并不應該選擇適用性有限的地方性知識。然而,地方性知識究竟是一種帶有地方色彩的知識還是一種看待知識的知識觀?地方性知識中的“地方性”究竟指的是具體的某一個地方,抑或是抽象的指向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情境?從前者的意義上講,“地方性知識”與“地方的知識”似乎可以等而視之。這些生于斯的地方文化是人類文化多樣性寶庫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琳諾斯基曾說:“文化……都是直接地或間接地滿足人類的需要。”[13]透過這些生于斯的文化,我們不僅可以了解人們曾經做出過怎樣的努力,還可以為應對各方面的挑戰保留多種可能。
當然,表面上看,將地方性知識視為“地方的知識”的確會面對能否應用到其他時空之中的問題。學校教育畢竟時間有限,在有限的時間之中,倘若只能學習一些離開這一時空條件便難以運用的知識和文化,難免會招人非議。如果這一認識成立,對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的“陽奉陰違”的現象便不足為怪,上文中那些官員的看似矛盾的舉動也便有了合理地解釋。然而,倘若將“地方性知識”看成一種知識觀,這種知識觀實際上是要提出一種觀念:任何知識的產生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性知識也許“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識,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地方性知識’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知識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辯護的,因此我們對知識的考察與其關注普遍的準則,不如著眼于如何形成知識的具體的情境條件。”[14]
對于具體的知識形成的特定歷史情境的關注,并不是要激起普適知識與“地方的知識”的沖突,反而是試圖從另一層面調和二者的矛盾:所謂的普適知識也有其形成的特定歷史條件和情境(地方性),而所謂的“地方的知識”也有其蘊含的普適意義與價值(普適性)。如此一來,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知識體系都面臨著“先天有效性”的危機。這種危機非但不是要讓人們在多元性面前無所適從,更是我們進一步推進“普適知識”乃至整個知識體系發展的重要前提。對于“理所當然”的懷疑不正是科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嗎?因此,地方性知識不僅具有批判性意義,更具有彌合普適性與地方性的建設性意義。這使得我們更能清晰地認識到作為一種知識觀的地方性知識帶來的認識上的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將直接影響考試內容乃至整個教育內容的選擇。換言之,選擇的任何知識都是地方性的,教育過程不僅要傳授知識本身,還要引導學生學習這些知識形成的歷史情境,從而加深對知識生成過程和條件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地方性知識的地域局限性為借口阻礙地方性知識進入教育內容的做法便無據可依,地方性知識學校傳承的現實困境也便迎刃而解。
(二)地方性知識傳承不能脫離“地方”
地方性知識既然生成于地方性因素,那么傳承這些知識的關鍵便在于保有“地方性”。盡管學校的確具有傳承知識與文化的功能,然而,作為一種具有明顯時空界限的教育機構,學校不可能將所有的知識納入學校系統進行傳承。即便是有些文化的確瀕臨滅絕,但我們也不能據此判定它就應當立刻進入學校。換言之,未能進入學校加以傳承,并不表示這種文化本身缺乏傳承的必要和意義。在知識爆炸的今天,在有限的時空內,學校必須協調好知識的篩選與方法的引導之間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學校在無法窮盡“地方的知識”的情形下,引導學生更加關注“知識的地方性”則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從地方性知識的角度講,學校只是地方性知識傳承的方式之一。我們不能因為作為主渠道的學校的存在而忽視學校之外的其他傳承過程。既然地方性知識的生成過程離不開地方性因素的作用,那么地方性知識的傳承也不能離開其生成的生態環境。知識的生態環境是知識能夠源源不斷得到生成的關鍵,學校只不過是從眾多的知識中篩選那些符合國家需求并且適合進入學校的知識。注重在真實的生活中習得知識和知識的生成過程,注重知識生成的生態環境在知識生成中的重要意義,是20世紀初中國進行的“鄉村建設”為我們留下的寶貴思路。
20世紀初,梁漱溟等學者為了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提出了借助“鄉村建設”從總體上和根源上解決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總體上”強調的是社會各系統的關聯性;“根源上”強調的是鄉村是中國的基礎,鄉村建設正是從基礎改進做起。這一邏輯對于地方性知識傳承的意義十分重大。首先,必須承認的是地方性知識最初并不在學校場域中傳承,進入學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在原有的生存時空中的傳承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為了不使之失傳,人們才想到借助現代教育最為核心的力量——學校來實現這一目的。因此,地方性知識的傳承也必須從總體上和根源上入手。總體而言,地方性知識的傳承必須處理好文化傳承與個體發展、文化傳承與文化發展、地方性與普適性、多元性與同一性等多種關系。從根源上講,地方性知識生成于“地方”,發展于“地方”,“地方”是其生存發展的基礎。因此,地方性知識傳承也許立足于“地方”實現“活態傳承”。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性知識的傳承依賴“地方文化建設”,而不僅僅是學校傳承。相比而言,前者的地位更為根本,學校傳承只是一種重要的補充。只有將地方性知識放置在自然與社會生態之中,生命力才有保證,否則,環境破壞了,“物種”也就難以保存了。
綜上所述,盡管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危機、對過分強調學校國家整合功能的警惕和學校知識觀的后現代轉向使得地方性知識進入學校既具有了理論基礎也有著現實需求,然而,在教育一線關于地方性知識進入學校的意義和可操作性仍然存在較大的質疑。問題的關鍵在于許多時候我們將“地方的知識”簡單等同于“地方性知識”。要改變這種狀況,既要正視作為知識觀的“地方性知識”促進學校知識觀的轉變,也要意識到學校傳承方式的有限性,力爭實現地方性知識的活態傳承。
[1]袁同凱.教育人類學簡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235.
[2]普麗春.學校教育中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0,(2):35.
[3][4][5][12]滕星等.教育領域中的國家整合與地方性知識[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5):31-33.
[6]吳彤.兩種“地方性知識”[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11):87-94.
[7]蔣紅斌.地方性知識與地方課程開發—一種批判性反思[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3,(4):69.
[8]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1sted.p16.New York:Basic Books,1973。轉引自王銘銘.格爾茲的解釋人類學[J].教學與研究,1999,(4):33.
[9]王銘銘.格爾茲的解釋人類學[J].教學與研究,1999,(4):33.
[10]劉鐵芳.鄉村教育的問題與出路[J].讀書,2001,(12):19—24.
[11]袁振國.當代教育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4.
[13][英]馬凌諾斯基.文化論[M].費孝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5.
[14]盛曉明.地方性知識的構造[J].哲學研究,2000,(12):36.
(責任編輯:曾慶偉)
本文是2013年度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海南文化特質的生成與時代價值——基于冼夫人文化現象的人類學闡釋”研究成果之一,項目批準號:HNSK(QN)13-68。
段會冬/海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教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基礎教育,民族文化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