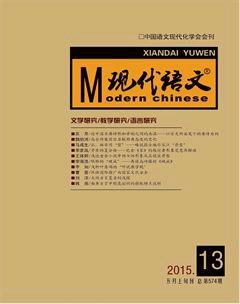新時期問題小說對當下的意義
摘 要:產生于“文革”結束后的新時期問題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作家們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以高度的熱情反映了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成為了時代的旗手。新時期問題小說家們身上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是當下中國文人急需的品質,在當下尤為珍貴。
關鍵詞:新時期 問題小說 當下 責任感 擔當意識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即人們所稱的“新時期”,問題小說大量、集中出現。這些小說反映了十年動亂遺留的問題,工廠生產力下降的問題,農村改制的問題,中年知識分子的問題,機關辦公經費困難的問題,下鄉知識青年返城的問題,兩地分居的問題,等等。這是十年動亂后百廢待興的現實生活的反映,也是文學自身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回歸的表現。雖然新時期問題小說在思想和藝術上有不成熟與粗糙的一面,但以其敢于擔當的批評精神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這是當下許多以娛樂為主要追求的文學創作應當學習的。
一、新時期問題小說之問題
首先是十年動亂造成的社會和人們精神上的創傷的問題。劉心武于1977年發表的《班主任》是新時期最早的“傷痕”小說。小說通過如何看待《牛虻》的典型情節,深刻地揭示出愚昧正是兩位主人公共有的個性特征。宋寶琦偷書是為了賣錢,并且惡作劇地亂加涂抹;謝惠敏只看見書里面有男女談戀愛的插圖就驚叫起來。宋寶琦以負罪的態度認為自己“不該看這黃書”,謝惠敏則以嚴肅的神情要“狠批這本黃書”[1]。小說從展示青少年嚴重的精神“內傷”的嶄新角度入手,揭示了從極“左”思潮桎梏中解救被毒害的青少年一代的必要性。新時期反映十年動亂帶給人精神上的創傷的作品還有很多,比如張弦的《記憶》通過顛倒了一個領袖的像幾秒鐘,使自己的人生被顛倒了幾十年的慘痛故事來批判個人崇拜;白樺的詩歌《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和由其小說改編的電影《太陽和人》都反映了盲目的個人崇拜給人造成的傷痛。
工廠改革問題。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是第一篇描寫改革的作品。他熱情地歌頌了新時期為實現“四化”而奮戰的創業者們。在作品中,喬光樸集大膽潑辣、剛毅果敢的性格和社會主義企業家的過人魄力與領導藝術于一身。事實上,改革中的現實,遠非喬光樸想象的那樣簡單,他對解決矛盾的方式和過程的把握有簡單化的傾向,他的方法只能對內,對外是行不通的,無法應對市場經濟的需要,鐵腕不適合市場,市場挑戰權威。之后的改革小說中,水運憲的《禍起蕭墻》使我們看到了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嚴峻形勢,看到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艱巨性;張潔的《沉重的翅膀》讓我們認識到工業現代化是帶著沉重的翅膀起飛的,更艱難的是傳統意識、庸人哲學等“慣性勢力”的嚴重挑戰。
農村經濟體制問題。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描寫新中國成立前,連“造屋”的夢也不敢做的貧農李順大,土改后立志要建造三間青瓦屋。為了實現這個愿望,他省吃儉用,好容易買回三間青磚瓦屋的全部建材,卻在“大躍進”刮起的“共產風”中,被拖到公社蓋了煉鐵爐。后來又積攢了足夠的鈔票,誰料到了“文革”,竟被一個造反派頭頭敲詐一空。直到粉碎“四人幫”后,他才在公社老支書的幫助下,將屋子蓋了起來。李順大三起兩落的造屋史,真實而尖銳地反映了“左”傾錯誤對土改以后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境遇的農民的嚴重打擊。今天的我們回過頭重新讀這篇小說,很容易對當時的農村體制發出質疑——熱心腸的區委書記幫助李順大順利蓋上了新房,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位區委書記也同樣在濫用他的行政權力來幫助李順大。另外一部小說《陳奐生上城》也是通過一系列偶然疊加出來的幸運來反映新的時期進城農民的辛酸。“在小說的結尾,陳奐生住縣委招待所的經歷演變成為傳奇,從側面證明縣委書記確實生活在有別于普通農民的世界,那兒的物質生活充裕程度遠遠超出了農民的想象力”[2]。
中年知識分子的問題。諶容的《人到中年》是以一種知識分子的受難方式折射了歷史的悲劇和文化的錯位。陸文婷是一個奉獻型的知識分子,然而,她在她的工作崗位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和報酬:每月工資只有56塊半,全家4口人住房僅有12平方米,其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為秦波之類的“馬列主義老太太”所漠視和踐踏。在那樣的條件下,盡管她依然表現出一種失望而不絕望、痛苦卻不悲觀的人格魅力,盡管她默默堅持高強度勞動而全然不顧個人的安危,十多年的超負荷運轉最終還是使她的血肉之軀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她的職業生涯以其生命“斷裂”的悲劇而告終。小說向社會發出了警告:知識分子的境遇已是中國現實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諸如祖國、民族、時代、人民這些宏偉的概念底下,個體究竟有沒有他的絕對可靠的價值定位?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體會這部中篇在當時所達到的深度,或許更為重要。
干群關系惡化問題。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把筆觸伸向1958年的“共產風”“浮夸風”,把大躍進與戰爭時期加以“銜接”,通過藝術剪輯突顯了領導與農民之間從魚水關系到主仆關系的顛倒,過去革命是為了下面的老百姓,而現在戲法則是變給上面看的。[3]小說著力塑造了兩個人物,革命干部老甘和農民代表共產黨員老壽。他們曾在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患難相助。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大躍進時,老壽還是那個老壽,而身為公社黨委書記的老甘卻變成了操著滿口革命辭令,實際上不顧群眾死活的官僚。這篇小說在內容上首次觸及到了“文革”前的極“左”思潮,并第一次以藝術的形式鞭撻了“大躍進”。今天看來,我們在痛心干部老甘的嚴重變質時,也應看到農民老壽的天真軟弱。正是因為有大量像老壽這樣(甚至更為軟弱)的農民作為溫床,才滋生了像甘書記那樣放肆的黨員干部。
夫妻兩地分居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戴晴的《盼》把兩地分居的知識分子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寫得如泣如訴,廣受好評。一對兢兢業業的年輕夫婦,他們無限忠于黨的事業,為祖國榮譽付出畢生心血,但當他們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時,國家卻沒有給予他們應有的待遇。這篇小說的寫實性,它回蕩于作品之中的憤激之情,以及人物命運的極端不幸所顯現的悲劇美,曾經牽動了全社會關注知識分子的神經,贏得了全國讀者的共鳴,較早地提出了知識分子愛與創造的要求同現實條件構成的尖銳矛盾問題,是一篇相當有深度的作品。
知識青年返城問題。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以北大荒四十萬知識青年返城為切入點,描寫了兵團戰士十年屯墾戍邊的壯舉,塑造了一批生動鮮活的知識青年形象。小說發表后在當時產生了廣泛影響,以其氣勢雄渾的英雄主義氣概和沉郁頓挫的文化品格而獨領風騷,感動了無數讀者,一舉獲得1984年全國中篇小說獎。其他知青小說的優秀之作如徐明旭的《調動》、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分別從知青回城難,回城之后精神上的失落感,以及對新的精神追求的企盼等方面反映了知青的生活。
新時期問題小說反映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很多,比如孩子的教育問題,兩代人之間的隔膜問題,教員中想要重新求學讀書的問題等都是問題小說作家所關注的問題,他們對這些問題傾注了很大的熱情,用手中的筆展現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二、新時期問題小說之于當下
讓我們再把視線轉移到今天的文學創作。從作家方面看,今天的新生代作家已經不把小說作為意識形態載體來對待,而是以極大的熱情專注于其商業性、世俗性。在他們的小說里,歌廳、咖啡館、超級購物廣場等與欲望相聯系的場景數不勝數。這些意象成為作家群體或個人想象之中對鐘愛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內容和情調的一種真情流露,同時也滿足了市場化時代的消費者的需求。欲望,作為人性的基本內容,確實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程度上,小說對人性的發掘,表現為對人類欲望的深度展示。90年代小說的一個重要情節就是圍繞“金錢”展開的。如《教授不教書》、《博士點》(南翔)、《試用期》(陳世旭)、《桃李》(張者)、《桃花》(張者)、《不過是垃圾》(格非)、《沙床》(葛紅兵)、《所謂教授》(史生榮)、《大學潛規則》(史生榮)等等;也有將諷刺變為挖苦,將幽默變為戲謔,以市民立場、實用理性來觀照知識分子窘迫一面的,如《所謂先生》(皮皮馮麗)《所謂作家》(王家達)、《風雅頌》(閻連科)、《上邪》(陳希我)、《臥底》(劉慶邦)等等。從客觀效果看,它們無疑推波助瀾了社會思潮中反智論的聲勢。[4]盡管有少數作家如劉震云還在其作品《單位》《一地雞毛》中有意在青年知識者日常生活呈現之外,委婉地表達對中國當代官僚體制的批評,然而大多數小說家顯然拋棄了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維度。他們樂觀地審視著市井生活,對生活苦難則推崇忍耐服從的人生哲學,對庸常的日常生活的邏輯無疑是認同的。他們一反80年代文學中高昂頭顱的啟蒙者形象,遁入世俗的庸常生活,埋頭營造身邊的溫情與安寧。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主體萎頓了,頹廢了。文學在意識到本身從社會中心退到邊緣的過程中,也日漸放棄了對社會核心話題和宏大敘事的承擔,甚至甘愿以平庸和小氣來保持可憐的獨特之處。王富仁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我們已經無蒙可啟”[5]文學不再是所謂民族國家的想象或文化共同體的想象,也不再主要是精神的產物。文學失去了原先附加或虛幻的權力光環,卻也沒有返璞歸真。對于我們這些傳統文學者而言,最令人憂傷且無奈的是,作為一種精神性的表達,今天的文學已經很少或不再能為社會提供建設性的價值觀念了。不僅是啟蒙文學遭到沖擊,而且根本的是文學擔當不了啟蒙的責任和使命。
在當代中國,快節奏的社會生活和巨大的生存壓力,加之消費文化長期以來對大眾的影響,使得大眾的欣賞趣味偏向于娛樂和消遣,不再像八十年代把什么都社會化、政治化。從某一方面看,淡化政治也是歷史進步的表現,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做政治家。現在的現實卻是:人們越來越習慣于把娛樂世界的自由當成是全部的自由,把娛樂參與等同于政治參與,把娛樂世界的“民主”當成政治民主。“一個人在消費娛樂世界里尋求釋放,把它作為自由的全部,自我的全部,那么,這樣的自由就是可疑的,這樣的個性和自我就是扭曲的。”[6]當前的文學現象后面隱藏著危機,因為文學畢竟不是游戲,它應當起到社會良心的作用。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處在社會精英的地位,筆下的文學作品對社會風向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就不能什么都不關心,什么都是玩,就不能淪為商品經濟和大眾文化市場的奴隸,成為無主見、無思想、無個性的精神盲流。
盡管新時期問題小說有諸多的不足,但瑕不掩瑜,洋溢在作品中的作家的熱情,對社會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對于今天的文學來說,是彌足珍貴的,是一份寶貴的遺產。它與“舊文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不將文學當作“失意時的消遣或得意時的玩意”,[7]而是作為一種與現實人生密切相關的事情。生活在一個政治權利、公民權利還有待擴大的社會,我們應該首先爭取這種公民權利,而不是一味沉浸在個人娛樂的世界,沉浸在虛幻的自由、自我表現中。上世紀八十年代問題小說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積極的擔當意識在現在看來是如此的可愛與寶貴。中國社會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獻計獻策來解決,當我們享受社會給予的權利時,別忘了自己身上還擔當著一份責任。
注釋:
[1]劉心武:《班主任》,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版。
[2]羅長青:《過渡時期的創作訴求——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文學研究》,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3]張光芒:《反思的力度及其局限——重讀<剪輯錯了的故事>》,名作欣賞,2010年,第12期。
[4]常慧林:《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反智敘事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5]王富仁:《摸索著魯迅的靈魂》,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02期。
[6]陶東風:《去精英化時代的大眾娛樂文化》,學術月刊,2009年,第05期。
[7]曹萬生:《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李天玲 浙江溫州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3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