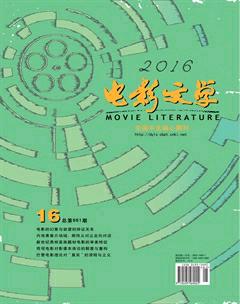1980—1983年電影中的審美體驗
汪弘揚
[摘要]從清朝末年開始進入現代化的中國,隨著社會背景的變遷,對于國人的心理造成了反反復復的影響。特別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劇變,不光是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造成了“斷裂”,也在集體意識和個體心理層面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表現在藝術作品領域,這種時代沖擊所帶來的傷痛尤為顯著。而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關于心理防御機制的相關描述,則可以用來描繪電影創作者的“集體無意識”是如何通過電影作品來表現歷史與個體的相互關系。
[關鍵詞]感憤體驗;潛抑;“新時期”;電影;審美心理
一、感憤體驗的背景
學者王一川在《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一書中論述,晚清之后的中國人由于遭遇了新的境遇,而產生了四種現代審美體驗形態:驚羨體驗、感憤體驗、回瞥體驗和斷零體驗。這四種現代審美體驗形態產生的語境是政治格局的劇變,這與“文革”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內電影藝術創作的語境發生了重合。而這兩個時期的主要區別在于晚清時期的政治劇變是由外部入侵所導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基于“崇洋”之情的“驚羨體驗”和由于國家瓦解所產生的“斷零體驗”。“回瞥體驗”所針對的是中國的古典傳統,并不能等同于“懷舊”,由于缺乏客體,所以不屬于論述范疇。而“感憤體驗”所描述的是一種將個人情感灌注進對時代的控訴之中,“對現實的生存狀況的感世與憤時交織的體驗”。這種體驗在1980—1983年的電影作品中被大量地表現出來,成為“傷痕”風潮下的重要分支和體現。因此,通過討論“感憤體驗”在電影作品中的表現,能夠發現這一時期的電影創作在中國電影的歷史脈絡中呈現出的某種歷時性特征。
二、感憤體驗的潛抑
自1979年以后,中國電影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美國著名電影理論家安德魯曾在《電影理論概念》一書中用這樣的語言描繪當時中國電影的景象:“中國電影在80年代已經達到一片富饒的三角洲,那不過是因為你們現在能明確表達始終與你們同在的那條論述之河的沉淀之物。即:對具體影片的偶發批評;制作訪問記;生產領導同作者的討論。”①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展開的電影理論爭鳴則成了這條“論述之河”的“開源之流”。在這次電影理論爭鳴中,可以概括出兩個被提及頻率很高的關鍵詞:“現代化”和“回歸現實”。“現代化”一詞的提出涉及當時的電影創作者對于電影語言的具體運用和對于電影本體觀念的認識;“回歸現實”則是當時的電影創作者在對于“文革”時期電影創作“假、大、空”的風氣的批判和反省的基礎上所提出的。
而“現代化”和“回歸現實”的共同背景就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盡管這場浩劫在政治和經濟上所造成的災難正在被不斷地糾正與彌補,但是在人們精神上的創痛卻一時難以消去。對于電影藝術來說如何在對歷史進行反思的同時,又能夠盡可能地不去觸碰那一道內心的“傷疤”呢?一般來說人們會盡可能地采取回避和壓抑等手段去避免痛苦感受的再次生發。因此,為了既在作品當中將個人情感灌注進對時代的控訴之中,又避免直觀的影像刺激內心深處關于苦難的回憶,于是,作為一種心理防御機制,采取“潛抑”的策略成了較好的選擇。
三、潛抑的手段與表現
在1980—1983年的電影創作中,比較典型的使用“潛抑”策略的場景是電影《小街》中出現的作為畫外音的“剪刀聲”。“剪刀”削去了女主角的長發,剝奪了女性的關鍵性別特征,致使女主角出現了性別認知的危機(“不男不女的樣子”),而那些操縱“剪刀”的剝奪者的形象,并沒有被完整、清晰地展現。因此,在這一場景當中,導演通過一種“粗線條”的描寫方式來表現對于關于過去經歷的苦難的回憶和控訴,反映了當時那些歷經折磨的電影藝術創作者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無意識”策略的顯著特點就是將災難的根源設置為一種模糊甚至是缺席的狀態,這種策略被集中運用在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上。
在1980—1983年的電影創作中,有兩個主要的手法經常被用來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首先是“推鏡頭+畫外音”的組合方式,在《天云山傳奇》《人到中年》等多部影片中經常出現這種表現手段。對于大量使用這種手段的原因,又要提及之前所說的兩個關鍵詞——“現代化”和“回歸現實”。謝晉在《〈天云山傳奇〉的導演闡述》中認為:“以人物的心理線索來結構電影,這是電影語言的新發展。人物想到哪里,畫面與畫外音就可以表現到哪里。”②在視覺上,“推鏡頭”所帶來的視覺變化,能夠產生一種逐漸逼近人物甚至是深入人物內心的幻覺,即通過空間距離的推進產生“認同”的效應。在聽覺上,將人物的內心活動通過“畫外音”的手段加以展現,通過“獨白”的聲音營造出一個其敘述之不可見均假定為已知的空間,使其符合人們將心理活動視為抽象層面的感知經驗。這兩種手段的結合運用,將觀眾的視聽感知吸引到主體身上,從而在影片當中突出人物的主體意識,并將歷史和對于災難的記憶推至背景,進而試圖消解“揭傷疤”所帶來的痛苦經歷。
第二種比較常見的表現方式是將“象征物”和所營造的“特定情境”結合起來。美國電影理論家梭羅門在《電影的觀念》中認為:“電影有兩種基本方法可以用來在視覺上描繪人的內心狀態。第一種方法要求用象征的東西代表內心的活動。由于敘事電影表現的形象始終是現實主義的,因此電影創作者不可能常常找到一套既不過于刻板又不過于曖昧的象征模式。因此,第二種更有成果的方法,是創造一種環境來明顯地體現某個具體人物的態度,從而暗示他的內心狀態。這種方法自然要使用攝影機和剪輯技術,把客觀地拍下來的現實變得像是某個特定人物眼中的世界。”在《小街》這部影片中,特定情景的設置與劇情的相關性緊密,表現手段多元化。例如,影片中在表現女主人公由有頭發到失去頭發的心境變化時,設置了一個獨立的場景,先是通過背景的顏色由鮮艷到晦暗的變化來表現人物內心的變化,然后是通過裹住身體的白色綢布、破碎的鏡子和剪頭發的聲音來外化人物內心活動,暗示頭發的失去給女主人公帶來的打擊。在電影《沙鷗》中,主人公出現在圓明園的場景也采取了這種表現手段,不過其中運用了蒙太奇的剪輯手段并結合了畫外音的表現手法,使影片的時空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來回游弋,從而表現出人物的內心不斷地在美好的回憶與殘酷的現實中穿梭。這樣的手段明顯削弱了形式表現的痕跡。在這個場景中還大量出現了圓明園中殘垣斷壁的鏡頭,不僅點明了影片中蘊含的民族精神的主題,還通過勾起主人公回憶的方式暗示出人物內心的破敗不堪。這樣,通過具有象征性含義的替代物或是“特定情境”,既能完成主體感受的宣發和情緒的渲染,又可以恰如其分地規避對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痛苦記憶的抵觸心理。
四、結語
在1980—1983年的幾部代表性作品中,隨著創作者的主體意識增強,人物的內心活動成了重要的表現對象,通過各種表現手段將人物內心活動進行外化,從而揭示出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與人物命運的互動關系,并對社會環境下個體的生存狀態展開思考,體現出一種復雜的、具有立體化視角的對于社會生活和歷史的觀察。這樣,影片不再只是一種對于現實狀態的反映,而通過對人物內心的展現抒發創作者對于整個時代的思考。而這特殊時代背景下的“感憤體驗”也被當時的電影創作者通過“潛抑”的方式在這種個體與歷史、民族的交織中顯現出來。
注釋:
① [美]達德利·安德魯:《電影理論概念》,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作者序。
② 謝晉、黃蜀芹、廖瑞群:《〈天云山傳奇〉的導演闡述》,《電影通訊》,1981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 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 [美]斯坦利·梭羅門.電影的觀念[M].齊宇,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3] 陳旭光.影像當代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 戴錦華.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