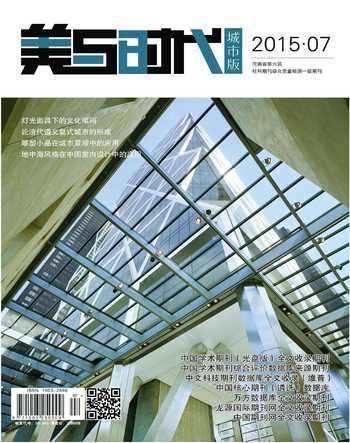論清代遵義復式城市的形成
韓笑 文竹
摘要:復式城市即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筑有城墻的獨立部分組成的城市。復式城市作為中國古代城市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城市形態,其原因主要出于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的需求。我國歷史名城遵義,僻處祖國西南一隅,其城池建設肇始于明,經營于清,最終在清中后期形成了典型的“拓展型”復式城市。其發展歷程也折射了中國古代因政治而建、因經濟而興的復式城市的歷史。
關鍵詞:清代;遵義;“老城”;“新城”;復式城市
貴州歷史名城遵義僻處祖國西南一隅,被歷代統治者視為“羈縻地”、“化外之區”。因此,“(遵義)自治瞥以來,城郭之修未矣。幾經分徙,殘壕廢堡,荒蔓難尋。平播后,分邑定治,興版筑。”
一、遵義“老城”的形成
戰國時,遵義在夜郎國東北,“城跡方圓里許,中有獅子碣,古樹蓊蔚,人不敢伐。”秦代,遵義屬瞥縣。“今貴州遵義府府城西,有鄨縣故城。”唐宣宗十三年,南詔侵入播州(遵義舊稱),太原人楊端請兵將其擊退,據播州為已有。“熹宗乾符三年(876),楊氏建邑于白綿堡。而南宋淳熙三年(1176),播州楊氏第十二代統治者楊軫將堡寨遷到環境較為優越的穆家川,據道光《遵義府志》記載,楊軫“病舊堡隘陋,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為湘江。堡在今府治南二十里無疑。”穆家川所在地,即今遵義“老城”湘江之濱。這為遵義市成為黔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礎。
南宋年間,歷來被視為“羈縻地”的遵義城市雖然得到較大發展,但仍然極其有限,穆家川始終沒有修筑城垣,播州人“所居無城池之固,架木為閣,聯竹為壁。”“雖稱州號,人戶星居,道路崎嶇,多阻巖壁。”
明季以后,明廷對播州實行“改土歸流”,并將播州一分為二:平越府和遵義府。遵義始設府治、筑城郭、治郡城。遵義城市規模初具,是為“老城”的起源。“城垣西南繞山顛,無濠,東北臨湘江為池,前后俱高三丈,長九百五十丈四尺,垛口一千七百八十二。設門四:東宣仁門,南陽明門,西懷德門,北望京門。各門建樓于上,有更鋪三十間。又別開小東門,后閉。”
明清之際,社會動蕩不堪,遵義府城城垣遭到損毀,但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縣唐秉琰才重修了遵義府城,共耗銀二萬一千五百九十七兩。 “周圍一千三百七十一丈四尺,計七里六分,高一丈五尺,厚七尺,將臺一,炮臺十二,槍眼九百九十九。四門:東景福門,西懷德門,南通貴門,北寧永門,城門上均建有箭樓。除四道城門外,小門三,一在東門左,一在西門左,并置柵,不通行。一在東門右,瀉西門溝之水,通人出入,置柵兵,以時啟閉。西門今塞,其小門當水入之沖,外即重山疊嶂,峭險無路。”至此,遵義“老城”形成,并在府城東門外形成了附郭街區。
二、遵義“新城”的修建
遵義老城對岸聛睨相視曰“新城”,始無之。清乾隆初年,知府陳氏自家鄉山東歷城引進山蠶,遵義絲綢業始興。此后,來遵“抱布貿絲”的商旅絡繹不絕,致使遵義經濟迅速發展。手工業和商業的繁盛促使遵義府城東門之外興隆、澤門、白田三黨為往來川黔的必經之地, “居民沿緣稠處設立街道,商號毗連,亦號繁盛。”
咸豐四年(1854),黔省爆發“咸同起義”,農民楊隆喜率眾來遵。東門外的附郭街區,因為缺少城垣的保護,遭到戰火侵擾,居民逃散,房屋焚毀。咸豐七年(1857),清軍驅逐了楊隆喜的起義軍,收復了府城東門外的附郭街區。此后人口雖然增加,黔省苗教兩匪又起,府城東門外的附郭街區又再一次受到威脅。
遵義知縣江炳琳害怕起義軍再次襲擊城外三黨,決議興筑城墻,遂“審度地勢,非旁河險要處筑建城垣不足以資保衛府城,乃集諭紳民,詳請巡撫設局勸捐,檄張朝輔董其役。”咸豐八年(1858)二月動工,次年十一月竣工,共耗時一年零九個月。“新城”建成,共用人工四十余萬,耗資三萬余。“新城”建成后,城垣周長共九百余丈,“東起鳳朝關,包桃源山,迤臨湘水,溯江岸直達萬壽橋,上登青玉案,緣圣廟后山,直抵筆花峰,繞雙薦山回接周鳳朝關。”
新城建成后,其城與郡城“隔河對峙,雉堞相望,犄角相恃,有警不易窺視,永為嚴疆之保障矣。新城分設千總駐防,以資彈壓。”為了與舊城加以區別,稱此城為“新城”,府城為“老城”。
三、遵義“老城”、“新城”的并立
清中后期,遵義復式城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府城城外街區的基礎上逐漸演變而成。
乾隆三年(1738),隨著山東籍知府陳氏在遵郡推廣山蠶,府城手工業、商業始興。此后,省外商賈紛至沓來。府城內以公署衙門為主的行政區難以滿足大宗貨物運輸的需要,尤其是在城市道路狹窄,市區貨物運輸極為不便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相對于城內,府城東門外臨近川黔孔道,更有利于遵義絲綢貿易的長距離開展。另外,“在城市進行商業活動很有可能是一種‘原始傾向,因為它比較符合商業發展的需求,居住成本也較為低廉(相對于城內)。”因而前來遵義從事絲綢貿易省外商賈通常聚集在城外。府城東門外鳳朝關側分別建有江西會館(萬壽宮)、湖廣會館(禹王宮)以及在萬壽橋“兩旁修建屋,集商貯貨”均可證明此點。
隨著清中前期,遵義社會經濟的逐步恢復和發展,城市人口在不斷增加。據道光《遵義府志》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遵義府城共有人丁四千三百五十,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府城人丁共計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八人。增長了三倍有余,城市人口密度在不斷增加。“總的來說,容納增加人口的主要途徑仍然是擴張城外街區,而不是增加城內的居住密度。”
在多種因素合力推動下,遵義府城東門外在康熙年間被大火燒毀的城外街區在此時已日益繁盛,并形成了三黨十二坊,可謂“居民數千家,舊稱繁盛。”時有興隆黨坊七:效靈、儒林、吉慶、息波、香桂、清香、太平;白田黨坊三:聞韶、承恩、旺澤;澤門黨坊二:籌邊、生意。對比府城內部的街坊而言規模較大(城內有東黨坊三:積善、豐樂、宣威;南黨坊二:崇孝、朝天;西黨坊一:仁壽;北黨坊二:春臺)。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成為此時遵義府城城外街區復興至關重要的動因。
當城市處在動亂時期時,城外街區往往因缺乏城垣保護遭到較大的破壞。在貴州“咸同起義”期間,府城東門外興隆、澤門、白田三黨備受農民軍戰火摧殘,居民四處逃散,房屋盡被焚毀。清軍鎮壓了農民起義后,三黨街市稍復,遵義當局遂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集結各種可供利用的資源修筑城垣,將三黨包圍在其中。同治四年(1865),白蓮教“號軍”首領宋玉、王廷英駐雷臺山、白崖溝攻打遵義府城,“新城”因有城垣的保護幸免于難。可見,“新城”的修建是在城外三黨面臨安全威脅和動亂之后采取的安全措施,軍事防御和地方控制是修筑城垣的主要動因之一。
“晚唐時期,尤其是南宋以后,隨著城市管理開始放松,許多城市在城門外形成了附郭街區。出于對附郭安全的關心,在一些比較重要的城市構筑了新的城墻,從而又把附郭街區圍進城里。”與此不同的是,遵義的城外街區并不是通過擴大原有城墻而將其包圍在府城中,而是另建新的城垣,從而形成與府城并立的格局,屬于“拓展型”復式城市。“新城”筑郭前并不是獨立的城市,而是遵義府城為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擴展的城外街區,出于安全的需要,在其周圍建筑城垣,從而形成“老城”、“新城”并立的格局,即先有治所“老城”一個城郭,然后與其商埠并存,從而形成復式城市。
由上述可知遵義“老城”、“新城”的并立并非受單一因素影響,而是在多種合力共同推動下逐步發展而來。主要表現在,“老城”、“新城”并立的格局是以府城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為至關重要的內在動因,以貴州“咸同起義”為催化劑,最終在遵義當局政治力量的直接推動下才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