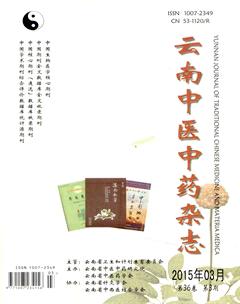《血證論》治療崩漏思路探微
胡幽蘭 藍婧 曾倩
摘要:崩漏是婦科常見病,也是疑難急危重癥。是月經周期、經期、經量的嚴重失調,相當于西醫學無排卵型功血的范疇,多見于青春期和更年期女性。唐氏認為此病的的發生多責之以脾,治法當用補中益氣,升其中州之氣,則水升而血亦升,多選用歸脾湯等補益脾經之方藥。
關鍵詞:《血證論》;崩漏;辨證;治療
中圖分類號:R271. 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5)03-0011-03
唐容川為清代名醫,所著《血證論》醫學理論源于《內經》、《傷寒雜病論》,并有所發展,正如其自序中所說“寢饋于《內經》、仲景之書,觸類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治血證十愈七八。”[1]書中較詳細的總結了血證論治之法,條分縷析,頗中肯綮。時至于今仍有指導意義。
崩漏是月經的周期、經期、經量發生嚴重失常的病癥,是指經血非時暴下不止或淋漓不盡,前者謂之崩中,后者謂之漏下。崩與漏出血情況雖然不同,然二者常相互轉化,交替出現,且其病兇病機相同,故概稱崩漏[2]。在婦科異常陰道流血癥之中,以崩漏最多見,約占婦科門診量的10%,發病人群以青春期和絕經過渡期為主(其中絕經過渡期功血的發病率高達50%)[3],筆者近日研讀《血證論》后,對崩漏的證治有些許心得,現歸納如下。1 辨證不離氣血水火
唐氏在《血證論·陰陽水火氣血論》中提出了水火氣血相互維系,相互滋生制約的思想。唐氏認為“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氣血,水即化氣,火即化血。”[1]1.1 水氣互化關于氣和水的關系,唐氏認為水在臍下丹田可化為氣,氣隨太陽經脈布護于外,成為衛外之氣,此氣上交于肺,成為呼吸的動力;氣又可化生為水,同時這種氣水互化的運轉流注也是作為五臟六腑間相互交流信息與功能相互影響的體現。例如,水借太陽之氣達于皮毛成為汗液;水化氣蒸騰于上是為津液;氣化水流行于下是為溲水。氣和水在生理上能互相維系,水能轉化成氣,氣也能轉化成水。因為“氣生于水,既能化水,水行于氣,亦能病氣”,水與氣相輔相成,相病相患。故唐氏認為,“氣與水本屬一家,治氣既是治水,治水既是治氣”[1]。1.2火能化血關于火和血的關系,唐氏認為火能化為血,血的顏色與火一致,皆為赤色,所謂“奉心化赤”。火為心之所主,心能化生血液,濡養周身。同時火的屬性為陽,陽易亢上,是受到了陰血的榮養制約,火才不至上炎。由火化生的血液下注,“內藏于肝,寄居血海,由沖、任、帶三脈行達周身”[1],發揮其正常的生理功能。生理上,火能化血,火為血制,二者相互聯系。病理上,二者同樣相互影響。血病也可造成火病,如:“血虛,則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動火,心失所養,火旺而益傷血。”[1]火病可致血病,如“血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血。”[1]所以唐容川說:“血與火原一家,知此乃可與言調血矣。”[1]1.3水火氣血相互聯系水與氣、火與血兩對不同屬性的物質相互聯系的關鍵,在于人體之中氣與血的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唐容川說:“運血者即是氣,守氣者即是血。氣為陽,氣盛相互作用即為火盛;血為陰,血虛即是水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氣,調陰和陽,可以左右逢源。”[1]可知,氣血的延伸內容已然涵括了水火陰陽。則唐氏認為“水、火、氣、血固是對子,然亦互相維系故水病則累血,血病則累氣。”[1]2男女分治
唐容川明確否定了“男子血貴,女子血賤”的觀點,認為男女氣血理應相同,而男女生理的差異僅在于“女子有月信,男子無月信”[1]。在對男女生理差異問題的闡述中,靈活地貫穿著唐氏“陰陽水火氣血”的主導思想。他說:“夫必明氣血水火變化運行之道,始可治氣血水火所生之病。”[1]男女由于陰陽屬性的差異,而有屬氣屬血的不同。男子主氣,血人丹田化為氣,氣又化為水,此水為腎精。女子主血,氣在血室化血為月信。自然界有盈虧之理,如月亮有盈虧圓缺,早晚潮汐的漲落,人也遵循同樣的法則。女子每月行經除舊生新,血滿則泄,月信則是血之余。唐宗海認為月信是除舊生新的生理表現,“舊”即是瘀血,“瘀血不生,則新血斷無生理”,因此在治療上他特別重視“去瘀生新之法”。男子多氣多水,女子多血多火。但男子也有血與火,女子亦有氣和水,互根互用,不離陰陽之理。
若血失常道,即為血不循經.在女子發為崩帶之疾,男子發為吐衄。但男子吐衄.是上行之血.女子崩帶.是下行之血,不可同論治之.然女子吐衄,則與男子一樣.男子下血,則也與崩帶無異,故“是書原非婦科.而于月經胎產尤為詳悉.誠欲人觸類引伸.于治血庶盡神歟。”[1]3婦人崩漏,責之中州3.1重在治脾,靈活運用如素體虛弱,或飲食失節,或過勞久思,或大病久病,損傷脾氣,致脾失健運,血失統攝,致血液不循常道而妄行,在婦女可致崩漏[4]。關于崩漏,唐容川說:“古名崩中。謂血乃中州脾土所統攝,脾不攝血,是以崩潰,名日崩中,示人治崩必治中州也。”[1]他認為崩中雖是血病,但其病機則屬于中氣下陷,“水隨而瀉,水為血之倡,氣行則水行,水行則血行”[1]。而在陰升陽降、水升火降、氣升血降的過程之中,脾胃是上述運動的樞紐。他說:“其問運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系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兩藏,全賴于脾。”故提出“治血者,必治脾為主”,“治氣,亦宣以脾為主。”[1]治法當用補中益氣,升其中州之氣,則水升而血亦升。常用歸脾湯加艾葉、阿膠、灶心土。汪昂《醫方集解·補養之劑》:“此手少陰、足太陰藥也。血不歸脾則妄行,參、術、黃芪、甘草之甘溫,所以補脾;茯神、遠志、棗仁、龍眼之甘溫酸苦,所以補心,心者,脾之母也。當歸滋陰而養血,木香行氣而舒脾,既以行血中之滯,又以助參、芪而補氣。氣壯則能攝血,血自歸經,而諸癥悉除矣。”[5]這也充分貫徹了唐氏“止血先治氣”的總原則。從現在臨床來看,有學者用歸脾湯治療崩漏.每收良效[6]。大虛者,宜十全大補湯加阿膠、續斷、升麻、炮姜、酸棗仁、山萸肉,再用魚肚、鹿角霜、蓮子、姜、鹽燉食以調養之,或用黃芪、糯米、當歸煎服以大補氣血。或選用六君子湯、養榮湯、炙甘草湯等補益脾經之品加減應用。唐氏強調“凡是崩中,此為正治。”[1]3.2木郁克土,肝脾同調如若肝氣郁結,木郁乘土或土虛木乘,脾失健運,統攝無權,沖任不固可致致崩漏。《景岳全書·婦人規》指出“崩淋之病……未有不由憂思郁怒,先損脾胃,次及沖任而然者。”五臟中,肝氣易郁,木郁乘土,脾氣受損,脾不統血,沖任不固而致崩漏[7]。唐容川認為婦人情志不遂使肝氣郁結,日久化火,火發為怒,則血橫決,加之木郁克土,脾失統攝,不能制約經血,發為崩漏。治以清肝火,補脾土,面而俱到,使血海寧靜。初用止血,以塞其流佐以清肝瀉火;澄其源,補其中州復其用[8]。選方宜用歸脾湯加丹皮、梔子、柴胡、白芍、麥冬、五味子,或用丹梔逍遙散加牡蠣、阿膠、蒲黃以疏肝健脾攝血,崩漏自除。現代藥理顯示“和肝”,“解郁”方藥具有協調皮質下中樞功能活動,調整中樞神經系統與自主功能神經紊亂,影響多種平滑肌的舒縮調節作用,達到止崩目的[9]。4討論
綜觀歷代醫家對崩漏辨治思路,筆者認為《血證論》的論述較為精當,且集前賢之精妙,其中還不乏個人主張與新意,可供臨床醫師遵循與參考。唐氏認為崩漏主要責之于中州脾土,正如《萬氏女科》云:“婦人崩中之病,皆兇中氣虛,不能收斂其血致”[10],常用歸脾湯、十全大補湯、六君子湯、養榮湯、炙甘草湯等補益脾經之品加減應用,也特別提出木郁克土型崩漏當肝脾同治,常用歸脾湯合丹梔逍遙散加減。當然,也有其不足之處,作者對于腎虛崩漏,沖任虛損所致崩漏等無論及;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環境的變化,生存壓力的不斷加大,病因病機更為復雜,虛實寒熱錯雜,氣血逆亂,陰陽失和等復雜病機將更為常見。因此,臨證貴在辨證不悖,謹守病機,用藥得法,方呵取得滿意的療效。參考文獻:[1]清·唐宗海《血證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2]張玉珍,《中醫婦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106[3]圈培·婦科血證論治[C].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婦科專業委員會第四屆中醫婦科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2011:4-6.[4]萬云慧從脾虛論治崩漏[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 2013,15(4):162.[5]清·汪昂《醫方集解》[M].中圍中醫藥出版社,2009.[6]劉曉英,歸脾湯化裁治療崩漏的臨床體會[J].中國社區醫師,2012,28(7):210.[7]張琦.淺淡從肝論治崩漏八法[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11,18(5):86.[8]孔凡涵.淺談中醫對崩漏的認識及辨治點滴[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2,10(12):10.[9]陳玉暖,丹梔逍遙散治療肝郁血熱型崩漏的體會[J].河北中醫,2004,26(6);603.[10]明·萬全《萬氏女科》[M].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
(收稿日期:2014-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