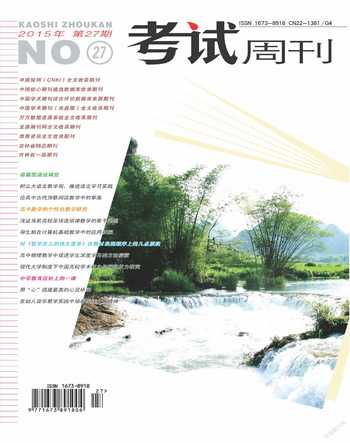構建教師學習共同體,促進食品安全性課程組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張建 朱新榮 陳國剛 董娟 田洪磊 許程劍
摘 要: 信息化時代,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報道層出不窮,從事食品安全性課程教學的教師迫切需要提高專業能力。教師學習共同體作為一種新型合作學習的方式,在教師專業成長中具有獨特的作用。基于此,本課程組教師在分析教師學習共同體的內涵及要素的基礎上,介紹了本課程組教師在構建教師學習共同體中的一些策略。
關鍵詞: 教師學習共同體 教師專業能力 食品安全 高校教育
世界教師組織聯合會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素質,有賴于教師的素質。”[1]高等院校作為培養人才的機構,教師的專業水平、綜合素質等方面直接影響到教育目標的實現和教育質量的提高。然而,高等院校長期施行具有較強的行政化、形式化和個人主義色彩的教研組(室)建制,這種缺乏真正競爭和合作的組織,造成了青年教師的成長動力不足和職業倦怠的現象。同時,高科技沖擊著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各種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在教學中被廣泛應用,一本備課筆記,以口頭講授和板書的形式向學生傳授知識的教學方式,已很難適應現代教育發展的要求。這就促使教師有敏銳的時代意識,不斷學習新知識,掌握新信息,勇于創新,主動探索,跟上時代潮流。20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興起教師學習共同體,這種具有平等的話語權和參與權的學習共同體,對加速青年教師的專業成長起到了明顯的作用。
1.高校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內涵
“專業學習共同體”這一概念廣泛受到關注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赫德指出,專業學習共同體是由有共同愿景的教師和教育管理者共同建構的團隊,他們在學習中共同探究、相互分享、注重實踐,以此達到教師和學生的共同發展。貝克認為,高校中的學習共同體是由學生、教師、管理者和其他有著明確的團隊歸屬感、共同愿景和廣泛交流機會的人組成的團隊,通過協作學習活動項目實現促進教育學的目標。作為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成功實踐的代表人物,邁阿密大學教學促進中心主任米爾頓·克斯教授把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定義為一個由跨學科的教師和學校職員組成的學習項目團隊。教師專業共同體以對學生的發展進步研究為中心,兼以實現教師專業行為的改進和教師在學科內容上持續的知識增長[2]-[4]。
國內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教師學習共同體提出了看法。鐘志賢指出教師學習共同體是為完成真實任務或解決問題,學習者與其他人相互依賴、探究、交流和協作的一種學習方式[5]。張建偉認為教師學習共同體是一個由學習者及其助學者們彼此之間經常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溝通、交流、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學習任務,在成員之間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聯系[6]。
2.高校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要素
2.1自我突破
自我突破是指能夠使自己的能力或者技巧得到較好的展現。如同藝術家對藝術作品一般,全心投入、不斷創造與突破,是一種真正的終身“學習”。教師專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教師智慧的生成,其重要內容是自我激勵、情感整理,主動定標和增強注意力與創造力。教師成為一名合格、成功的教育者的過程,就是一個人不斷豐富和完善主觀世界的歷程,是充分地挖掘自身具有的強烈自我發展與自我突破能力的過程。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能夠為教師提供學習新思想、新觀念、新知識,實現自我突破的機會[7]。
2.2合作文化
教師文化指“教師這個特殊群體的有特色的價值—規范系統”。能夠使教師在民主平等的氛圍中超越純粹的個人反思和對外來指導的依賴,轉向相互學習和交流分享,進而增強教師的自信,確定發展方向,推動教師個體發展和學校改革的深入。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核心是合作文化,這種有效合作的文化氛圍是以分享、信任、支持和日常工作為中心,以共同的工作和促進成長為特征的。教師共同體是典型的合作文化中的學習型組織,它要求共同體成員有改進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共同愿景,成員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而相互支持和合作,在合作中對改進教學和自身學習不斷進行反思性的專業探究,從而真正做到自我反思、同伴互助、專業引領和持續學習[8],[9]。
2.3開放模式
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教師的發展是個人的事,這種“孤軍作戰”的方式嚴重阻礙了教師的專業成長。教師必須意識到,目前知識激增、更新速度不斷加快,以個體的方式獲取的知識必然十分有限,即所謂的“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只有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教師專業發展才能開發個人最大的潛能,匯聚團隊力量。就教師個體而言,就是要開放個人的內心世界,實現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交融,如果更積極地吸納周遭的新知識和新信息,那么學習就是優化和完善最具體的方式,通過形形色色的學習過程,個人既能從新實踐體驗中重新檢視原有的內容和結構,又能吸收新知識補充和擴展原有的知識結構,并在不斷實踐過程中修正信念體系[10]。
2.4共同愿景
沃倫·本尼斯認為:“在人類組織中,愿景是唯一最有力的、最具激勵性的因素。它可以把不同的人聯結在一起。”共同愿景是組織成員心中共有的愿望景象,由個人愿景整合凝聚得來,是組織中每個成員深受感召的力量,它能夠激發強勁的凝聚力、驅動力和創造力,培養改革創新和一往無前的精神。在博耶爾看來,學習共同體是所有人因共同的使命并朝共同的愿景一起學習的組織,共同體中的人共同分享學習的興趣,共同尋找通向知識的旅程和理解世界運作方式,朝著教育這一目標相互作用和共同參與。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使每位教師都處于具有凝聚力和共同目標的方式中[11]。
2.5團隊對話學習
團體學習對個人的學習會起到推動作用,當團體真正在學習的時候,不僅團體整體產生出色的成果,個別成員成長的速度也比其他學習方式要快。學習是他人的思想與自我見解之間的對話,基于對話的團隊學習使成員彼此共享知識、經驗、智慧、生活意義及生命價值,并在共享中相互造就。佐藤學認為,學習者在通過與客體的對話、他者的對話和自身的對話中獲得當下的人生意義,并最終走向自我完善。在教師學習共同體中,對話雙方都將對方視為知識的可能性源泉,通過對話和共同的探索活動將公共知識轉化為個人知識;共同體通過互動將個人難題轉化為公共難題,借助集體智慧解決個人困境,從而構成了一種加速個人智慧學習和實踐創新的良性循環[12]。
3.構建食品安全性課程組教師學習共同體的策略
3.1構建教師共同體的共同愿景
目前食品安全性課程組共有六名教師,另外聘請了一名老教授作為指導者,在老教授的指導下,全體課程組成員追求個人愿景及全員參與并溝通探討的基礎上,全體課程組教師明確了共同的愿景,例如:一年內、三年內要把食品安全性課程建設分別建設成什么級別的課程;由課程組組成的教學團隊要建設成一支什么樣的教師隊伍;某一次教研活動要實現哪些目標,等等。有了共同愿景,食品安全性全體共同成員就精神振奮,并不斷促進自己的成長和超越,目前食品安全性課程已經成為大學一類課程,食品安全課程群建設也得到了大學的資助。
3.2創建積極和諧的共同學習氛圍
近三年來,食品安全性課程組通過以下三種方式積極創建和諧的學習共同體環境,首先課程組負責人積極轉變領導方式和觀念,親自加入課程組不同形式的共同體,如,親自舉辦學術講座,親自舉行示范課,親自參與課程組的教研活動等;其次,課程組成員之間關系做到融洽、氣氛民主,如老教師經驗較豐富,青年教師思想較活躍,在學習中共同相互促進;再次,合理分工,讓每個人均能體驗到合作的快樂,如集體備課中可以輪流做中心發言人。三年來食品安全性課程每年都是大學的優質課程,同時課程組3名教師獲得大學教學能手稱號,1個獲得了大學師德標兵稱號。
3.3積極創造對話機會
近年來,食品安全性課程組充分利用大學、學院及自身創造的機會,增加與名師、老教授和專家對話的機會,提高其專業能力。第一,組建與名師學習共同體,通過學校的對口支援制度,聘請對口支援高校的名師來校任課,全體課程組教師全程聽課并交流,創造與名校名師的對話機會;第二,組建與校外專家學習共同體,一是充分利用院每年舉辦的學術交流會議,二是利用課程組全體教師申請到的大學外出學習機會,創造與校外專家對話的機會;第三,組建師傅與徒弟學習共同體,根據教師的專業發展差異,以自主、自愿為原則,找一些相對應的專業能力強的教師或專家與其組建師傅與徒弟學習共同體,實現定向對話。三年來,課程組教師利用大學、學院及自身的機會,累計聘請6名教師來校任課,聘請30名專家來校交流,外出學習交流20余次,課程組全體教師已經與名師或專家組成了師傅與徒弟的學習共同體。
3.4建立健全共同學習機制
教師學習共同體是建立在其成員主動自覺地學習的基礎上的,而其自覺性并不是自發的,其成長需要經歷由他律到自律的過程,配以制度保障是完全必要的。目前食品安全性課程組通過以下制度確保教師學習共同體的持久性。首先,根據教師發展的需要構建共同體組織,如組建備課組和專家組等;其次,給成員提出明確要求,如公開課、讀書報告會、專題討論、課題研究的次數、內容等,目前食品安全性課程教師要求每周進行一次教學學術交流,每學期寫一份評課材料,每學年撰寫一篇專題研究論文,青年教師和骨干教師每學期分別上一節匯報課和示范課等;再次,建立相應的考核機制,課程組聘請院專家引領的考核小組對教師進行發展性考核,制訂如首席教師、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的評比方案。通過以上制度的執行,使食品安全性全體教師從“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
4.結語
食品安全性課程組教師學習共同體的建立,作為一種學習方式,提高了課程組全體教師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增進了教師之間的信息交流與協作,提高了群體努力的滿意度,使個體從共同體成員的互動中獲益。學習共同體使教師工作不斷超越自我已有水平,給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使教師的工作更具創造性,使教育教學工作成為展示教師生命價值的方式和途徑。學習型團隊讓教師在相互間的交流與溝通中獲得心理支持,通過分享材料、計劃和資料,減輕負擔,共同營造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從而促進自身的專業成長。
參考文獻:
[1]王梅.淺談教師的職業素質[J].科技視界,2013(23):129.
[2]趙健.學習共同體——關于學習的社會文化分析[M].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6.
[3]郭書法,夏娟,張海燕.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專業學習共同體[J].寧夏社會科學,2014,1:157-160.
[4]詹澤慧,李曉華.美國高校教師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對話美國邁阿密大學教學促進中心主任米爾頓·克斯教授[J].中國電化教育,2009,10:1-6.
[5]鐘志賢.知識建構、學習共同體與互動概念的理解[J].電化教育研究,2005,11:20-24.
[6]張建偉,孫宴青.建構性學習——學習科學的整合性探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7]肖川.教師:與新課程共成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8]教育部師范教育司.教師專業化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9]馮生堯,李子建.教師文化的表現、成因與意義[J].教育導刊,2002,7:32-34.
[10]熊燕,王曉蓬.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內涵及生成要素[J].當代教育科學,2010,3:29-31.
[11]唐宗清,等譯.領導合作型學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2]魏會廷.教師合作文化視域下高校教師專業學習共同體的構建[J].安康學院學報,2012,3:110-112.
基金項目:石河子大學教育教學改革項目(JG-2012-051);石河子大學青年骨干教師培訓項目(3152SPXY01027)
通訊作者:朱新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