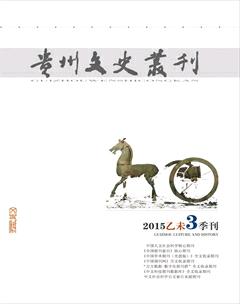關于《明夷待訪錄》中所體現的黃宗羲政治哲學思想的研究
賀志韌
摘 要:《明夷待訪錄》是我國明代末期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撰寫的一本蘊含了豐富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著作。該書總結了明朝衰亡的經驗教訓,通過對上古三代及三代以后的政治體制的比較,對秦漢以后,尤其是明代的封建專制體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和批判。認為將“天下人之天下”變為“一家一姓之天下”是造成天下百姓貧困及封建王朝自身衰亡的根本原因,進而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和“君為天下之大害”的重要思想,具有先進的現代啟蒙思想特色。其所推崇的“三代之法”實際上即是西方世界所倡導的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自然法”。另外,該書中還具有大量類似社會契約論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認為沒有君主的公民社會是最健康最合理的社會,人們會自發地按照自己和他人的需求組織成一個健全、有效的社會職能體系,具有鮮明的現代色彩,非常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參考。本文將就《明夷待訪錄》中所體現的黃宗羲的政治哲學思想進行梳理和發微,總結其特色,并評價其優劣。同時參照在其之前的類似思想觀念以及國外的相關思想理論進行對比和分析,以圖達到對這一思想獲得較為深刻、全面的認識和把握。
關鍵詞:啟蒙 自然法 社會契約論 封建專制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5)03-79-84
《明夷待訪錄》一書是黃宗羲在其生命的晚期所作的,成書于清代康熙二年(1663)。其成書原因和目的是黃為后世準備的開萬世太平的“為治大學”。“明夷”一詞出自《周易》中的“明夷”卦,卦象為上卦為坤卦,下卦為離卦,地在火上,日沒地下,意指暗主在上,明臣在下,即對封建君主專制的諷刺和抨擊。“待訪”是指等待后人的考察和吸取經驗教訓。此書因其過于激進的思想,在清代乾隆年間被長期列為禁書,直到晚清維新變法之際,才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從故紙堆里發掘出來,“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使之廣為流傳,為當時的資產階級改良實驗提供了重要參考和理論服務。該書現在所存篇目不全,僅余二十一篇。內容涉及到政治體制、教育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制度等多個方面,均是為治國理政、富國強兵所提的建議。其中《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篇專門闡述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體制改革主張。
一、《明夷待訪錄》中的人性思想
人性論幾乎是一切政治哲學思想的基礎和前提,因為政治是建立在個人的基礎之上的,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由一個個單個的個人組成的,政治哲學要體現出意義,就必須要首先對人的普遍性和個別性進行討論,尤其是普遍性。比如老子認為人生來就是貪圖美色、美食、美好的音樂等物質享受,所以他說“五音使人耳聾,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口爽,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他還認為人一有思想就會對君主的統治表示不滿,會亂發議論,從而不利于統治的維持、社會的安定,所以要“絕圣棄智,使民無知”,所以要“裹其腹,而虛其心,使民可由而不可知。”孔子認為人生來就有仁愛之心,但同時又有貪欲,所以要“約之以禮”“治之以德”。孟子認為人性本善,要想富國強兵就必須推行讓人民安居樂業、道德素質提升的王道政治。孔孟的思想成為先秦以后的儒家思想的正統與核心,被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所推崇和繼承。黃宗羲作為浙中王門的后期代表,卻并不持有該種觀點,而是支持荀子、韓非子的“人性本惡”的觀點。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后天的成長中通過社會交往不斷地克服自己的貪欲,使自己向善,國家要通過制定禮法來約束個體的私欲。韓非子持有同樣的觀點,他說賣珠寶的商店老板希望他人富貴,而賣棺材的老板卻希望他人死亡,并不是前者本性是善的,后者本性是惡的,而是因為他們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希望自己能夠從中牟利而已。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提到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句正是對這一觀點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表達。
“利”的觀念在重農抑商、推崇“仁義”之學的古代中國,一直未能受到普遍的重視和認可,反而受到排斥和打壓。孔子在《論語》中明確地說道:“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說:“王何必曰利,唯有義而已矣。”將“義”和“利”放在鮮明的對立面上。這些圣賢的話語被后世幾千年的儒學家奉為圭臬,并演變成教條,始終貫徹于主流意識形態之中。雖然在宋代浙學的永康學派和永嘉學派中以陳亮和葉適為代表的一部人重新劃分了“義”和“利”的關系,將“義”和“利”視為有機統一體,而非對立矛盾體,從而將“利”推向一個積極、崇高的地位,但對于整個中國,封建王朝的影響卻是極為有限的。“利”的觀念在中國雖然一直未能受到重視,但在西方世界里卻一直占據著重要,甚至是主導的地位。除中世紀受基督教倫理思想的影響,“利”的觀念不被普遍認可以外,包括古希臘哲學和文藝復興以后的啟蒙思想及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倫理思想在內的整個西方哲學,都是對此持十分重視和肯定態度的。“利”的思想本質上是承認人的欲望的正當性和必然性,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就有大量關于如何使個人發財的論述。英國的啟蒙思想家霍布斯認為人生來是自私的,“人對人是狼”。人因為物質需要的匱乏會不斷地向外擴張,從而就會觸犯別人的利益。當大家都勢均力敵的時候,為了保證每個人的利益都不受侵犯,就必須互相做出妥協和讓步,這就形成了法律和規矩。法國的盧梭認為最好的社會形態就是人與人之間形成共同的契約觀念,大家共同遵守,各自享有應有的權利和義務,這樣社會就能平穩、和諧地發展,人民就能安居樂業。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認為人生來是自私自利的,他說我們每天所獲得的食物和飲料不是來自屠戶、面包師和釀酒家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他的這一思想被約翰·穆勒總結為“經濟人假設”,亞當·斯密依次認為只要每個人都最大程度地區實現自我利益,社會生產的最大潛力就會被激發出來,人與人之間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相互競爭又相互妥協的動態的和諧關系,這對國家的發展是起決定作用的,他稱之為“看不見的手”,即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黃宗羲的觀點與荀子、韓非子、霍布斯和亞當·斯密的觀點十分類似,他在《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中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1〕指出人的本來面目即是自私自利的。但是黃宗羲對于人性的理解不僅僅是這么簡單作出界定,而是從道德假設的層面作了進一步的延伸。他假設大多數人是自私自利的,但是還存在著一小部分人與眾不同的人,也就是圣人,他們首先考慮的不是個人利益的得失,而是天下人利益的得失。黃宗羲進一步從人的能力方面來推導,認為雖然圣人有這樣好的出發點,但是由于天下人有千千萬萬,因此圣人的辛勞也就必定是普通人的千萬倍。比普通人辛勞千萬倍,自己卻絲毫得不到一點回報,即便是圣人也很難堅持下去。所以才出現了像許由、務光這樣經過各種考量而放棄了堯和湯的禪讓的隱士;出現了像堯、舜這樣的雖然一開始滿懷熱情地積極參與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卻最終難以繼續,而將帝位禪讓給他人的帝王;出現了像大禹一樣的雖然一直勤政到死,一開始卻是迫不得已被推到帝位上的君主。因此黃宗羲總結說,可見雖然自私自利并非是一切人所共有的秉性,但好逸惡勞卻是人之常情。而好逸惡勞實際上還是自私自利的表現。這里,黃宗羲所談到的自私自利顯然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所認為的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的自私自利,而是一種中性的,認為人有維護其自身基本生存、生活和休息的物質、精神享受的權利。黃宗羲從人性的落腳點出發,把人分為普通人和圣人兩種,并從開始的動機和事后的心理兩處對上古圣王這一特定人群進行考察。實質上否定了傳統儒家所一貫推崇的堯、舜、禹三個圣王的絕對神圣性和道德性,從而最終對他一開始所設立的人分為普通人和圣人兩種的假設進行了全盤推倒,最終認定人性本質上就是自利的。endprint
二、《明夷待訪錄》中對君權的批判
黃宗羲對君權的批判是建立在其經濟思想上的,即“產業”論。明代末年,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沿江沿海一帶的大城市出現了類似于西方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經濟形態,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出現了趨向工廠化的大型手工業作坊。這一特征在黃宗羲所在的江浙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隨著市民階層的興起,市民心理和市民文化越來越普遍地反映出來,大量的文人不再將科舉取士作為唯一的職業理想,而是轉而從事職業教師或商業貿易等職業。“三言二拍”、《金瓶梅》這種表現市民生活的大型文學作品應運而生。以董其昌、陳洪綬等為代表的藝術家也不再局限于“文以載道”的藝術表現形式,而是更多地將視線轉向于對世俗生活的細節和情趣的描繪和表達,這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發展趨向也是極其吻合的。
市民階層的興起顯然影響了黃宗羲的價值取向,他將“天下”一詞由傳統的政治定位改變為經濟定位,稱之為“產業”。傳統的“天下”的概念是指政治上的領土主權,強調對某塊土地及依附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絕對支配。對這一觀念的最佳詮釋就是《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即中國古代的傳統觀念是認為“天下”唯一的主人、唯一的主體是君主,君主享有對國家領域范圍內的一切領土和一切人民的絕對支配和占有權。即人民群眾從根本上來說是皇帝的奴隸,他們只有在他們自身內部才享有關于平等、民主、自由這些問題討論的話語權。黃宗羲沒有從這種傳統的政治角度來看待“天下”這個概念,而是認為“天下”代表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土地和人民,而是代表了這塊土地上所產出的一切資源和商品,它的根本意義在于對物質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源的支配,這種觀念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是相符的。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關系根本上還是要落腳于社會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決定歷史走向的根本力量。在黃宗羲的觀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質上說的是君主一家一姓對全國的勞動生產力和生產資源的絕對占有權和分配權。他認為這是極其不公道的。這種觀念類似于莊子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思想,即認為君主是竊取全體國民經濟利益的江洋大盜、罪魁禍首。黃宗羲認為在上古三代的時候,天下的產業是屬于全體國民共享的,大家“各得其私,各得其所”,是一種“大道行也,天下為公”的黃金時代狀態。而三代以后,隨著君主專制的確立,天下的產業就由天下人所共有的公產轉變成了皇帝一家一姓的私產了。他認為這是歷史的極大倒退。為了證明他這一觀點并非是想象虛擬的,黃宗羲還以漢高祖劉邦所說的“某業所就,孰與仲多”來為自己論證,認為“其逐利之性不覺溢于辭矣”。
他不但從宏觀理論上對君主專制將天下人的產業變為他一家之產業外,還從人的心理發展過程的細節中揣摩君主的心態,認為君主剛開始霸占天下人的產業的時候可能還心里多少懷有一絲歉疚,表面上要表示出自己是來幫助大家管理產業,久而久之卻會將之視為理所應當,而心安理得了。他說:“后世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2〕把君主貪得無厭、自私自利、恬不知恥、異想天開的嘴臉刻畫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因此得出一個驚世駭俗的結論,即“然則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實際上,上古三代的情況并不見得有黃宗羲想象的那么好,當時人們的物質生活極端不富裕,不可能有大量的物質財富集中在君主一個人的身上,因為他首先要保證國內除奴隸之外的一切公民的基本生存能力,才能去進行剝削和壓迫,不然統治是無法維持的,這就造成了上古三代“天下為公”的假象。實際上,如果當時真的是如黃宗羲所說的只有極少數的人有興趣為大家服務,那么大禹和湯就不會將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形成家天下的局面了。從夏桀和商紂的荒淫殘暴上可以看出,當時已經出現了大量物質財富向君主集中的情況,而正是由于當時物質財富還很不富裕,大量的資源被君主掠奪過去就會造成全國百姓的生存危機,這才會導致他們亡國的。從大禹召開諸侯首領會議,將遲到的諸侯處死,并鑄造九鼎來象征對天下九州的統治,以及他的兒子啟在攻伐有扈氏之前所頒布的《甘誓》中可以看出,當時君主已經擁有了對臣子和人民的絕對控制和支配的權力,而非是櫛風沐雨、任勞任怨地為他們服務。黃宗羲之所以這樣宣揚當時社會的各種美好景象,無非是繼承儒家一貫的借古諷今、托古改制的傳統,一方面為人們提供一個看似鮮活的參照,不至于停留在空想的層面;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激發人們對今天還不如以前的歷史倒退的憤怒感和逼迫感。
黃宗羲除了認為君主專制會對天下百姓的利益進行侵犯之外,同時還認為這一制度對它所要維持的封建王朝自身也是埋伏下的一顆致命的定時炸彈。因為把整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家一姓的肩膀上是極其荒謬和危險的,它要求每個繼承人都必須具備協調、統籌全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局面能力的高難度的本領。開國的君主可能會憑借他長期的領導組織經驗和威望而實現穩定、有效的統治,但是他的子孫未必有這個能力和威望去領導一個龐大的國家和官僚體系。尤其是如果中間出現一個無能、昏庸的君主,他很有可能把祖先辛辛苦苦積下來的基業揮霍一空,令整個王朝處于癱瘓狀態。而作為他后面的王朝繼承人以及旁系的皇室成員和皇族后裔則要受到牽連,為他的錯誤買單。最后整個國家會在農民起義或外敵入侵的打擊下滅亡,而皇族子孫、即便是剛剛出生的幼童都要面臨滅頂之災的殘酷命運。他說:“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子孫矣。昔人愿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 摧沮者乎!”〔3〕生動地引用了宋順帝告誡人們不要投生帝王家,以及明毅宗崇禎帝為女人的命運悲嘆的話語來諷刺君主專制為自己家族掘墓的荒誕和悲哀。endprint
黃宗羲通過對君權的批判,樹立了一種新的“忠臣”觀,他說:“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4〕認為真正的忠臣應當是忠于天下百姓,而不是忠于君主一人。臣與君的關系應當只是輔佐與被輔佐,協理與主治的關系,即臣下是君主治理天下、管理國家的助手,而非子孫或奴隸。如果君主的行為不利于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那么為臣的應當勸諫,否則就應當辭職,而不應當委曲求全,甚至為君死節。他說:“我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者之事也。”〔5〕認為為臣的應當有獨立的人格尊嚴,而不做像宦官、宮妾一樣一味討好、逢迎皇帝的小人。皇帝能聽從自己的建議固然好,如果聽不進自己的建議一味獨斷專行導致亡國,那么作為臣子的人沒有任何必要和義務去為皇帝死節、殉葬,因為那都是皇帝自己的事,與臣子無關。黃宗羲的這一思想極大地提升了儒家士大夫的人格地位,同時貶低了皇帝的地位,大臣不再只是作為皇帝的附庸和工具而存在,而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享有選擇和拒絕為皇帝服務的自由,并且不對皇帝個人進行任何形式的負責,而是直接向人民群眾負責,從此擺脫了夾在為民請命和為君執政之間兩難的境地。
三、《明夷待訪錄》中的自然法觀念
一個國家要想維持其正常運行,就必須形成一整套的規章制度來約束民眾,使大家在規定的范圍內各行其是、各得其所,而不侵犯到別人的利益,并為政府的運行提供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因此任何一種政治哲學都必然會涉及到關于國家法律制度的討論。“自然法”這一概念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時期的斯多噶學派,該派的思想家們認為理性是人所共有的,自然狀態是理性控制下的和諧狀態,是最合理最理想的狀態。公元6世紀的古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其所著的《法學階梯》一書中將羅馬法分為自然法、萬民法和市民法,首次正式地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意指自然界授予一切動物所應共同遵守的法律。該理論在后來發展為被人們視為“不言而喻的真理”:即認為人與人生而平等,大家都共同享有生存、自由、追求財富和幸福的自然權利,法律的一切規定均應以保障此種自由為最高準則。這種理論后來被以伏爾泰、霍布斯、盧梭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們發展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法律理論系統,并被拿破侖寫入《民法典》,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參考。
在我國先秦時期曾經有過與西方自然法思想較為接近的思想,如孟子所提倡的“民貴君輕”的王道政治主張健康的國家體制應該是和諧、平穩、可持續發展的,它要求人們“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使“數口之家無饑”、“ 頒白者不負載于道路”,從而實現人民“養生喪死無憾”的理想社會狀態。《管子》和《呂氏春秋》中也有大量關于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如何和諧處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的論述和建議。但是這些理論都只是從實用的具體層面來闡述的,沒有上升到宏觀的立法準則的高度。漢代的董仲舒在他的巨著《春秋繁露》中首次從天人關系的形而上的高度提出了類似于自然法的執政準則,他提出君主是代天行事的,是天的意志在人間施行的代表和媒介,人民群眾應當服從他的統治。同時,天的意志是對民眾的集體意志的體現,是為了實現人民群眾的共同利益。因此,君主的行政措施必須符合、滿足人民利益的根本需求,才能得到上天的肯定和眷顧,否則人民群眾就可以推翻他的統治。這種民主思想在當時是極為激進的,因此沒有完全被漢武帝所認可,漢武帝所采納的僅僅是前半部分,即認為君主是代天立言,人民群眾必須無條件服從。漢武帝的取舍直接決定了后世兩千年儒家思想的主流部分不是主張民權,而是強調君權。
黃宗羲所處的時代與董仲舒所處的時代迥然不同,董所處的時代是封建君主專制蒸蒸日上,正發揮它積極、強勢的作用的時期,而黃所處的時代則是封建君主專制已趨消極、沒落的時期。黃的思想也比董的思想更現代、更鮮明、更激進。董的思想雖然帶有從立法層面來限制君權的意識,但卻是一種隱藏在其行政意識之中的一種不清晰的、含混的意識。黃宗羲則明確地在《明夷待訪錄》中的《原法》篇中提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6〕清晰地認識到秦漢以來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下的法律都是違背自然法的精神的,是維護君主一人的權利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偽法,其實質是一紙自我辯護書,即將一切權利都歸于自己,一切義務和責任都歸于民眾。他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認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認為只有將法律的地位抬高到國家體制中最高的位置才能夠從根本上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才能體現出人的主體性。這與我們現在提倡依法治國是不謀而合的。黃宗羲清晰地認識到人的自利的本性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而一旦君主成為國家唯一的主體,那么這一負面效應將會帶來災難性的惡果。所以必須從法律的根源上杜絕掉君主的特殊性,實現人人平等,做到不僅僅“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帝王自身犯法也與民同罪,這樣的法律才是公正的,這樣的社會才是健全的。
黃宗羲不僅僅從破的層面上批判封建君主專制的法律體系,而且從立的層面提出自己理想中的法律原則,也就是他所謂的“三代之法”。他認為“三代之法”是“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盡其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7〕將三代的法歸結為“無法之法”,非常類似于道家所言的“大道無為”,認為三代的法是真正還政于民,還本于民,為人民的生產、生活提供物質保障,切切實實為人民服務的公法。這種公法的本質就是自然法,它的特性包括公平、公正、公開、自由 、民主、平等等現代精神特性。正因為這一法律的本質是為人民自身服務,所以不存在任何特權的階層和個人,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現有人故意要去擾亂司法的想法和行為。正因為在這一法律面前沒有任何特殊的階層和個人,所以也就不存在人格上的高低貴賤之分。既然沒有人會想到去破壞司法的公正性,司法行為也就沒必要有所遮掩、隱瞞。黃宗羲的這種思考是非常積極的,但是卻過于理想化,邏輯上也不夠嚴密。他忽略被司法的對象,即人民群眾自身存在的人格弊端,即他自己一貫強調的自利性。認為只要司法公平,法律條文就不需要太繁瑣、太細致,只要幾條大的方面的原則和標準就行,這是比較片面、迂腐的看法的。一個完全自利的沒有道德感的人,他在被司法的過程中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鉆法律的漏洞來為自己辯護,甚至謀取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如果法律的條文過于疏松,就必然會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這也為我國今天建設依法治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了個醒,即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從憲法的根本原則和標準上確立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就能保證每個人的合法權利都不受侵犯,不斷地完善憲法基礎上的各項法律法規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各種新型犯罪涌現出來,如果不及時跟進、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踩紅線、鉆漏洞的不法分子肯定大行其道。endprint
參考文獻:
〔1〕〔2〕〔3〕〔4〕〔5〕〔6〕〔7〕黃宗羲著,李偉譯注:《明夷待訪錄譯注》,岳麓書社,2008年5月。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written by Huang Zongxi in “Ming Yi Dai Fang Lu”
He Zhi Ren
Abstact:The “Ming Yi Dai Fang Lu” is an important book which concludes l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ritten by Huang Zongxi in Late Ming dynasty. The lessons learned of Ming dynastys decline and falling is being summarized by contras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ancient 3 generations”and the after generations in this book. In the book, Huang Zongxi think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eoples poverty in Ming and the Ming dynastys falling is the Absolute monarchy. The “ancient 3 generations law” which was thought as the best law in this book is very close to the nature law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lots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nd anarchism thoughts in this book. Huang thinks if without emperor , people will spontaneously organized into a society system. These theories are very modern of which are worthy us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Key words:Absolute monarchy;nature law;social contract theory;feudal autocracy
責任編輯:厐思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