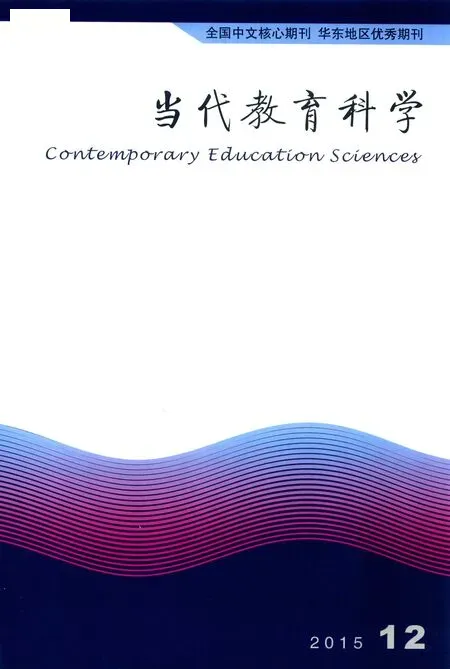課堂教學中的傾聽缺失現象及其原因探析
●白穎穎
課堂教學中的傾聽缺失現象及其原因探析
●白穎穎
新課改實施以來,課堂教學已一改過去的教師“一言堂”,創造出發言熱鬧的課堂,但在師生的言語互動中卻潛藏著傾聽缺失的危機,教師對學生消極的聽、異化的聽、虛假的聽以及學生對教師順從的聽、對學習同伴的偽聽,是目前課堂教學中存在的主要的傾聽問題。其中,教學計劃重于創生、教師鐘情標準答案、話語霸權習慣是教師傾聽缺失的直接原因,缺乏批判性思維、嚴重的自我中心傾向造成了學生傾聽的缺失,而技術手段的過度使用、知識中心主義的傳統慣習、大班額授課模式的限制以及家校教育的缺乏也在相當程度上加劇了這種傾聽缺失的傾向。
課堂傾聽;缺失;原因探析;教師;學生
課堂教學應當追求的不僅是熱烈的發言,還應當有“用心地相互傾聽”。“互相傾聽是互相學習的基礎。教師往往想讓學生多發言,但實際上,仔細地傾聽每個學生的發言,并在此基礎上開展指導,遠遠比前者更重要。如果要創設一個每個學生都能安心發言的教室環境的話,就必須對各種不同的意見十分敏感地傾聽,建立起相互傾聽的關系來,否則這一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傾聽這一行為,是讓學習成為學習的最重要的行為。”[1]然而,在課改大潮中,我國的課堂教學卻一味追求“發言熱鬧”、“師生互動”,從教師“一言堂”的極端走向課堂無效對話的另一個偏鋒。深度審視課堂中的師生對話和生生討論,不難發現在這“熱鬧”之下,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真實傾聽的缺失。
一、課堂傾聽缺失現象揭示
筆者收集了武漢某小學16節完整的課堂教學實錄①,涵蓋英語、語文、數學、科學、美術等五個科目,分別從教師對學生的傾聽、學生對教師以及學生同伴的傾聽兩個維度切入進行觀察。發現課堂中典型的傾聽問題如下:
(一)教師傾聽問題
1.消極的聽
課堂教學中,教師對學生表述不清或回答錯誤的問題,處理方式往往較為消極,缺少對學生的深度傾聽和進一步引導分析,多以“節約”時間為由直接跳過而進入下一步的教學設計;在教學過程中,對于能力有限的學生的傾聽缺乏耐心,實質上是一種消極的聽,如:
教學片斷1②:數學,五年級上冊,《三角形的面積》
師:怎樣來研究三角形的面積呢?有同學已經想好了,來,你說一說吧!生1:三角形的面積公式是S=2ah.師:哦,你已經知道了三角形的面積公式是吧?那你是怎樣研究出來的?分享一下你的想法。生1沉默。師:哦,只知道公式,不知道怎么推導出來的,是吧?我們這節課呀,就是要研究這個推導的過程。好,你說吧!(指向生2)生2:算個總的,是三角形的兩倍,然后再除以2,就是三角形的面積。師:怎么是兩倍?(皺眉)你準備怎樣研究?好,你先坐下來。(轉身尋找其他學生,指向生3)來,你說。生3:就是先是一個三角形,然后把它延長,變成一個長方形,然后長方形的面積就是長乘以寬……師:(打斷學生,用手撫摸學生的頭)你是想把它轉化為長方形來研究。隨后,教師就這一問題繼續提問了幾個學生。
該教學片段中,面對學生2稍顯含混的發言,教師在自身“傾聽”不足的情況下選擇了消極處理,教師只是在感官上接收了學生的言語信息,而沒有對學生的發言做出意義解讀,以至于沒能理解學生內隱的想法。
2.異化的聽
教學中教師過于注重標準答案,喜歡聽學生切近標準答案的表述,對學生的不同見解缺乏開放和接納的心態,存在“異化”[2]的傾聽現象。即教師傾向于控制學生按照自己的教學預設來發言,排斥與自己想法不一致的、背離標準答案的學生發言,對學生的“聽”是一種帶有先入觀念或個人偏好的聽,如:
教學片斷2③:語文,四年級,《小兵張嘎》
學習“妙計擾敵”部分,教師給出5分鐘時間,要求學生從課文中找出“妙計擾敵”部分的起止段落。
師:請同學們拿出一支筆,找找看,“妙計擾敵”從哪里到哪里?(停頓片刻,示意生4回答)你說,是從哪里開始的?生4:是從第37自然段開始的。師:真好!到哪里?生4:嗯,一直到最后一自然段。師:最后嗎?你說。(教師面露疑色,面向眾學生發問,最后示意生5回答。)生5:我覺得應該是一直到第48自然段。師:48自然段?有沒有不同意見?(教師略微皺了皺眉,俯身轉向身邊的學生,尋找“不同意見”。)這個妙計到他趁亂脫身以前都是的呀,那應該是到哪里呀?生6:我覺得應該是一直到第53自然段。教師連連點頭肯定,面露喜色,終于找到了“滿意”的回答。說到:對了!來,同學們,請你們在第37自然段和58自然段的前面畫上“\”,把它區分出來。
在這一環節的教學中,面對多個學生的發言,教師共給予2次肯定:在學生4和學生6回答正確時,均給予了稱贊,但對學生4、學生5終止段落的劃分方法卻未給予反饋,面對學生不同的劃分意見沒有追問,轉而提問可能會提供“標準答案”的學生,是一種異化的聽。
3.虛假的聽
課堂多隱匿有教師“虛假的聽”[3]、表面的聽,教師往往做出聽的姿態,但實際上并未對學生的發言作出真實傾聽和有效反饋。
教學片斷3④:語文,二年級說話課《感恩父母》
師:現在還有小朋友說,你不愛爸爸媽媽嗎?(有學生舉手)生7(叫出學生名字,似示意學生回答)生7起立欲回答,教師卻未湊近上前,在生7未開口前搶先說:不!此時無聲勝有聲。(遂即轉身放映幻燈片,進行下一環節的教學。)生7有些尷尬,在教師轉身后慢慢坐下。
一句“此時無聲勝有聲”,看似是對發言環節的精彩收尾,實則是教師虛假的聽,表面上給了學生反饋,卻是在強壓下制止了學生自由想法的表達。
(二)學生傾聽問題
1.對教師順從的聽
學生對教師的傾聽多屬于順從的聽取,普遍缺乏批判性思考和質疑,不敢挑戰教師的權威。在課堂中,學生多采取被動的、接受式的聽,被動接受教師的觀念,教師的想法甚至思維要點。不會“對所學的東西的真實性、精確性、性質與價值進行個人的判斷,對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合理決策。”[4]
在教學實錄的觀察中,這一問題較為普遍。主要表現為學生嚴格按照教師的教學指令進行學習行為的操作,對于教師提供的“既成知識”欣然接納,包括教師語言表述中的錯誤等,較少提出質疑。且在教師作出總結性發言或強調重要知識點時,學生大都會埋頭做筆記。⑤
2.對學習同伴的偽聽
學生對學習同伴的傾聽缺失現象較為嚴重,課堂上多表現為過分關注自己的想法,較少積極傾聽同伴的發言。在課堂上的發言多是自己觀點的表達而不是尋求思維火花的碰撞,思考較多的往往是怎樣讓自己的發言更趨完善,以至于很少能對同伴的發言作出獨到的評價或進一步思考,如:
教學片斷4⑥:一個二年級的課堂上,在教師提出問題后,學生爭先恐后的搶著發言,在學習同伴發言時,仍將手臂舉得高高的,擔心老師看不見,有的甚至半起身想要站起來,未等發言同伴說完,就有好幾個學生七嘴八舌地搶著說了,心思完全不在發言的同伴身上。
二、課堂傾聽缺失的原因探析
(一)直接原因
1.教學計劃重于創生,缺乏傾聽耐心
佐藤學曾把教師傾聽學生的發言比作和學生玩棒球投球練習,“把學生投過來的球準確接住,投球的學生即便不對你說什么,他的心情也是很愉快的。學生投得很差的球或投偏了的球如果也能準確地接住的話,學生后來就會投出更好的球來。然而,多數的教師只注意自己的教學進度,并沒去想準確地‘接住’每個學生的發言,未能與那些傾心‘投球’的學生的想法產生共振。”[5]在當前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多表現為過多地關注教學進度而習慣性地忽視對“投球”學生的想法的傾聽與揣摩。即便是有的教師會在學生拋出想法后回以“好”、“很好”、“不錯”等等,也多為機械性的言語回應,并未與“投球”學生的想法“產生共振”,實質上就是一種無效的傾聽。為了控制課堂,教師把課堂教學內容限定在了學科教學計劃、學期教學計劃、課時計劃等的框架之下,偏愛學生表達清晰的、與自己想法一致的發言,而對于學生含混不清的、與自己想法相異的發言則缺乏傾聽的耐心。
2.教師先入觀念嚴重,鐘情標準答案
課堂上,教師多青睞學生趨近標準答案的發言,偏向于讓思維清晰、概括能力強的學生在問題討論或發言進入尾聲時作出“總結性”發言,或者索性由教師自己作出標準答案的總結。教師在提出教學問題前,自己心中已對問題解釋有預設,師生互動中總會引導學生向教師所預設的思路和語言表述靠近,并沒有注意到學生想法的獨特性,去傾心解讀學生想法背后內隱的可發展性信息。實質上,學生在課堂中的發言沒有“好”與“壞”的差別,每一個學生的發言都是精彩的,有他自身的“邏輯世界”,教師要有足夠的耐心去傾聽,以開放的心態為學生勇敢展示自己的“邏輯世界”搭建平臺。教師一味追求“好的教學”,就易陷入“好的發言”堆砌起來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但作為教師“必須尊重每一個學生的發言,應該對所有學生的發言都寄予信賴和期待”。[6]
3.教師話語霸權習慣,拒聞學生異向話語
教師象征著權威,權威代表著話語權,而掌握話語權就掌握了主動權,因此,課堂師生關系中,學生往往處于相對次之、被動的地位。而處于師長地位上的教師,話語霸權便成為了一種不自覺的習慣。“教師在每個學習者發言之前或者之后講話,在‘正式’課堂發言中教師的講話占了大約70%,教師的講話具有排斥或支配許多重要的語言功能的權力,如提問問題、評價他人的發言、做長長的陳述、發布命令、批判先前的陳述、改變或安排主題、決定在關鍵時刻誰來發言以及打斷他人的講話等等。”[7]教師總習慣于按照自己的思維習慣去理解學生的想法,對于背離自己想法或教學設計的“異向交往話語”,[8]則沉默不理或是做出其他形式的變相忽略。但認真傾聽是理解的關鍵性前提,沒有發自內心的、開放的、主動的傾聽,理解就失去了它現實的可能性,教師在課堂上所表現出的聽不過是虛假的聽。
4.學生缺乏批判思維,慣于知識接受
傳統觀念下,中國學生自小便被灌輸“聽話”的行為守則,以致于很多孩子在潛移默化中養成了“遵守”、“接受”的慣習。在學習中,把教師話語和書本知識奉為“絕對真理”;生活中,不敢也不會對身邊的人、事、問題產生質疑,普遍缺乏反思意識、批判精神和獨立見解。然而,“學生傾聽教師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所謂‘價值無涉’的知識,而是為了意義的追尋。”[9]在實際的課堂中,學生做的最多的不是在教師的啟發下對學習內容進行主動的意義建構,而是將教師的“絕對真理”從黑板、課件、書本以及教師話語的“單向流動”中,復制到自己的聽課筆記或“心理筆記”上。在“聽”的心智加工過程中,僅僅是進行了感官上的接收和不加批判的理解,沒有從內心深處去傾聽、思考教師的話語。尤其在小學低年級的課堂中,這種類型的傾聽問題表現較為嚴重。
5.自我中心傾向重,生生傾聽難以形成
Philips曾對課堂中學生對學習同伴的傾聽做過精致描述:當老師在說話的時候,把老師當成話的接受對象;同儕們,相對地,并不像老師一樣經常注視說話者的臉;他們看著聆聽中的老師多過那位說話的同學;當一個學生在說話的時候,其他的學生常常沒有看任何人,他們不是看著遠方就是在看下面。[10]學生在課堂上多關注教師和知識,或是教師與自己的對話,對于同伴的發言則未給予認真的傾聽,甚至完全“屏蔽”周遭信息,沉迷于對自己發言的準備中。在看似熱鬧的發言背后,呈現出的是以教師為中心的簡式“自行車輪軸形”人物關系圖,學生與教師之間發生著可能的聯結,而學生與學生之間卻沒有建立起有實質意義的相互聯系。
(二)間接原因
1.技術依賴漸成風,教學重心遭到異化
教學技術手段的進步,使得教學多媒體設施、網絡教學平臺等現代技術手段在教學中得到越來越普遍的應用,然而在技術繁榮的背后,卻潛藏著過度依賴的危機。炫眼的課件設計、逼真精致的教具、便捷快速的網絡操作等,教師傾向于在教學中融入盡可能多的技術特效,以博得“眼球效應”,然而這些技術手段的過多運用卻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制造出了喧鬧而非有效活躍的課堂。特別是在公開課教學中,過度使用尤為嚴重。柏拉圖早有先見智慧,曾預示當我們發明出一種技術手段以擴大我們的知覺能力時,我們天生的能力反而會因此萎縮和改變,觀點雖顯極端,但卻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提醒。對于技術的過度依賴和沉迷會損害聽的能力,迷失聽本身,技術手段永遠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旦手段被當成目的,聽就被遮蔽了。[11]同時,教師本人也因為對技術手段的過分關注和依賴而忽略了對學生的耐心傾聽,久而久之,造成其傾聽意識的薄弱和傾聽能力的下降。
2.應試傳統慣習,知識偏向量化追求
在傳統課堂教學實踐中,往往以知識獲得的多少和理解運用程度作為衡量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效果的評判指標。這就造成了教學中對知識的量化追求,課堂教學演變為了追逐效率和效益的加工工廠,教師每天思考最多的不是怎樣訓練學生的思維,怎樣讓課堂教學“建基于學生的獨特性之上,傾聽學生的觀念并創造條件讓學生誕生更精彩的觀念”,[12]而是怎樣在最短的時間內教給學生最多的“知識”。美國教學研究專家弗蘭德斯曾在大量課堂觀察研究基礎上提出了“三分之二律”,即課堂時間的三分之二用于講話,講話時間的三分之二是教師在講話,教師講話時間的三分之二是向學生講話而不是與學生對話。[13]教師多徜徉于“純知識講授”的機械操作中不能自拔,總在想法設法向學生灌入更多“既成知識”。這種應試取向和知識中心主義的傳統慣習,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著課堂傾聽。
3.大班額授課模式,時間空間受到限制
長久以來,大班額問題都是我國義務教育階段教學改革面對的一個大難題。小班教學中,教師有充足的時間與學生進行互動,而在大班教學中,教師關注單個學生的時間和精力被“肢解”,在相對有限的課堂時間內,教師無法做到兼顧所有學生。此外,教室內的座位安排也對課堂中的師生傾聽有重要影響。在我國當前的課堂教學中,運用較多的座位安排結構有秧田型、馬蹄型、圓型和模塊型四種。[14]大班教學中,通常不得不采用秧田型來組織教學,這種座位排列方式不利于師生間的相互傾聽;而小班教學中易于采用馬蹄型、圓型或模塊型的座位排列,一定程度上創造了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相互傾聽的空間條件。四種類型教室空間安排對課堂教學傾聽影響的對比分析見表1。

表1 教室空間安排對傾聽影響的對比分析
4.學校家庭和社會,普遍缺乏傾聽教育
家庭中傾聽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學生傾聽意識薄弱和傾聽能力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首先,親子關系處理中父母傾聽的缺失。現代家庭中,繁重的工作壓力使得親子相處的時間相對有限,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多與隔輩親屬進行親密接觸,隔代看護的一個重要弊端就是對孩子的溺愛和教育不當。隔代親屬對孩子的“有求必應”和父母物質上的“補償”,使孩子容易出現過度“自我中心”的偏向,不懂得關心他人、傾聽他人的需求和表達。其次,父母作為對孩子精神教育最為重要的影響個體,因工作等原因與孩子的傾心對話和交流較少,普遍表現為不懂得傾聽孩子的內心,不會變換視角去理解孩子的“邏輯世界”,短時交流中也多表現出急躁。此外,從學前教育到義務教育,直至高等教育,學校教育內容都側重于知識授受和德育說教,并沒有對傾聽能力的培養投以相應的關注,傾聽作為個人生活的基本技能,有所提及也多是就生理上的有或無、強或弱來談。在物質發達、信息高度泛濫的現代社會,快節奏的生活使得人與人之間的傾心交流、靜心溝通相對減少,不會或不愿傾聽成了社會的一種“通病”。
三、結語
“教育的過程就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相互傾聽與應答的過程。當這一過程被阻斷或者處于混亂無序的時候,師生之間的交往和溝通就將陷入困境,教育的危機也將隨之出現。”[15]被遮蔽的傾聽下,師生之間、生生之間進行的是無效甚至低效的課堂對話。當前我國的課堂教學已經在面臨著這種傾聽缺失所帶來的教育危機。課堂中發言熱鬧的虛假繁榮之下,真實暴露的是師生之間教師話語霸權式的單項牽引和生生之間微乎其微的關聯。然而,真正活躍的課堂需要的是靜心的傾聽和互動的交流,師生任何一方的單權獨霸都不能給予課堂以鮮活、持久的生命力。在缺乏主體間真實傾聽的前提下,課堂中的“熱鬧的發言”雖能以某種形式繼續演繹,卻定然不能長久。
改變課堂中的無效傾聽,需要教師、學校、家長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以下幾點應首先提上日程:1.教師要從意識到行動,真正的踐行傾聽榜樣:在意識上,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尊重每個孩子的話語習慣和獨特的“邏輯世界”,傾聽每個孩子的精彩;在行動上,教師不僅要傾心聽學生所說,還要注意覺察學生在說的同時所表露出的面部表情、體態語等非言語信息,體味學生話語中潛在的復雜想法甚至心情,身體力行地為學生樹立傾聽榜樣。2.將傾聽教育、關心教育引入學校:諸如定期開展傾聽學習活動、開辦關于傾聽的講座,或是在口語交際等課程的教學內容上作出一些調整,把對傾聽意識的培養和對傾聽技能的訓練納入其中;通過家校平臺、學校與社區的合作等,向家長和社會開展有關傾聽的教育宣傳。3.改變傳統評價觀念,轉換對師生的考察重心:將對學生的評價由知識指向轉為能力指向,對教師的評價由績效評價觀轉向發展評價觀,對師生的評價需要涵蓋對其傾聽能力的考察。傾聽現狀的改善無疑會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邁出”是改變的第一步。
注釋:
①16節教學錄像的具體科目、年級、課程內容等基本構成如下:英語課3節,四年級《Children of the world》、五年級《A story》、六年級《Holidays》;語文課6節,一年級《比一比》、二年級《窗前的氣球》和《說話課:感恩父母》、三年級《自然之道》、四年級《小兵張嘎》、五年級《隔窗看雀》;數學課5節,二年級《9的乘法口訣》、三年級《24時計時法》、四年級《數學廣角》、五年級《方程的意義》和《三角形的面積》;科學課1節,《誰選擇了他們》;美術課1節,《參觀券的設計》。其中語文、數學、英語、科學教材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美術教材為人民美術出版社。
②③④⑤⑥均選自筆者的課堂錄像觀察。
[1][5][8][日]佐藤學著.李季湄譯.靜悄悄的革命——創造活動、合作、反思的綜合學習課程[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3:72-73,35,46.
[2][9]周杰.傾聽教學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101-103,140.
[3][11][15]李政濤.傾聽著的教育——論教師對學生的傾聽[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1(1).
[4]劉儒德.論批判性思維的意義和內涵[J].高等師范教育研究,2000(1).
[6][日]佐藤學著,鐘啟泉、陳靜靜譯.教師的挑戰——寧靜的課堂革命[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5.
[7]Philips, S.U.The Invisible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Classroom and Community on the Warm Springs Reservation[M]. NewYork:Longman.1983:82-83.
[10]Courtney B.Cazden著.蔡敏玲等譯.教室言談:教與學的語言[M].臺北:臺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8:95-96.
[12][美]愛莉諾·達克沃斯著,張華等譯.多多益善——傾聽學習者的解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65-170.
[13]N.A.Flanders.Analyzing teaching behavior[M].MA:Addisi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0:178.
[14]陳佑清著.教學論新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355-356.
(責任編輯:劉君玲)
白穎穎/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課程與教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