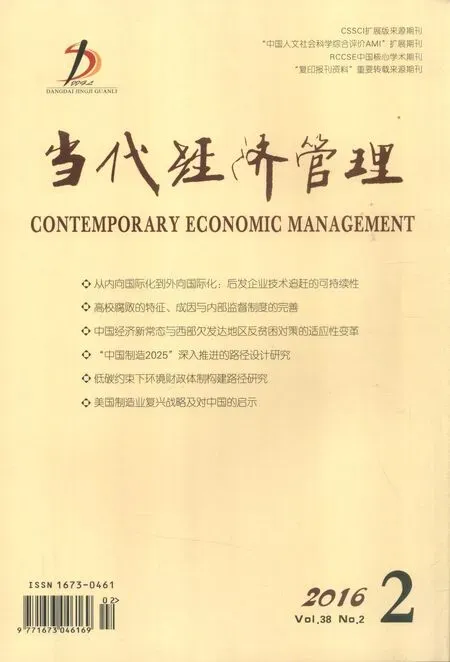公司治理、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
■葉陳剛,王 孜,武劍鋒
(1.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北京100029; 2.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商學院,北京100024)
?
公司治理、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
■葉陳剛1,王孜1,武劍鋒2
(1.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北京100029; 2.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商學院,北京100024)
[摘要]以滬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運用J-F系數法從環保目標、法規和懲處構建環境績效,考察了公司治理和政治關聯對環境績效的影響,探討了政治關聯在公司治理和環境績效關系中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股權性質、董事會規模和兩權分離促進了環境績效,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呈負相關關系,政治關聯會抑制公司治理對環境績效的正向提升作用,拓展了環境績效的研究視角,為提升公司治理和環境績效水平提供了經驗證據。
[關鍵詞]公司治理;政治關聯;環境績效;環境溢價;社會責任
網絡出版網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1.1137.004.html網絡出版時間:2016-2-1 11:37:33
一、引 言
從廣東鶴山公眾制止核燃料項目,到柴靜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的備受關注,折射出公民對改善環境日漸高漲的良好意愿;從康菲石油公司對渤海灣漏油事件提出賠償金額,到新安股份管理層因涉嫌嚴重環境污染問題被處罰,再到“史上最嚴”《環境保護法》的施行,反映出政府對企業逐漸強化的環境監管和執法水平;從實務界到理論界,公司治理、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的研究方興未艾。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是市場失調的表現,政府和社會施加外部驅動力給企業進行有效的環境監管和環境治理,企業自身也受到主動實施環境行為的內部驅動力,這種內外部的力量通過環境消耗和環境維護的不斷博弈達到平衡的環境績效水平,提升環境績效水平可以降低市場失調程度。Ramanathan(2014)研究發現環境績效的最終效果主要靠企業內部運營來實現,其次是經濟壓力、環境法規和外部利益相關者同樣影響環境表現水平。[1]從法律和道德角度來講,企業既需為負面的環境后果付出代價,也可以從正面的環境效果中受益,Charl(2011)認為企業有動力也有壓力實施環境管理行為。[2]那么股權性質、董事會和高管契約等公司治理特征是否會影響環境績效?政治關聯能否提升環境績效?政治關聯在公司治理和環境管理中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問題亟需從理論和經驗上得到解決。
本文考察了不同的公司治理因素對環境績效的影響,對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繼而探討了政治關聯在公司治理和環境績效兩者關系中作用。本文的增量貢獻在于:通過環境法規、環保目標和政府獎勵懲處3個維度和5個指標構建環境績效指數,運用Janis-Fadner (J-F)系數將企業的環境事故、環境懲罰、未通過環保核查等負面效應更準確地反映出來,豐富和完善了環境績效衡量和評價指標;將政治關聯納入環境績效視野,分析政治關聯對公司治理和環境績效的調節作用,拓展了環境績效的研究視角,為提升公司治理和環境績效水平提供了經驗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公司治理與環境績效
環境信息的特殊屬性使得委托人難以監督和控制代理人的環境行為,為減少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公司治理通過安排各種制度和契約解決雙方的代理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收斂企業環境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保障委托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Christopher,2015),[3]減少企業“搭便車”行為,公司治理與環境績效的相關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Salo,2008)。[4]國有企業投資環境管理會增加運營成本降低競爭力,但如果國家的目標為優先實現社會利益,國有企業會毫不猶豫地執行國家目標,領導者因優先選擇國家利益增加了晉升砝碼。從壓力角度分析,國有企業對解決就業、保護環境、增加社會福利有更重的責任,國家也能更直接地對其控制和傳遞自身政策導向,企業此時不僅僅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終極目標,在政府的壓力下更有可能承擔環境責任;從激勵角度分析,國有企業更容易受到政府的保護和扶持,他們更容易獲取異質性資源也有更多“退路”,對經濟損失的擔心低于非國有企業,有動機將環境成本內部化,如Ghazali (2007)研究發現國有控股公司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5]國有企業對環境績效是一種正向影響,據此分析提出假設1a:
假設1a:相對于民營上市公司,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更高
董事會的規模是公司治理和戰略控制的重要因素(高明華,2014),[6]董事會規模越大,代表管理層異質性增加,環保人士和具有專業環境技能的董事越多,其環境偏好和環境敏感性可能引導企業做決策時考慮環境管理,從口碑和環境外部性的長遠考慮,也愿意在環保和環境宣傳方面承擔成本;其次,大規模的董事會意味著更多的政治資源,有機會獲得更多外部投資,也可能更早地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再者,董事會的規模越大,彼此監督的水平增加,如果企業做出了不利于環境管理的決策,會被更早地發現問題并及時應對,Elsayed(2009)證實了董事會雖然會增加組織協調成本,同時也對提升環境績效產生了積極影響,[7]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b:
假設1b:上市公司董事會規模越大,環境績效越高
獨立董事獨立于公司的管理和經營活動以及那些可能影響他們做出獨立判斷的事物,他們不代表企業任何一方的利益,會從企業自身出發并顧全大局,履行監督的職責(李維安,2014),[8]避免董事會決策“一言堂”的局面。獨立董事大都由高學歷的學者或有豐富管理經驗的管理者擔任,一方面他們道德水平較高,其中不乏環保人士和環境敏感型人士,另一方面沒有企業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Charl,2011),[2]在監督時更有可能維護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董事會中獨立董事人數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上市公司內部受監督的水平,他們有監督和協調企業是否實施環境責任的動因,據此提出假設1c:
假設1c: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比例越高,環境績效越高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董事會無法有效實施監督職能,本應由董事會選拔公司的總經理等高層執行官員負責公司的具體經營管理事務,并決定他們的獎懲制度,兩職合一使董事會難以評價總經理的環境保護行為、也難以監督和解聘總經理,權利的放大使董事會被董事長操縱。Patton等(1987)認為,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一人兼任進一步增加了環境信息不對稱水平,監督機制無法有效運行時,增加了委托代理問題,此時董事長可能會為謀求一己私利損失委托人的利益帶來逆向選擇問題,[9]在這種權利高度集中的情形下,企業舞弊可能性增加,管理層很有可能選擇個人短期利益而放棄長期的環境規劃,因此提出假設1d:
假設1d:相對于兩職合一的上市公司,兩職分離企業的環境績效更高
董事會對經營者管理能力的度量和薪酬支付可以激發他們的工作能力和熱情,尤其可以增加他們決策控制的科學性,并愿意承擔決策控制的風險。當經營者的薪酬與短期利潤緊密聯系時,他們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忽視企業的長期發展,但實際上,社會福利中的環境訴求是長期的,企業相應做出的環境戰略不可能短期實現,Pascual (2009)發現環境風險特別是可能的環境事故,會對企業未來發展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10]管理者此時會將自身利益與企業長期戰略相結合,彌合彼此的利益分歧,做出最優決策,此時高管薪酬和環境績效呈正相關關系,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e:
假設1e: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越高,環境績效越高
(二)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
Stigler(1971)提出的部門利益理論則認為政府規制作為“掠奪之手”,[11]代表了特殊利益集團尋租,環境角度的政治關聯意味著一種腐敗,利用自己的實力加入有權力的環境組織或政府組織以降低環境法規評價標準,或利用地方保護主義甚至行賄手段與政府部門建立政治關聯,或邀請政府官員和環保機構成員成為公司董事以逃避企業的環境責任,高管在企業和政府間的角色轉換以及政府和企業的利益重疊會帶來職能扭曲。另外,地方政府本身為了追求經濟利益,會主動放松對企業的環境管制,雙方一拍即合,通過政治關聯各取所需,政府為企業制定了非常低的環境標準,企業則在這個最低標準內經營發展,極力壓縮環境投資,長遠來看,整個社會環境利益會逐漸惡化,Charles(2006)通過實證發現,企業的政治支出成本與環境績效有強烈的反比關系,[12]也就是說企業的政治關聯策略使它們故意忽略環境責任、歪曲環境績效,出現重大的道德失誤。基于部門利益理論提出假設2:
假設2:上市公司政治關聯程度越高,環境績效越低
(三)公司治理、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
姚圣(2011)發現政治關聯會降低企業環境信息透明度,[13]雷倩華(2014)證實政治關聯會削弱政府的環境監管效果,[14]政治關聯可能出現“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企業企圖脫離法律軌道或走法律的擦邊球,通過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以獲取特殊服務;其次,聘請政府高官的企業可能面臨更多代理成本,如管理者沒有足夠的專業技能、將更多精力花在維護政治聯系上、要求更多的薪資等,都會降低內部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另外,有效的公司治理依賴于公開的信息披露,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管理者為個人私利忽略企業長期利益,降低企業公司治理的能力,進一步弱化了公司治理為環境績效創造的效益。政治關聯弱化了公司治理和環境績效的關系,假設3如下:
假設3:上市公司政治關聯程度越高,公司治理對環境績效的正向影響越低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根據國家環保總局《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和《上市公司環保核查行業分類管理名錄》中認定的16個重污染行業,選取2009~2014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所有重污染行業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按照下列標準進行了篩選:剔除數據不滿連續五年的公司和數據不全的公司;剔除財務狀況異常的ST、PT公司;為消除極端值影響,對所有小于1%分位數或大于99%分位數的變量進行Winsorize處理,最終得到267家公司,1 602個有效樣本。
ISO14000、環境友好型企業、是否出現過重大環境污染、環保核查、是否受到過環境處罰數據分別來自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上市公司年報、中國經濟新聞庫、國家環保部網站、地方環境保護總局網站,其他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
(二)環境績效的衡量
Henri(2008)認為環境法規、環保目標和政府獎勵懲處是環境績效指標最重要的三個維度,[15]它們對環境績效指標的量化有重要作用,基于Henri的觀點,從以下五個方面構建環境績效:企業是否通過ISO14000、是否評選為環境友好企業、是否出現重大環境事故、是否通過環保核查、是否因環境問題受到過處罰,請參見表1。

表1 環境績效變量選取與賦值表
Testa(2014)發現能源密集型企業對國際ISO14001標準反應敏感,企業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短期和長期環境績效都有明顯提高;[16]環境友好型企業具體數據由企業統計和提供,當地環保行政主管部門審核,全面性和可信度較高,可以作為企業環境績效良好的評定標準之一;重大環境事故代表的環境問題深度最有參考性,是企業最真實的環境表現,負面信息的可信度更高,其代表的環境問題也更嚴重;地方環保部門利用上市公司尋租并非鮮見,無論是出于地方經濟發展的考慮,還是當地法治水平的限制,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地方保護主義,核查效果遠小于國家環保部門;在面對企業的環境問題時,負面懲處比正面獎勵更有代表性、說明性和真實性。
運用Janis-Fadner系數來計算環境績效,J-F系數最早用于內容分析法計算企業合法性,本文中將J-F計算方法引入環境績效(EPI)中,具體計算公式方法如式(1):

在式(1)中,EPI代表環境績效,p代表正面環境績效總得分,q代表負面環境績效總得分,EPI指數的取值范圍從-1到1,數值越接近于1,代表企業的環境績效越好;數值越接近-1,代表企業的環境效果越差。
(三)公司治理與政治關聯的衡量
股權性質用State表示,國有企業有實力也更有責任承擔環境責任;董事會規模用Bsize表示,Elsayed(2009)證實大規模董事會可以增加環境績效;[7]獨立董事比例用Pctind表示,Charl等(2011)發現,董事會中獨立董事人數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上市公司受監督水平,對企業的環境監督性較高;[2]兩職分離用Dual表示,總經理和董事長由不同人任職時,賦值為1,兩職合一時賦值為0;高管薪酬用MS表示,Pascual(2009)認為,薪酬越高的管理人員,越有可能以長遠的眼光看待問題,而不僅僅局限于短期利益;[10]借鑒杜興強等(2011)的研究方法,[17]關注企業與當地政府或其他公共相關方的關系,根據數據庫企業高管簡歷,如果高管過去或現在有在政府、黨委紀委、人大、政協常設機構、法院檢察院任職則認為高管擁有政治關聯,政治關聯指標(PC)為高管政治關聯人數除以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
(四)控制變量的選取
企業規模用Size表示,較大的公司傾向于進行更多環境管理(呂峻等,2012);[18]資產負債率用Lev衡量,債務杠桿失衡的企業,沒有更多實力和精力考慮環境問題;盈利能力用總資產收益率ROA表示,盈利能力高代表了企業有較好的成長性,更有可能承擔環境責任;上市公司年份Year和行業Industry啞變量。
(五)計量模型和變量說明
通過構建的模型(2)至(4)來檢驗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設1至3:

其中,EPI用來反映企業環境績效水平,在實證過程中使用股權性質State、董事會規模Bsize、獨立董事比例Pctind、兩職分離Dual、高管薪酬MS5個細分指標替代公司治理指標CG,具體變量定義與說明見表2:

表2 變量定義與說明表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3報告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環境績效EPI均值為0.5,中位數為1,說明大部分樣本企業的環境績效處于正向水平,即正面環境效應大于負面環境效應,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1,企業間環境績效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股權性質State均值為0.65,研究樣本中有64.6%的企業實際控制人為國家,與我國上市公司的整體情形大致相同;董事會規模Bsize最大值為2.890,最小值為1.609,說明研究樣本的董事會規模偏小;獨立董事比例Pctind中位數和均值分別為0.333和0.365,總體獨立董事比例較低;兩職分離Dual平均值為0.88,中位數為1,實行董事長和總經理分離制度的樣本公司較多;高管薪酬MS的最小值為1.040,最大值為1.718,可見高管間薪酬差距較大;政治關聯指標PC中位數為1.61,均值為2.53,說明樣本企業間的政治關聯程度較低。

表3 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公司治理與環境績效的檢驗結果
表4報告了自變量為公司治理的細分變量、因變量為環境績效EPI的回歸結果,由第1列可以看出,環境績效與股權性質的系數為0.0398,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t值為2.28),說明國有企業一方面有政府的強大后盾,不必為環境投入帶來的巨大成本和競爭力降低而擔心,另一方面面臨政府給予承擔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更大壓力,環境管理更為積極,假設1a的股權性質得到驗證;從第2列可以看出,董事會規模的回歸系數為0.206,同環境績效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意味著大規模的董事會中可能存在環境偏好型領導者,在制定企業戰略時不會忽略環境因素,且董事人數的增加意味著更大的內部監督水平,假設1b的董事會規模維度得到驗證;有第4列看出,兩職分離與環境績效的回歸系數為0.0719,t值為2.92,顯著正相關,這表明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不同人擔任,可以積極促進企業環境水平,假設1d的兩職分離維度通過檢驗。
另外,從表4第3列和第5列可以看出,獨立董事比例和高管薪酬單獨進入模型回歸時,與環境績效的回歸系數為負,與預期的符號相反,并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假設1c和1e沒有得到驗證,可能的原因是我國獨立董事比例較低、執行力較弱,并非管理學的專家對財務報表不甚了解,無法有效履行監督職責,另外,高管有動機向獨立董事隱瞞真實的信息,不充分、不及時的數據無法暴露企業可靠的環境情況,這就失去了獨立董事監督企業環境管理行為的基礎;我國的高管薪酬較少與環境效益掛鉤,甚至出現嚴重的環境事故都不會影響管理者收入,他們的薪酬更多是基于企業業績的契約安排,那么單純依靠市場價值、忽略環境價值建立經營者的報酬激勵機制就存在很大局限性。

表4 公司治理與環境績效回歸結果
(三)公司治理、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的檢驗結果
表5報告了政治關聯對公司治理與環境績效影響的實證結果,將PC單獨放入回歸模型中進行檢驗,從第1列可以看出,政治關聯與環境績效顯著負相關(系數為-2.201,t值為-16.57),假設2得到驗證。這表明政治關聯程度越高,企業環境績效越差,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企業政治關聯的動機更多是逃避環境規制。
在第2列中,股權性質和政治關聯交叉項的系數為-0.874,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隨著政治關聯水平的提高,股權性質帶來的環境績效好處被削弱,假設3中的股權性質維度通過檢驗。從第2列可以看出,董事會規模和政治關聯交互項的系數為-1.654,t值為-3.01,在1%水平上顯著,假設3中的董事會規模維度通過驗證。結果說明若董事會規模與環境績效的正向關系存在時,政治關聯會削弱董事會規模帶來的環境績效效率,二者的關系隨著政治關聯的提高而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由第3至5列可以看出,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分離、高管薪酬與政治關聯的交叉項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樣本公司的政治關聯程度對獨立董事、兩只分離和高管薪酬提升環境績效的效應較弱。總體而言,假設1中的股權性質、董事會規模和兩職分離三個維度通過驗證,假設1中的獨立董事比例和高管薪酬維度沒有通過驗證;假設2中的環境績效與政治關聯顯著負相關,通過驗證;假設3中的股權性質和董事會規模兩個維度通過檢驗,獨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和兩職分離維度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5 公司治理與環境績效回歸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首先替換關鍵因變量環境績效,將正面環境績效總和與負面環境績效總和加總,以替代利用J-F指數法計算出的EPI指數;其次,換關鍵自變量政治關聯,使用高管是否具有政治關聯的啞變量PC-Dum,以替換政治關聯的指標PC;最后,將后一年度的環境績效與前一年度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政治關聯重新做回歸,以檢驗之前結果的可靠性,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6。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從表6可以看出,模型中主要變量的顯著性基本沒有實質變化,需要關注的是,原回歸結果中政治關聯和兩職分離的交叉項系數雖然為負,但是不顯著,在穩定性檢驗中,Dual*PC-Dum的系數為-0.410,t值為-3.23,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政治關聯會抑制兩職分離帶來的環境效果;股權性質、董事會規模和兩職分離可以顯著促進企業的環境績效水平;并且隨著政治關聯程度的提高,公司治理對企業環境績效的促進作用會被減弱,上文的研究結果具有可靠性。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選取2009年到2013年滬市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衡量了樣本企業的環境績效水平,探討公司治理和政治關聯是否對企業進行環境管理有促進作用,并著重分析了政治關聯是否會抑制公司治理帶給環境績效的好處,研究結果顯示,國有企業的環境績效水平優于非國有企業,董事會規模越大,企業環境績效水平越高,董事長與總經理由同一人擔任和政治關聯程度越高的企業,環境績效水平更低;股權性質、董事會規模和兩職分離與環境績效的正向關系存在時,政治關聯會削弱這三個公司治理細分變量提升環境績效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由于企業環境保護的付出和收益較難衡量,并且現階段缺乏專業的環境評價的數據庫,對于環境績效的測度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司治理的內部和外部維度,全面考察公司治理對環境績效的作用;再者,可以從政治不確定角度出發,探究其對于公司治理和企業環境績效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Ramanathan R., Poomkaew B., Nath P.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Pressures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 [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2014, 23(2): 169-182.
[2] Charl V., Naiker V. The Effect of Board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 (6): 1636-1663.
[3] Christopher S. A., Jennifer L. B., Alan D.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entives, and Tax Avoida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5, 60(1): 1-17.
[4] Salo 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ustry and Country Effects [J]. Competition & Change, 2008, 12 (4): 328-354.
[5] Ghazali N. A.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Some Malaysian Evidence [J].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7, 7(3): 251-266.
[6]高明華,蘇然,方芳.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評價及有效性檢驗[J].經濟學動態,2014(2): 24-35.
[7] Elsayed K., Paton 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Does Firm Life Cycle Matter? [J]. Business Strategy & the Environment, 2009, 18(6): 397-413.
[8]李維安,徐建.董事會獨立性、總經理繼任與戰略變化幅度——獨立董事有效性的實證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 2014,17(1): 4-13.
[9] Patton A., Baker A. J. Why Won't Directors Rock the Boat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7,12: 10-18.
[10] Pascual B., Luis R. 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 Integrated Agency-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1): 103-126.
[11] Stigler G.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1, 2(1): 3-21.
[12] Charles H. C., Dennis M. P., Robin W. R.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Expenditure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6, 67(2): 139-154.
[13]姚圣.政治關聯、環境信息披露與環境業績——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財貿研究,2011(4): 78-85.
[14]雷倩華,羅黨論,王玨.環保監管、政治關聯、與企業價值——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14, 36 (9): 111-121.
[15] Henri J. F. Journeault M.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Firm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8, 87: 35-49.
[16] Testa F., Rizzi F., Daddi T. EMAS and ISO14001: the Differences in Effectively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4, 68: 165-173.
[17]杜興強,曾泉,杜穎潔.政治聯系、過度投資與公司價值——基于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 2011(8): 93-110.
[18]呂峻.公司環境披露與環境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J].管理學報,2012, 9(12): 1856-1863.
(責任編輯:張丹郁)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Ye Chengang1, Wang Zi1, Wu Jianfeng2
(1.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China; 2.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Using listed companies in heavy polluting indust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2009 to 2014. We calcul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rom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rules and punishmen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i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ate,board size and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the enhancing the level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weak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increas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we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Key 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political connection;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nvironmental premium;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作者簡介:葉陳剛(1962-),男,湖北蘄春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審計與公司治理;王孜(1987-),男,河北邢臺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審計與公司治理;武劍鋒(1981-),女,山西壽陽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際商學院講師,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環境會計與公司治理。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3AZD002)與國家留學基金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201406640032)及大信審計教育研究基金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0-23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2.004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2-0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