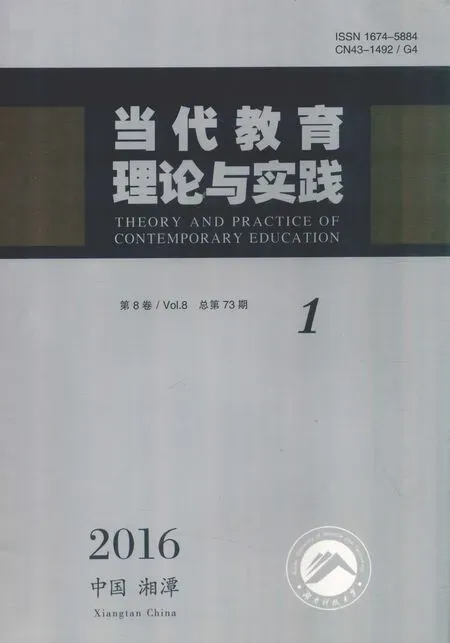論哲學教學的“一以貫之”之道
?
論哲學教學的“一以貫之”之道
阮春暉
(邵陽學院 政法系,湖南 邵陽 422000)

摘要:哲學教學靈動模式的展開可以在經典文本中找到相關依據。“一以貫之”語出《論語》,其基本意涵包括“以一為本”與“貫一于用”兩個方面。哲學實際都具有“一以貫之”的內容特色,使得思想自身帶具靈動的內在品格。哲學思想的內在流動性,要求我們在教學中依循與之相應的靈動模式,即維守哲學教學中的“一”、采用“達貫”的方法和勵推流動的教學場景。
關鍵詞:哲學教學;一以貫之;靈動模式;課堂應用

1“一以貫之”的文本依據及其意涵
“一以貫之”之說出自《論語》,其語有兩處: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
對于前言,朱熹作注為:“圣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1]也就是說,盡管人倫物事繁復多途,其用各有不同,但“泛應曲當”之用的根本——仁道忠恕之“一體”——卻是始終如一的。這是強調“本”對于“用”的優先性。對于后語,朱熹的解法和前解相差不大,還是突出“本”對于多而能識之用的重要性;而胡適對此卻另有解法:“我的意思,以為孔子說的‘一以貫之’和曾子說的‘忠恕’,只是要尋出事物的條理系統,用來推論,要使人聞一知十,舉一反三。這是孔門的方法論,不單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學。”[2]如果說,朱熹主要是從“體一”這一人生哲學立場來解釋“一以貫之”的話,那么胡適則著重是從方法論這一角度來加以詮解,即“一以貫之”這種學習方法對于尋出事物條理系統的重要意義。這里的“條理系統”,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事物之本。這樣看來,胡適此解是突出“用”對于“本”的尋繹性。
本文以為,從單章看,前者主要從內容而論,即人倫物事都體現為忠恕貫有之道;后者主要從方法而談,即在多學而識的過程中貫之以根本的原則與方法。不過,我們閱讀《論語》,顯然不能僅從單章之意來判別其意義范圍。實際上,整部《論語》貫穿的是關于德性的主題,它展露在為學、為政、為人等多個方面。在論及這些具體行為時,相關語錄會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多次出現,對同一陳詞作出多層解釋,從而形成意義層疊,如君子、義利、一以貫之等。我們研學《論語》、理講中國哲學,需有前后相貫的視眼來對此作出盡可能詳盡的理解。據此,在相對整全的意義上,“一以貫之”既可以解讀為在各種生活之用中貫之以“一”的原則與規范,這是“本”;也可以研析為在“一”的基礎上采用多種形式和方法達及對事物多方面的認識,這是“貫”或“用”。“以一為本”與“貫一于用”的合意,是“一以貫之”的基本意涵。
2“一以貫之”的哲學意義
《論語》中“一以貫之”的內在意涵,可以延展為對于整個中國哲學的理解。不妨這樣認為,整個中國哲學都具有“一以貫之”的內容特色。在儒家,“一”為仁義禮;在道家,則為“道”;在墨家,則為“兼愛”;在法家,則為“法”。置于宋明儒學的意域范圍,這個“一”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方面指“貫之以一”,即通過不懈的格致工夫達至豁然貫通的知識和道德境界,這是程朱理學走的路線;另方面指從終極的道德根源“一”出發,使之流貫廓充于事事物物,成就道德的事業,這是陸王心學走的路線。事實上,其他各家也都有類似的理論特點。不管是儒墨道法、儒學內部的理論支脈還是其他各家之說,其共通點都是強調“一”的流貫在成就圣賢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思想核心“一”在社會生活中如何施為,如何將思想主張及于整個社會,以成就功名事業,促就道德提升。

從這點看,中國哲學實際具有“動”的內在品格,是流貫的思想體系之構成。這種流動構成包括三個方面:自流動、外流動和內流動。所謂自流動,是指思想自身有其內在的活動韻律,各理論要素呈現為相互連貫、相互說明的關系。如朱熹講天理,其內涵必定包括天理這一范疇是由什么理論因素支撐起來的,支撐因素之間是怎樣的互動關系;王陽明講良知,良知不是靜凝不動的,它必定有“致”的因素。所謂外流動,是指思想核心“一”有一種內在的動力源,它必然會發之于外,流行發用于事事物物之中,從而在“一”和外物之間形成互動。所謂內流動,也就是事事物物的方向和價值都必然回歸于“一”,即回歸到統一的、普遍的道德原則和事物的根本上來,也就是朱熹所講的“其體之一”, 普遍的“一”是萬物之“多”回歸的價值原點。如陽明說“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3],其中“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是外流動,“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便是內流動。
3“一以貫之”靈動模式在哲學教學中的應用
中國哲學的這種靈動性質,自然要求我們在哲學教學中遵循其“內外兩活”的思想特征,以“一以貫之”式的靈動模式展開哲學教學。
3.1 維守教學中的“一”
哲學教學要有“本”,這個“本”也就是“一”。對于哲學課堂教學而言,此“本”或“一”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一種基本精神。對于整個中國哲學來說,這種基本精神就是對形上道德的不斷追求,即《大學》所言之“止于至善”。也就是說,中國哲學是把高尚的道德塑造作為第一要義來看待的,從德看事,將事歸之以德。儒墨道法諸家,都是把成圣成賢、人生境界的提升作為自己的終極道德目標,只不過其追求的方式不同而已。儒家的“止于至善”,道家的“圣人之治”,墨家的“尚賢”,法家的“有道之君”,都是如此。中國哲學既然是關于德性錘煉的思想學說,我們在哲學教學中自是不能輕忽,課堂教學要始終堅持、顯明這一根本精神。這是哲學教學對于“一”的總把握。第二,一個道德支點。哲學基本精神的勃發,需有一個道德支點。對于中國哲學而言,這個道德支點就是成圣成賢;而對于不同的思想家,這個道德支點又各有其分殊而表現為分殊“一”。此分殊“一”在朱熹為天理,在王陽明為良知,在王夫之為“人”,如此等等。哲學教學就要厘清這些道德支點的具體內涵及其對于不同思想家所帶來的思想意義。應當承認,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這個道德支點有很大不同,但作為道德的本質,如完善自我、成就事業、服務社會等,在各個歷史時期卻是相同的。哲學教學理當把這些不同的道德支點貫穿起來,找出其間的異同,堅持德性教學,服務當今社會生活建設,這樣才能讓哲學的基本精神有一個個的具體落點,哲學教學之“本”才有實際意義。
3.2 采用“達貫”的方法
哲學是流動的思想體系,它本身是靈動的,哲學課堂教學要盡可能把這種靈動的思想展現出來,這就需要我們采用“達貫”的教學模式。
所謂“達”,即在把握思想本質的基礎上上達至對于人的道德精神的塑造;所謂“貫”,即把人的道德精神展現在具體的事物之中。以中國哲學中天道、人道和地道的相互關系為例。在中國哲學中,天道是宇宙萬物生成、變化和發展的最終原理,在中國哲學的特殊意域中,天道特指人們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地道是宇宙萬事萬物總合而形成的一種現象界存在,具體表現為人與人、人與自然萬物、物與物的現象倫理。人道是人的生活之道,是人生日用常行、事業作為中的生活規范和道德之舉。“三道”之間,由人道而上達天道,由天道而下貫人道、地道,構成以“人道”為中心、達貫天道和地道的流動循環體系。
哲學教學,可以依此采用“達貫”的靈動模式。我們知道,在不同時期、不同思想家那里,天道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是分殊“一”的不同。盡管如此,在上達至于對整體“一”的趨求和下貫為具體的生活事為上,卻是一致的。在教學中,要注重不同的思想家在對分殊“一”的推解中是如何追求天道以實現人之德性完善和人生事業的,并在這個體悟過程中受這些思想家行為的浸染而實現自我德性的完善。教師要把握住這點,拿捏好教學方向,讓學生在修人道的過程中無形間達至對德性共相的體認。這其實就是孔子所說的“下學而上達”,也是哲學教學中一條不斷更新自我的道德上升之路。需指出的是,這種道德上升之路不是通過強灌的方式,而是在對傳統哲學理解的基礎上潤物細無聲地引發心靈的觸動與共鳴,從而實現心靈的凈化和道德的完善。但哲學教學的路途不止于此。在參會、體悟天道德性之后,教師在教學中還要引導學生通過人道的方式把天道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下貫到自然萬物、人生倫常等“地道”中去,使自然萬物、人生倫常接受天道的規制和引領。這是教學中讓天道散為萬殊的下貫之路。在如何而為萬殊這一點上,要特別提醒需以“德性”為前提、以“為”為保障,也就是事為不在事之大小,而在人之道德、人之實際舉動。對于學生而言,具體表現為在學業攻讀、情感選擇、事業努力、走廊儀節、角落文明等平常事為中展現自我的人生追求和道德力量。事實上,許多古圣先賢都致力于首先從道德上來確認人的行為方式,孔子仁學、程朱理學等都是如此。在這個前提下,再貫之以不論大小、層次的各種生活實踐,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王陽明的“滿街都是圣人”才有可能成為現實。這樣,才能把課堂教學與生活實踐聯系起來,達到“課堂上有應用”的目的。
3.3 勵推流動的教學場景
中國哲學“貫”的靈動性,也必然要求哲學教學始終勵推流動的教學場景,形成一種動態的思想交流氛圍。這就意味著哲學教學要遵循哲學本質,采用與之相應的靈動教學模式。就課堂教學而言,這種靈動模式主要包括:
第一,“師—生”無阻礙思想交流。也就是說,教師與學生之間能就課堂教學內容展開自由對話。這是哲學教學取得流動性效果的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實際也是師之于生、生之于師的一個“對貫”靈動模式。要做到這一點,教師對講授的內容自然要做到爛熟于胸,準確把握哲學思想的核心實質。在講解過程中,教師除了采用一些哲學術語外,更重要的是能把一些看起來很深奧的哲學思想用學生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貼切地表達出來,如網絡語言、生活語言、聊天語言等,把流動的哲學思想用形象、通俗化的語言講活講透,有意識地引導學生把思維的焦點放到課堂教學上來,勾起學生內心深處的交流欲望。這對于非哲學專業的學生來講尤其具有語言的吸引力。通過這樣的方式,形成學生想說、敢說、能說的心理機制體系,久之則會自覺地把教師和教學內容納入到學生的心理機制體系之中,從而樂于和教師交流看法,師生之間在課堂上的自由對話就有望實現。
第二,“生—生”思想碰撞式交流。如果說“師—生”無阻礙交流是哲學教學中縱向流動的話,那么“生—生”思想碰撞式交流則是聯通多點的橫向交流。這種模式要求在所有學生中就某一或某些問題有共同的思考,并把這種思考通過語言在課堂上表述出來,從而形成集體性的思維流動。課堂教學中,每個學生都有一個或多個思考點,這些思考點有可能是相同的,但由于存在著理解方式和程度的差異,也很有可能是不同的。同或不同,都是思想交流的前提條件,關鍵在于怎樣把這些“同”或“不同”激發、創造出來。例如,王陽明的良知內涵包含兩個基本方面,即是非之心和價值根源,在理解“是非之心內在于我”時,這是否意味著行為主體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從而造成判斷的混亂?當我們說良知“生天生地”的時候,是從生成論還是從價值根源上來說良知?這些問題都是由良知內涵而來,也是學生感興趣的話題。圍繞這些問題,學生自然有相同或不同的看法,這時就可以順勢讓學生展開思想交流。學生可以互問互答,既可以是商討式的,也可以是辯論式的,只要言之成理,都要加以首肯。這種“生—生”思想碰撞式交流實際是“師—生”交流的互補,不僅能大大拓展課堂教學內容,也使得思想家的靈動思想通過這種對貫方式得以再現。
第三,站在思想者的立場進行思考。這是說,要把課堂上的教學主體置于每個哲學家所處的思想環境和在這環境中產生的問題意識,并進而體會他們對問題意識所采用的思維方式和解決途徑。很多哲學問題,在我們后人看來有時覺得不切實際、迂腐甚至是好笑,但我們是在有了當時人們不曾有的歷史知識和更廣闊的思維視野之后來看待同一個問題的,如果我們站在百千年之前,在相同的思想環境和精神氛圍中,我們會對同樣的問題產生有如此深度的思想智慧嗎?恐怕未必。我國先秦時期產生的諸子百家之學,是在當時周文疲敝、禮崩樂壞的思想環境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他們的思想主張,其實都是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實施社會救治,都是對社會弊病所開出的治癥藥方,而其中有些思想主張,因其不實用實際是行不通的,如儒家的道德之政、墨家的兼愛之說、道家的無為之治,但我們不能因此說這些思想就是迂腐無用、不切實際,實際上這些思想主張所表現出來的對于社會問題的深沉思考及其歷史文化意義,至今仍然有諸多探索價值。哲學教學,首要的是要走進思想家們的精神世界,沿著先哲們走過的思想軌跡去探尋,設想在同一時空里與他們共同探討宇宙和心靈的奧秘,從而發現歷史的真實、思想的真諦。這實際上是把課堂教學探討和過往思想家的思索貫連起來,能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古今之間的思想隔度。
哲學教學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它有許多方法值得繼承,也有諸多方式需要采掘。“一以貫之”作為一種哲學課堂教學的探討模式,既有經典的文本依據作為理論來源,同時也具備實際運用的諸多空間,可視為當前哲學教學的一種嘗試,它不僅適用于中國哲學的教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其他西方哲學的教學也具有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3]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責任校對游星雅)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5884(2016)01-0057-04
作者簡介:阮春暉(1974-),男,湖南隆回人,博士,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邵陽學院教改課題(2014JG28)
收稿日期:20150602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