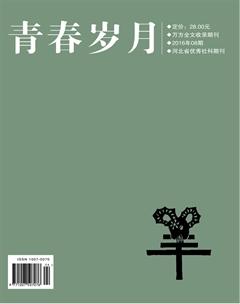試論漢代龍形象的藝術化表現
楊博
【摘要】漢代龍形象的藝術造型廣泛見于漢代的遺存中,其形體的造型風格及形象的樣式特征與當時歷史事件、神話故事緊密相關。通過對圖像的比較研究發現,含有漢代龍形象的物質遺存有著不同以往的觀看模式,并且漢代的龍形象的造型特征與實物的現實功能之間有著充分的內在聯系。
【關鍵詞】漢代;龍;造型;運用
一、研究背景
自從西水坡的蚌殼龍被發掘后,這一發現不但更新了人們對我國古代天文學水平的認識,而且說明了作為中華名族主要圖騰之一的龍形象,有著超乎人類想象的發展歷程。漢代是龍形象運用于造型藝術發展的井噴時期,其形象常見于墓葬儀軌儀式、宮廷建筑,日常用物等多方面。這些承載于各種實物的藝術形象盡管歷經千年之久,但大多數形體仍然使我們感受得到了其形神兼備的藝術魅力,具有多方面的藝術價值和實用價值。更進一步說,實物的功能訴求如何影響龍形象的表現風格與形式的問題仍有待探討。本文結合圖示與文獻,分析漢代龍形象的藝術特征與造型來源,進而了解并揭示藝術造型與實物功能之間的關系。
二、造型來源及特征
在漢代,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國內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都發展迅速。在此益于藝術發展的大背景下,大量雄渾有力的龍形象出現了,總的來說,漢代龍的造型可分為兩大類,一類身軀細長彎曲似蛇身,體態多變無定式,另一類身軀體胖渾圓如走獸,只是脖長尾巨。如此兩類的共同點,也就是使我們斷定為龍形象的依據是,漢代的龍必定有長而彎曲的巨角,雙眼突出怒睜,長而闊的巨口中有雙排利齒, 龍首顎下有彎曲飄然的長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形體塑造具有生動的表現力,并非只是較之前代龍形象多出了某些部位,而是富有創造力地去根據不同投資人的要求和喜好去表現。漢代龍顎下的龍須即是一個例子,青龍作為古代四神獸之一,常出現在漢代的瓦當上,此瓦當上的龍形象,昂首挺胸,四肢奔放矯健地擺動著,而龍須被處理成S形,可看得出工匠處理時的自信。需要解釋的是漢代的龍形象的龍須造型從無到有的理論依據,因為龍這一事物畢竟更多可能是一種虛構的動物,不存在具體的實物提供給世人模仿復制。筆者認為當時的流行文本為形體的造型塑造提供了充分的存在依據與想象基礎。《漢書》記載了有關龍須的一個事件,《漢書》載:“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龍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由此可以看出龍須是龍的重要特征,在漢代人觀念中有重要地位,更是皇家權威的象征之一。另外,漢人對于龍角的表達也是開創性的,造型同樣肯定有致,可看出這是一條舒身騰飛的青龍,全身呈“弓”字形,耳朵上的如龍角平滑彎曲,由粗至細,再由一重勾結束。這一巨角也不乏文本支持,東漢王充在論衡龍虛篇中載:“短書云: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而后世的段成式提出了新的看法: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依段氏所言,尺木似為龍角。龍如無角,其神性也白然大減,無法升天了。甲骨文中的龍字,角也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這也從側面證實了角對龍的重性。
由此可知,非模仿性的造型塑造并非憑空而來,首先帶有政治性或宗教性的故事為造型提供了必要的存在理由。而獨特的造型風格與樣式則是時人主動選擇,進而如何去創造。筆者以為,時人對龍這一事物認識的更新與豐富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造型塑造。陜西綏王得元墓出土的漆繪云龍紋或許可以說明這一創作規律,在一個規矩圓形的外框內部有一個非線性的構圖,龍身扭曲環繞其中,若仔細觀察整個畫面會發現除了龍形象外還有云氣紋的描繪,云氣的運行流轉動率與龍無異,云團貼于龍身而起,發端于極細小單線,轉而用封閉式雙線壯大云團。整個圖像飽滿精巧,不同元素之間和諧統一,仿佛建構了一個雙龍遨游于祥云之中,龍與氣體相互變幻的場景。畫面不但展現了與龍相關聯的事物,而且表現出了龍能夠騰云駕霧的特殊物性。在漢代,把活物把自然元素相結合,進而能夠制作出前所未有的表現形式,體現了觀念思想的深刻醇厚。《論衡·感虛篇》:“夫龍之登玄云,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云。云龍相應,龍乘云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古籍中有關龍形象的描述不但是具體的,而且不乏詩意,為時人的藝術創作增加不少有利因素。
三、觀看方式
龍形象作為中華名族的一種標識,其藝術形式從史前時期到清代,歷經數千年的變化,形成了各時代獨有的特征。這些特征的形成與轉變除了受到制作工具、工藝手段,使用受眾等因素變更的影響外,時人對“龍”的觀看模式的改變可看作是影響造型及風格的隱性因素。這里所指的觀看模式是指人眼聚焦一實物時的感知過程,首先從鎖定實物形象到所視對象被識別,繼而觀看者對龍形象產生特定的視覺官感和心理感應。這一基本模式,或者說這一觀看到識別再到意識感應的過程會由于物件形式與風格的不同,會存在內在的區別。為了進一步說明龍的藝術形象發展至漢代,其被審視的程式發生了改變的內涵,筆者選取從先秦至漢的玉質龍形器物進行縱向的比較,論述人們觀看它們時不同的視覺流程,進而試圖了解漢代龍形象的造型特征及其大致的運用原則。根據已發表的考古資料,迄今所知的龍紋玉器以公元前3500年左右紅山文化所出者為最早,其中最出名者是1971年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的一件C形玉龍,首尾明顯分開,吻部前伸,嘴緊閉,鼻端截面呈橢圓形,有對稱雙洞,表示鼻孔,雙目呈菱形,未見雙耳,頸后豎起一道彎勾狀長鬃。可以看出,此時的龍形造型塑造較為簡練,形體輪廓簡明,塑造時不失細節或者說龍的細節表現包含于征形。觀看時,器物的形體所示即是形象的全部,也就是說我們幾乎同時識別出了形制與形象,筆者認為可定性為強制性的觀看模式。
帶有禮儀功能的玉器在漢代依舊流行,以龍為塑造對象的玉器在形式上發生了轉變,觀看模式較之以前更為開放,審美性更強。漢代是龍紋造型的真正定型期,逐漸趨于表現龍的兇猛威武之態、翻云覆雨之勢、氣韻生動之神采。江蘇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的一件玉龍,龍體蜷曲呈“S”形,作回首狀,長尾上卷,器表遍布勾連云紋以示龍鱗,身邊飾以鏤雕云紋。此件器物較之看來要繁瑣許多,眼睛同時被多處鏤空而產生的正負形以及華麗的棱角所吸引,也幾乎是在同時,我們辨認出了主體形象,并回饋了相應的心理感受。但當我們注視龍的主要身體部位后,注意力必定被精雕細琢的邊界所牽引,如此的樣式揭示了龍與其他諸如云雨、火焰一類的因素的“互助”關系。相比較而言,上訴紅山文化出土的龍形器物屬于單次審美,而這件漢龍物件則提供了多次審美路徑,而且制造出了具有動感的幻境,凸顯了漢代人無窮的想象力。
四、總結
龍的形象在漢代的使用率極高,并且極具藝術表現力,不同的形式表現應用于不同的媒介與場所。其樣式與風格不是來自無度的憑空想象,而是受到了時人觀念與歷史事件的直接影響。形體造型作為一種視覺呈現方式,其內在的構成要素暗合了人類的視覺習慣,而不同的審美體驗和心理感應是造型藝術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1] 馮 時. 中國天文考古學[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2] 巫 鴻. 山盤山出土車飾與西漢美術中的“祥瑞”圖像,禮儀中的美術[J].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08-01,1.
[3] ﹝美﹞阿恩海姆. 朱疆源, 譯. 藝術與視知覺[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