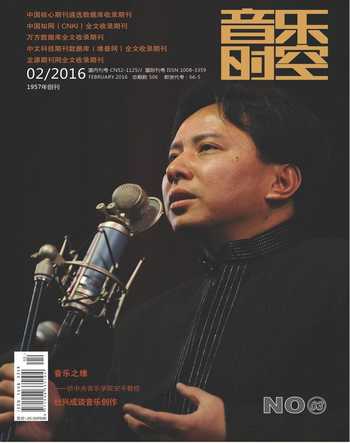傳統音樂文化在城市中的特征
張穎
摘要:隨著城市化的不斷進程,人口增多、流動率加劇,城市成為一個集多種身份、功能為一體的復合整體。亞文化、跨文化、移民文化、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民族或族群認同等一系列問題成為城市音樂文化研究的焦點。傳統音樂文化進入城市后,其音樂主體、身份、生存生態、傳播途徑與媒介等都發生改變。文章以城市中的蒙古族音樂為例,探析傳統音樂文化在城市中的多樣特征。
關鍵詞:城市音樂 傳統音樂 蒙古族音樂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城市中的亞文化群體、移民、社會性別、權利與政治等問題日益得到關注。外來人口的不斷涌入,使得城市結構發生改變,有著相同思維、相同文化認同的“族群”開始尋找并建立自身文化標識。城市音樂文化成為民族音樂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伴隨著人口的遷移而進入城市的傳統音樂成為尋求民族或族群文化認同的載體,它承載著歷史,也在不斷加快的城市化步伐中發生著變遷。正如杜亞雄所說,隨著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傳統音樂中的許多品種,出現了流行地域城市化、演出目的商業化、活動性質世俗化、表演曲目流行化和形式內容西方化等方面的轉變。
“蒙古族”作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行為方式上都極具特性,它有自己固定的組織方式、生活狀態和文化需求。“蒙古族音樂”正是他們對自身身份、文化認同的表現,意識形態的一體化、社會空間的國家化,使得傳統音樂呈現出現代多樣性。隨著城鎮化的進程,蒙古傳統音樂既不屬于國家權利干涉下的“主導文化”,也不屬于市場干預結果下的“主流文化”,而是逐漸在現代化的城市中成為了“亞文化”。
一、古今對話
歷史是一個不斷被書寫的過程,歷史事實與文獻記載、書面文本與口頭文本之間形成“互文”關系。中國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落于1628年從新疆向西遷移,至1630年到達俄羅斯伏爾加河中下游的草原,1771年東歸回到新疆。但隨著城市環境的變化,傳統音樂文化的生存、發展生態都發生了巨大改變,使得它不得不適應城市社會與經濟的節奏,以多重身份存在。
(一)作為標識的蒙古族音樂
民族是社會或國家之中建立在文化相似性或差異性基礎上的群體,族群成員的文化獨特性來自于他們的語言、宗教、歷史經歷等。中國傳統音樂文多元共存,各民族或族群內部在同化的基礎上追尋自身差異性。正如斯托克(Stokes)所言:“音樂行為能夠生動地體現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甚至能夠描繪出一個基于共同的音樂文化精神的‘想象的社會,通過音樂構筑局部與整體,自我與集體等關系,同時音樂創造活動也提供了社區集體生活——自我復制與變化過程——的背景,即音樂不僅反映社會意義也產生著社會意義。”民族或族群在與周邊文化相互影響的同時,會將某一傳統音樂文化作為凝聚族群性的工具,使之成為標識。
《江格爾》是蒙古族衛拉特部落的英雄史詩,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藏族《格薩爾》、柯爾克孜《瑪納斯》并稱“中國三大史詩”。新疆塔城地區和布克賽爾縣將《江格爾》作為對外的一張名片,大力打造江格爾文化品牌,已創作排演史詩歌舞劇《江格爾》、建立了江格爾說唱團、修建起江格爾廣場,投資1000萬元建成集文化交流、展演、資料陳列為一體的江格爾宮,并成功承辦了“中國新疆史詩《江格爾》國際學術研討會”。《江格爾》成為和布克賽爾縣的核心文化標識,也成為區別于其他蒙古族地區的最主要文化特征之一。
(二)作為商品的蒙古族音樂
近年來,旅游業越來越被人類學所關注,旅行者將異文化看做是可購買的商品,而當地人則將觀光者視為流動的經濟來源。旅游業成為一些國家與地區新的發展戰略,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逐漸灌輸、增長當地人的民族自豪感,鼓舞本地的藝術傳統。如每年10月都是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的旅游高峰期,秋季的胡楊林得到了大量中外游客及攝影師的青睞,因而很多當地牧民都開始經營農家樂,“胡楊人家”成為額濟納一道特殊的風景。而伴隨自然風光的,必然有蒙古長調等民族文化的輸出,這也成為了當地人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
二、傳播與媒介
隨著現代交流方式的變化,影音媒體的全面普及,文化、視覺與聽覺的關系不斷加深。城市音樂文化的傳播不再是點——點,而是點——面。傳播形式可以是文化交流式的展演,或是盈利性的音樂會等。報刊雜志、音響制品、廣播電臺、電視節目等都是傳統音樂在城市中的傳播媒介。
音樂節等大型的活動能在短時間內匯聚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到同一個地點,文化的變遷便在其中產生,當地不斷地輸出該社區、該族群的文化與認同,同時又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此時,圖形圖像、音樂實體、音頻影像等媒介則作為一個“窗口”向外界傳達當地人的思想、認同與文化。筆者曾以“蒙古音樂”為關鍵詞搜索豆瓣網的北京同城活動,整理發現僅2013年豆瓣上發布的蒙古音樂演出信息就有49則,其演出形式多種多樣,有個人的專場、樂隊的專場,也有小型樂隊或新興樂隊的聯合演出,這些活動現場大多會現場出售CD或DVD光盤,演出結束后,精彩的片段會上傳至互聯網,形成圖形圖像、音樂實體、音頻影像為一體的傳播網絡。
三、多元整合
隨著城鄉差距的縮小、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人口的遷移必然產生文化的碰撞,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后,除了受到快節奏、現代化的沖擊,必然會對自身原有的文化有所保留;城市人口在主流文化之外也不可避免地接觸到這些亞文化。傳統音樂就在這過程中演變,它不再是人們音樂生活中的唯一,而是當代多元音樂文化中的一員。無論是牧區還是北京,蒙古人自身的意識形態、風俗習慣等都與過去產生了一定區別,在大城市中會更大程度上受到“漢化”“主導音樂”“主流音樂”的影響,因此蒙古音樂一定不可能是一絲不變的原來面貌,而是整合了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因素。
筆者曾于2013年觀看Taan Towch①和杭蓋樂隊現場演出,在經濟機制下,樂隊要生存就必須有“市場”,“市場”又取決于樂隊的自身特征以及受眾群的審美,因此這兩個樂隊無一例外都保留了蒙古音樂中最具代表性的馬頭琴、呼麥等元素,建立起“蒙古族音樂”這一標簽,同時加入架子鼓、電吉他等樂器,從而保有“市場”占有率。
四、整治與權力
政治經濟是影響傳統音樂文化在城市中傳承與變遷的一個重要方面,國家政權、國家權力、國家綜合國力、國家經濟實力等都影響文化的發展。如:國家政治疆界的劃分,人為地將本是同一民族的蒙古人歸屬不同國家,在國家意識層面,他們分屬不同群體。然而從民族屬性來看,他們有共同的信仰、風俗、音樂,他們所呈現的文化并不分國界,都屬于蒙古族所特有。再如: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話語權增加,國際交流日益擴大,國際對中國的關注度持續升溫,這些都為杭蓋等樂隊能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并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由于現代城市的集中性、復合性、開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城市音樂文化的主體、身份、生存生態、傳播途徑與媒介等都發生改變,研究對象、視角等也不斷擴展。傳統音樂文化不僅連接鄉村與城市,也溝通古代與現代;以多重身份將多元文化整合起來,通過各類傳播媒介擴散,以適應城市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在傳統與變遷中并完成自身的認同訴求。
注釋:
①2013年12月7日本文作者觀看演出時,該樂隊名為“Taan Towch”樂隊,該樂隊現已更名為Horse Radio樂隊。
參考文獻:
[1]杜亞雄.民族音樂學家,請你也將目光投向城市[J].中國音樂,2011,(01).
[2]KayKaufman Shelemay,Soundscapes: Exploring Musicina Changing World,secondeditio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