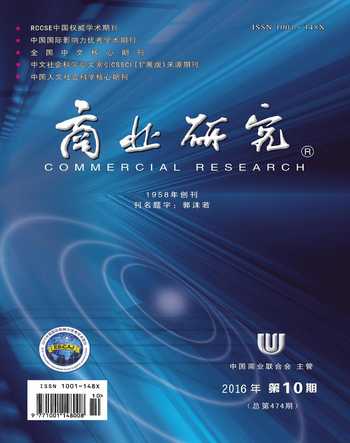重整期間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控制權之建構
李琳
摘要:公司破產重整時,債權人取代股東成為最終控制權人,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利益沖突加劇,司法權基于重整效率的考量介入到公司治理中,這些都決定和影響著債權人在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在現有制度下,我國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時嚴重缺位,最終控制權被法院、破產管理人架空。這不利于債權人利益的保護,扭曲了公司治理結構。為矯正公司治理結構,使債權人在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得以發揮最終控制人的作用,應引入債權人派生訴訟,賦予債權人在破產管理人選任方面的話語權,加強債權人對管理人財產處分權的控制,明確債權人有權決定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主體,補充債權人對債務人自行管理的事中監督。
關鍵詞:重整期間;公司治理;債權人控制權;債權人派生訴訟
中圖分類號:DF411.92 文獻標識碼:A
破產重整是公司身陷財務困境時選擇的一種拯救措施。債務公司希望通過重整恢復到正常經營狀態,但僅依靠原有的公司治理機制難以達到此目的。因為,公司重整時剩余風險承擔者和控制權人已由股東轉移至債權人。但債權人因受限于專業知識、時間等多方面因素,并不直接經營管理公司,而是授予專門的人員行使經營管理權。于是,有了最終控制權與經營控制權的區分。債權人作為重整公司的最終控制權人,應對重整期間公司治理的有關事項、爭議享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我國《破產法》有關公司控制權的規定并非如此,債權人在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與其剩余風險承擔者的角色并不匹配。鑒于此,考慮到公司重整時的特殊性,本文試圖圍繞我國公司重整期間債權人控制權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相關建議,以期為改善債權人參與重整公司治理的現狀提供可行的理論支撐與實踐指引。
一、重整期間債權人控制權之理論分析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公司治理”指公司內部的監管決策,其本質是在現代公司基本的產權結構下有關公司控制權的分配、行使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現代公司產權結構的基本原理是“誰投資誰所有”,故公司所有權由全體股東共同享有。公司所有權的核心是剩余權,包括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公司正常經營時,股東即是剩余索取權人。現代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要求剩余索取權人擁有公司控制權。因此,在公司正常經營的情況下,股東作為剩余索取權人享有公司控制權。但“狀態依存所有權”①告訴我們,在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企業的所有權安排會發生變化,這使得重整期間的公司治理具有不同于非破產下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一)債權人成為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的最終控制權人
股權和債權對公司財產的不同主張,構成了公司財產最基本的分配,而債權相對于股權具有優先性。當公司資不抵債進行破產清算時,公司財產優先清償未被清償的債權人。股東的剩余索取權變的沒有經濟價值,債權人成為剩余索取權人。但若進行破產重整,公司仍繼續運轉,此時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所有者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因為,重整中實施的商業決策直接影響了股東的分配利益,股東享有或喪失剩余財產的索取權。按照企業理論剩余索取者也即企業的風險承擔者。公司正常經營時,公司資產只有按照事先的契約規定向利益相關者支付完畢之后,才能對股東進行盈余分配。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的“固定索取權”②是可預期的,而股東的投資收益則是隱形的、不確定的,股東是剩余風險承擔者。但當公司遭遇財務困境進行破產重整時,債務人為挽救公司與債權人談判,使債權人在重整計劃中做出一定的妥協與讓步。這使得債權人無法通過合同規制保護其自身利益,且須承擔企業重整失敗的風險,債權最終可能得不到清償。對此,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在破產狀態下,債權人作為剩余風險的承擔者應從股東手中接過公司控制權。其實,控制權轉移的基本道理就是債權人承擔剩余風險時,比其他主體有更大的激勵作出適當的決策。破產法也對此作出了相關規定,如賦予債權人會議享有決定債務人是否營業的權力。然而,身為控制權人的債權人卻不能像股東一樣不受約束地擁有公司的控制權,這是因為重整制度具有社會本位性與政策目標性。如破產法第87條賦予法院享有特定條件下強制批準重整計劃的權力,正體現了重整制度對社會本位的價值追求,這使重整期間的債權人控制權受到了一定制約。
(二)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沖突變得尖銳
在公司財務狀況正常的情況下,債權人與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并不明顯。因為,此時債務人公司的資產能夠保證任何一個債權人實現其債權,且還有剩余分配給股東。例如,某公司負債100元,凈資產為1 000元,現有三種投資方案A、B、C。A方案:公司50%可能獲利300元,50%可能損失200元;B方案:50%可能獲利400元,50%可能損失500元;C方案:公司50%可能獲利200元,50%可能獲利40元。管理者無論實施A、B、C哪種方案,都不影響債權人對債務公司財產的債權主張,債權人并不關心債務公司的投資決策。然而,在公司財務狀況惡化的情況下,債權人則希望管理者選擇沒有損失風險的C投資方案,而股東卻傾向風險較大、收益較高的B投資方案。因為,如果投資成功,高風險帶來的高回報于股東而言即意味著可能有剩余分配,但于債權人而言僅意味固有債權的實現。而一旦投資失敗,債務人的財務狀況會進一步惡化,清償力會進一步減弱,債權人的債權實現率便會進一步降低,而股東在有限責任的保護下卻只如方案實施前一樣得不到分紅而已。因此,破產狀態下債權人與股東的投資偏好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兩者間的利益沖突加劇。公司治理的功能在于配置權、責、利。利益分配是公司的終極價值。而重整程序的啟動不僅不意味著利益爭奪的結束,反而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利益沖突變得尖銳。這勢必影響了債權人在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的角色與作用。
(三)重整期間公司自治理論得以突破
在實然狀態下,債務公司為了破產重整與債權人談判,使債權人在重整計劃中做出債權讓步。債權人的固有利益無法通過契約予以保護,且須承擔企業重整失敗的風險。債權人的契約保護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契約本質上是不完備的,即“不完備契約理論”③。正因為契約是不完備的,才有了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各個契約當事人間的分配問題,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公司治理問題。當公司陷入財務困境進行破產重整時,債權人取代股東成為實際上的剩余索取人和風險承擔者,控制權也因此而轉移。重整期間控制權的轉移和擴張如果能用契約理論創設和規制,則無需司法權介入。但此時,因公司財富的稀缺性,利益沖突變得復雜、尖銳,當事人間的談判成本增加,往往遲遲不能達成協議,以致無法重新安排彼此間的權利義務。“波斯納曾強調正義的第二種含義——也許是最普遍的含義——是效率。在資源稀缺的世界中,對效率的追求,便是最大的正義。”科斯在其談判理論中即指出實現效率的最佳途徑是自愿合作。但實際上,重整制度中存在著諸多阻礙當事人自愿合作的因素。由此,需要司法權介入,使司法裁判適時取代當事人談判,以對當事人的權利體系重新調整。事實上,司法發揮了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應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率最大化為目的。重整期間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是重整制度的本性使然,由此也產生了控制權在法院與債權人之間的配置問題。
二、重整期間債權人控制權的現有制度之檢視
公司破產重整時,剩余控制權從股東轉移至債權人。但與公司正常經營相同的是,分散的債權人因受限于專業知識、時間、能力等多方面的要求并不直接經營管理公司,而是由他人行使經營控制權,債權人則作為最終控制權人參與公司治理。重整期間的經營控制權指管理、處分破產財產,經營各項業務的權力(利)。經營控制權是重整程序的桎轄之桎,其配置關乎公司能否成功重整。在世界范圍內,圍繞經營控制權的重整公司控制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債務人自行管理模式,也稱為占有中的債務人(DIP),如美國;二是管理人控制模式,如英國。我國《企業破產法》第13條、73條、74條規定了經營控制權,可分三種情況:一是管理人管理;二是在管理人監督下的債務人自行管理;三是管理人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負責營業事務。可見,我國重整期間的公司控制權模式為“管理人中心主義”,下文將具體分析此種模式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管理人管理債務公司時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當事人提出重整申請至法院受理期間債權人控制權缺位。破產法規定管理人產生于法院受理之時,從當事人申請破產到法院受理有15到37天的時間,也就是說這段時間仍是債務人自行管理。但是,債務人有可能在這期間轉移或隱匿財產、實施偏頗性清償等,債權人可能主張擔保債權、申請強制執行等。《企業破產法》第31條、32條、33條雖規定了某些不當減少破產財產的行為無效或可撤銷,但這三條對破產財產的保護遠遠不夠,無法禁止那些有執行優勢、尚在民事程序中的債權人在這段時間獲得清償。這不僅不利于債務人保有財產實現重整,而且對其他債權人也不公平。何況債務人在身陷財務困境時,卻還要顧及繁瑣的訴訟,處理各種訴訟事務,這顯然也不利于破產財產的保值增值。不僅如此,在債務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申請重整時,股東的剩余索取權變的不確定,對公司管理層的控制力減弱。然而,此時管理人、債權人會議并不存在,以致公司管理層處于一種近乎不受任何主體約束、權力被放大的地位。其很可能為謀取自身利益而實施不利于公司運營的商業決策,從而損害公司、債權人、出資人的利益,也可能與某一方當事人勾結而損害其他當事人的權益。總之,法院受理重整申請前債權人控制權的缺位易導致不公平清償、破產財產減值、經營控制權膨脹等結果,使債權人的整體利益受到威脅。
第二,在管理人選任方面債權人與法院控制權錯位。破產法規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而作為最終控制權人的債權人,卻只享有請求法院變更管理人的權利,但是否變更仍由法院決定。雖然司法權介入公司治理是重整程序的本性使然,但過分加大法院的權力會扭曲重整期間的公司治理結構。法院作為居中裁判者,無論選擇什么樣的破產管理人都不會影響自身,卻可能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出資人的利益,使決策者和風險承擔者不一致,這不符合經濟學理論的要求。而且,如此規定使債權人無法像股東一樣用投票權制約管理者去留。而控制權主要表現為投票權,擁有投票權就擁有契約中未予說明事項的決策權。債權人投票權的缺失大大削弱了債權人對管理人的控制力,使債權人在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另外,《企業破產法》第24條規定了可擔任破產管理人的三類主體,須注意的是清算組為管理人的情況。由《指定管理人的規定》第19條可知,清算組的組成中包含政府部門人員。由18條規定又可知人民法院在4種情形下可指定清算組為管理人,而作為第4種情形的兜底條款,無疑把是否指定清算組為管理人交由人民法院自由裁量,事實上法院也多指定由政府官員為主組成的清算組擔任管理人。然而,重整事務的專業性較強,政府官員為主的清算組能否勝任工作令人懷疑。不僅如此,政府也有可能趁機對公司的經營管理進行不正當的行政干預,或者阻礙公司運營發展,或者為某一方謀利而損害其他當事人的利益。總之,我國現有的僅由法院選任管理人的模式極易導致法院、政府對重整公司治理施加不正當的公權力干預。
第三,在約束管理人財產處分權方面債權人控制權缺位。《企業破產法》第26條規定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之前,管理人決定繼續、停止營業或實施某些財產處分行為應當經人民法院許可。債權人是重整期間的剩余風險承擔者,管理人欲實施的涉及公司財產增減,關乎公司生存死亡的行為,勢必影響債權人利益的實現,債權人應有權決定是否許可。重整程序的社會本位性使債權人的控制權受到一定限制,但這并不表示法院可以當然替代債權人控制。26條的規定顯然又加大了法院在重整公司治理中的份量,造成債權人控制權的缺位。此外,《企業破產法》第69條規定管理人實施某些對債權人利益有重大影響的財產處分行為,應當報告債權人委員會或法院,“報告”二字表明管理人實施這些行為不需要債權人委員會或法院的批準。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后破產法反而降低了債權人和法院對破產管理人的監督級別,改“批準”為“報告”。如此規定給了管理人相當大的自由,使其能及時實施某個商業決策,以免受到債權人、法院過多的限制而錯過商業時機,提高了重整的效率,但卻可能引發管理人的道德風險。因為,我國破產管理人的組成、選任方法等存在各種弊端,破產管理人隊伍的專業素養和職業精神無法保證。若對其在經營管理中實施的某些行為不加審查,很可能出現損害債權人、公司、出資人利益的后果。其還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身或某一方謀利而損害其他人的權益,甚至損害公共利益。總之,重整期間債權人對管理人財產處分行為的控制嚴重缺位。
(二)債務人自行管理時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在決定債務人能否自行管理方面債權人控制權缺位。《企業破產法》規定債務人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須有兩個前提條件,即債務人申請和法院批準。但是,并沒有規定在何種情況下債務人可申請自行管理,以及法院批準債務人自行管理的條件。規則的缺失、不明確必然導致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擴張,權力的擴張會導致權力的濫用。一方面,債務人為得到公司的控制權很可能與法官產生共謀,在其掌握公司的控制權之后,又可能實施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至此,公司控制權演變為債務人逃避債務,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眾所周知能擔任破產管理人的主體里有一類為“清算組”,而清算組的組成中主要是政府官員。在政府的權威下,法院可能不會批準債務人自行管理,而是由清算組擔任管理人管理債務公司。至此,公司控制權又可能異化為政府干預公司治理,干擾市場配置資源的手段。現代企業理論強調企業的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應盡可能地匹配,即權力與責任(風險)的分布應盡可能對稱。如果擁有控制權的人不對使用權力的后果負責,便不可能真正負責任地使用權力。法院作為獨立的審判機構,在重整程序中并不享有當事人的利益,其不管作出任何決定,都不會對自身造成實質的影響。而債權人卻不同,其作為剩余風險承擔者卻要為法院控制權的行使后果買單,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債權人基于剩余索取權理應有權決定重整期間經營控制權的主體,破產法不應將這一影響債權人利益的實體性權利賦予法院,造成債權人與法院控制權的錯位,如此定會扭曲公司治理結構。
第二,在債務人自行管理方面債權人監督權缺失。如果一個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擁有完全的所有權,那么他會實施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管理決策。但實際上,風險能力的分布與經營能力的分布是不對稱的。其實,這就是所謂的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理論。兩權分離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委托代理問題的產生。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希望達到自身效用最大化,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公司管理者并不總會做出有利于所有權人的決策。因此,代理問題的要點就在于促使代理人采取適當的行動,以最大化委托人的福利。靠什么克服代理問題,用什么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風險,答案便是“監督制衡”。我國破產法有關債權人對債務人自行管理的監督權規定僅出現在第78條中,主要指在債務人有欺詐、惡意減少債務人財產或者實施其他顯著不利于債權人的行為的情況下,債權人可申請人民法院終止重整程序,宣告債務人破產。由此可知,債權人對債務人自行管理的監督是一種事后監督。事后監督表現為“秋后算賬”,是對錯誤決策的一種彌補,但往往是亡羊補牢,為時已晚。我國破產法規定的債權人事后監督權,于債權人而言顯然是“亡羊補牢”。因為,前后程序轉換導致的清償拖延,以及破產財產的貶值都進一步降低了債權人的受償率,而未能有效地彌補債權人的損失。總之,“監督”是分離關系無法避免的結果,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監督機制才能真正解決代理問題。我國應改進債權人的這種單一的事后監督方式,輔之以其他監督方式,“以使代理人偷懶、不負責、攫取公司財富的行為被降低到最低點”。
(三)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受聘時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在是否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負責營業事務方面,債權人決定權缺失。我國破產法規定管理人可以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負責營業事務,但沒有規定聘任的方式和程序。《企業破產法》第28條規定管理人聘任工作人員需要得到法院的許可。參照28條的規定,經營管理人員的聘任似乎也需要得到法院的許可。實踐中也確實如此,管理人在向法院申請繼續營業時往往一并將該事項納入,法院在批復中予以明確。管理人之所以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是因為其經營能力和專業知識有限,需要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協助其完成重整工作。故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的行為關乎公司的運營和發展,會影響債權人的受償利益,債權人須為受聘人員的行為承擔風險。然而,破產法卻把這一關乎債權人利益的實體性權利再次賦予了法院。此外,須注意立法者在此用了“可以”而不是“應當”,表明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不是管理人的義務,而是一種自由行使的權利。以常人的邏輯推斷,管理人為了獨享公司控制權,可能不會向法院申請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與其分享同一杯羹。事實上,由管理人提出,法院批準,而債權人卻不參與的聘任規則,使得此種公司控制情況在實踐中鮮有發生。
第二,當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與破產管理人意見相左時,債權人決斷權缺失。我國破產法規定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只負責營業事務,并不享有管理破產財產的權力。重整期間公司繼續營業的實際上是資金在流轉,既有資金流入也有資金流出。破產財產不是靜態的財產概念,而是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公司正負財產的集合。財產管理和營業事務無法完全割裂,企業的經營活動總是伴隨著財產的處分、資金的流轉。如果經營管理人員實施的經營決策涉及到財產處分的,且財產處分策略與破產管理人處分財產的方案矛盾,此時是聽從管理人還是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法律并沒有規定。管理人與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按照委托代理關系理論,當委托人與代理人意見不一致時,當然聽從于委托人。據此,應該以管理人的方案為準。但是,管理人之所以會聘任經營管理人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人不擅長公司事務的管理。其作出的方案并不一定正確,而經營管理人員的決策可能更有利于公司財產的保值增值。遇到此種情況,應該由剩余索取權人——債權人作出決斷,以便權力行使與風險承擔盡可能地對稱。債權人享有最終決定權并不違背委托代理關系理論,因為對債權人來講,破產管理人也是其受托人,美國破產法就稱之為“破產受托人”(bankruptcy trustee)。其實,按照所有權理論,于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而言,債權人乃其真正的委托人。
三、重整期間債權人控制權之制度建構
法院作為司法裁判者,基于重整效率的考量介入到公司治理中。只能在當事人存有爭議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為保證重整程序的順利進行行使程序性權力、裁決權力、審查確認權力,如主持召開第一次債權人會議、確認債權、審查通過重整計劃等,不應享有屬于債權人的關乎債權人利益的實體性權利。破產管理人是破產程序的受托人,對債權人負有受信義務。其一切職務行為的后果都指向債權人,債權人理應有權監督管理人以免其濫用職權,損害債權人利益。然而,我國立法設計中債權人作為最終控制權人的地位嚴重弱化。很多情況下不是債權人會議或債權人委員會,而是人民法院擁有決策權,且法院選任的管理人一定程度上也架空了債權人的決策權和監督權。因此,應重塑債權人的控制權,以使債權人能真正地參與到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
(一)引入債權人派生訴訟以彌補其缺位現象
我國破產法對債權人的保護主要表現為債權人會議或債權人委員會集中行使控制權。然而,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前,如果公司的經營管理層或公司外的第三人實施了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從而間接損害了債權人的分配利益,單個債權人卻無法行使最終控制權以保護債務公司利益。此時,有必要引入一種類似于股東派生訴訟的制度,即債權人派生訴訟。關于債權人訴權的正當性可用“相機治理理論”④予以解釋。按照此理論,當公司破產或瀕臨破產時,債權人在公司受到損害的情況下,有權以維護公司利益的目的,代表公司行使訴權。債權人派生訴訟制度不僅保護了公司利益從而間接維護了債權人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加強了債權人對公司經營層的監督和制約力度。在制度的具體構建上,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原告主體資格問題。我國《公司法》第152條對股份有限公司提起派生訴訟的股東作了持股時間和比例的限制,這是為了以防某些主體通過“購買股份”進行濫訴,致使公司受到不必要的訴訟干擾。因為,股東派生訴訟中公司雖然不是原告,但因案件結果與其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在我國以往的司法實踐中通常被列為第三人而參與訴訟⑤。“但提高原告訴訟資格對預防濫訴并無必要性,而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進行訴訟擔保。因為并不是訴訟的重要性程度決定了是否屬于敲詐訴訟,而是勝訴概率決定著是否屬于敲詐訴訟(strike suit)”就債權人派生訴訟而言,更沒有限制原告資格的必要性了。因為合同具有相對性,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前債權人之間并無聯系,彼此并不認識。如果法律規定須有一定人數或合計達到一定債權數額的債權人才能提起派生訴訟,無疑使引入債權人派生訴訟的目的落空。因為此制度正是為避免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前,單個債權人無法發揮最終控制權人的作用而設計的。因此,對于債權人的派生訴訟,不應該在債權人人數與債權數額方面作限制性規定。
第二,債權人派生訴訟的前置程序。債權人派生訴訟是由股東派生訴訟演變而來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都對股東派生訴訟規定了前置程序,我國公司法也不例外。前置程序的設計是因為考慮到股東所享有的權利派生于公司,債權人派生訴訟也是如此。況且單個或少數債權人因限于專業知識、信息等多方面的因素往往并不具有正確的判斷能力,其判斷與公司判斷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如果使債權人在不告知公司管理者的情況下就隨意提起訴訟,其很可能是徒勞無益的。不僅浪費司法資源,也可能使公司因疲于應付訴訟而無心經營管理。故就債權人派生訴訟而言,建議法律規定在重整申請受理前,債權人須首先告知董事會、監事會,請求董事會或監事會提起針對侵害人的訴訟;在重整申請受理后,對于管理人管理的重整案件,債權人須首先向管理人發起訴訟請求,而債務人自行管理的仍須先向董事會、監事會發起訴訟請求。總之,債權人派生訴訟依然需要貫徹前置程序規則,只有當公司怠于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才可以“代位”提起訴訟。
第三,訴訟費用承擔問題。債權人向法院提起派生訴訟,需要預繳案件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用。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受理費的收取按案件類別區別對待,債權人派生訴訟顯然屬于財產類案件。財產案件的受理費是以訴訟標的額的大小為基準,按一定比例收取的。而債權人派生訴訟通常涉及的財產金額較大,故訴訟費用一般較高。我國民訴法雖規定,原告勝訴時其預繳的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但起訴時高額訴訟費用的籌集并非易事。且律師費在我國不屬于法定訴訟費用,原告無論勝訴、敗訴都需要自行承擔。至此,個別債權人若非出于個人偏好,實在想不到為何會自甘承擔律師費用及其他非法定訴訟費用去維護“集體/公司利益”,而自身并不能直接獲得實際的賠償。當實現權利再分配需要的交易成本小于其可能增加的價值時,權利才會被重新配置。由此,若要債權人派生訴訟不成為那朵只能遠觀的美麗蓮花,原告債權人勝訴時所支付的律師費及其他合理費用也應獲得補償。其實,這種補償制度在一些國家是有先例的,如英國、美國、日本。具體如何補償,本文認為須區分派生訴訟終結日是在重整申請受理前,還是受理后。對于重整申請受理前終結的訴訟,原告債權人可主張受理費、申請費、律師費等合理支出用公司從侵害人處獲得的賠償金額予以補償。對于重整申請受理后終結的訴訟,原告債權人支付的合理費用應視為“共益債務”⑥,從破產財產中隨時撥付。
然而,這里還存在一個“搭便車”的問題。因為于提起訴訟的原告債權人而言,即使其勝訴,也只能待財產分配時按債權比例主張一定的合同收益權;但若敗訴,卻需要承擔高額的訴訟成本。所以,在債權人看來與其主動提起訴訟,不如觀望,免費搭車占別人的便宜,而最終的結果可能是無人提起訴訟。因此,為制止搭便車的現象,提高債權人的訴訟熱情,法律需要設計一項激勵措施。對此,美國判例法賦予原告債權人一定的直接受償權。美國的做法給我國以啟示。不過考慮到派生訴訟維護公司利益的本意及破產程序啟動的目的,筆者認為原告債權人不宜直接從敗訴方那獲得索賠,賠償利益仍應歸于公司。但是,在債務公司財產擬分配時,原告債權人可主張其一定比例的債權優先于其他未提起訴訟的普通債權人的債權受償。總之,為確保債權人派生訴訟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建議對勝訴債權人支出的包括律師費在內的一切合理費用予以補償,并提高其一定額度內債權受償的優先等級。
(二)債權人應介入破產管理人的選任
破產管理人是在破產程序中管理破產財產及公司各項營業事務的破產受托人。選擇什么樣的破產管理人,關系到其能否盡忠職守的完成重整工作,公司重整成功的可能性,債權人利益的實現程度。因此,不應該把這一關乎債權人利益的重要事務僅交由法院處理,債權人理應介入破產管理人的選任。在破產法制發達的美國就是采取由利益相關者選任破產信托人的做法,而法庭僅在是否任命破產受托人方面享有裁定權。美國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但是,我國的控制權模式是“管理人中心主義”,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請的同時就須指定管理人。而美國主要是DIP管理,只有當債務人的經營管理層存在管理不善等類似原因,或為維護債權人、股權持有人等相關者利益時才任命破產受托人。鑒于此,我國立法可以這樣設計:在破產申請受理時,人民法院指定臨時管理人。臨時管理人若想成為正式的管理人接管公司,須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時,由出席會議的有表決權的債權人過半數通過,并且其所代表的債權額應占無財產擔保債權總額的二分之一以上。如果債權人會議未能表決通過,則出席會議的債權人有權從管理人名冊中重新選任破產管理人。如此設計一方面破解了我國立法規定破產管理人產生于法院受理之時,而此時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卻來不及召開的矛盾局面;另一方面又確保了債權人對破產管理人選任的參與,能對債權人與法院的控制權錯位予以一定矯正,使債權人的最終控制權人地位得以彰顯。另外,因公司重整時股東仍享有一定權益,故應賦予股東一定的話語權。股東(大)會可以向債權人會議推薦管理人的人選,也可與債權人協商確定管理人,并由債權人會議作出任命決定。總之,重整期間債權人作為最終控制權人應有權決定破產管理人的人選,法院任命的臨時管理人若不能盡職盡責地為債權人利益服務,便會面臨被債權人撤換的命運。
(三)加強債權人對管理人財產處分行為的控制
現代公司法確立了司法有限介入原則,表達了司法對公司決策機關商業判斷的尊重,不會輕易使用公平正義的法理念去評判公司自治事務。重整期間公司控制權的轉移和擴張使得司法有限介入得以突破,但無論如何法官不是公司管理者,其作為審判機構能否對重整程序中關乎企業運營、發展的財產處分行為做出正確的商業判斷著實令人懷疑。美國《破產法典》第554條規定經過通知和聽證之后,破產受托人可以放棄某些財產,但放棄的財產須是破產財產且須是累贅的、不重要的、無益于債務人的財產。破產法庭只需要確認放棄財產的決定是破產受托人基于誠信做出的合理商業判斷,檢驗商業判斷的標準為“最低減讓財產”。美國的做法值得我們反思,我國有必要對重整期間公司治理中的司法權控制予以一定限制,把公司內部事務的最終決策權還給最具有發言權的控制權人——債權人。建議對關乎債權人利益的不屬于“最低減讓財產”⑦的重大財產,建立債權人委員會對管理人處分行為的許可制度。即原則上管理人實施的關乎債權人利益的重大財產處分行為,須首先得到債權人委員會的許可;但在不及時實施財產處分便會給債務人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以致公司無法實現重整的情況下,破產管理人可以無須事先征得債權人委員會的同意就作出財產處分的決定,不過緊急處分后破產管理人仍須及時告知債權人委員會。這樣一方面能確保破產管理人及時實施商業決策,提升公司財產價值,提高公司重整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能夠防止破產管理人隨意放棄某些對債務人重整有重要作用或價值的財產,以免影響重整程序的順利進行,從而損害債權人的分配利益。總之,在破產管理人財產處分行為的控制權分配上,應把更多的決定權分配給利益相關人——債權人,而非不相干的法院。
(四)明確債權人有權決定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的主體
首先,債權人有權決定重整公司由管理人管理還是債務人自行管理。如果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請時即準許債務人自行管理,則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時,債權人可按照破產法第64條的表決規則決定是否由債務人繼續管理。即若出席會議的有表決權的債權人過半數贊成債務人自行管理,并且其所代表的債權額占無財產擔保債權總額的二分之一以上,那么債務人便可繼續管理公司。反之,債務人不能繼續管理公司。債權人會議可以申請法院撤回自行管理的批準,并作出由管理人接管的決定。當然,債權人會議既可以任命法院選出的臨時管理人為正式的管理人接管公司,也可以重新選任管理人。但是,如果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請時沒有準許債務人自行管理,則在第一次債權人會議召開時,債權人可作出決定使臨時管理人成為正式的管理人繼續管理公司,也可選任新的管理人接管公司,當然還可決定由債務人自行管理。其次,債權人有權重新選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層。重整程序的啟動切斷了公司管理層對股東的受信義務,管理層對股東的忠誠轉移給債權人。在債務人自行管理的情況下,管理層作為債權人的受托人為公司利益行使經營控制權。如果債務人的經營管理層實施了損害公司,進而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債權人會議或債權人委員可代表全體債權人行使委托人的權利,重新選出新的管理者。具體流程和方法可以比照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的相關規定。最后,債權人有權決定是否聘任債務人的經營管理人員負責營業事務。破產管理人與其聘任的經營管理人員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經營管理人員對破產管理人負責,并最終對債權人負責,其行為后果由債權人承擔。故債權人有權過問經營管理人員的聘任事務,是否聘任由債權人會議或債權人委員會表決決定。此外,當受聘的經營管理人員實施的商業決策與管理人作出的方案相左時,作為剩余風險承擔者的債權人應該享有最終的決定權,債權人會議或債權人委員會可通過投票表決的方式選擇其中一種方案。
(五)債務人自行管理時,增加債權人的監督方式
目前,我國債權人對債務人的監督方式形式化、單一化。應補充債權人對債務人的事中監督,以便及時發現經營層的管理錯誤,將債權人的利益損失盡可能地控制在最低點。但若由債權人直接對債務人進行事中監督,無法保障及時性。因為,債權人會議并非常設性機構,且債權人委員會又非必設機構。鑒于此,可考慮將債權人的部分監督權授于管理人行使,但為避免管理人架空債權人,須保證債權人可以隨時了解管理人的監督成果。管理人可以通過專項調查、階段性報告等方式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監督,且債權人有權隨時查閱管理人的調查結果和債務人提交給管理人的報告書。不僅如此,若管理人在行使監督權的過程中,發現債務人實施了有損債權人利益的行為,應及時報告債權人委員會,未設債權人委員會的應及時報告人民法院。此外,須知在債務人自行管理的情況下,監事會對公司的經營管理層仍享有監督權,監督職能并未喪失。因此,債務人自行管理的其經營管理層不僅要受破產管理人監督,還要受監事會監督。但這兩個監督主體所代表的利益卻不同,管理人代表的是最終控制權人——債權人的利益,并兼顧債務人、出資人、社會公共利益,監事會僅代表股東利益。當管理人作出的監督決議與監事會的決議存在沖突時,應以管理人的決議為準。因為,重整程序不是以保護股東利益為目的的,而是為公平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社會公共利益而設計的。但無論如何,監督關系的起點和終點都要立足于債權人,管理人也好債務人的經營層也罷都要向債權人負責。
注釋:
① “狀態依存所有權”指不同的經營狀態對應著不同的企業所有權安排,股東只是公司正常經營下的企業所有權人和公司控制權人。參見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89.
② “固定索取權”是指債權人基于與公司訂立的契約而享有的合同收益權。
③ 如果一個契約能夠詳細說明未來可能出現的所有狀態,每種狀態下各方當事人的權利(力)、義務、責任,以及權利和義務的執行機制,那么這樣的契約就是完備的,否則就是不完備的。但實際上,由于現實中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及未來的不確定性,契約當事人不可能訂立一份涵蓋所有情況包含當事人間所有權利義務的完美契約,契約只能是不完備的。參見張維迎.理解公司:產權、激勵與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42-143.
④ “相機治理”是指企業控制權隨著企業績效、財務狀況或經營狀態的變化而相應地向不同的主體進行有序地轉移。主要是為了有效解決這么一個問題:在企業績效、財務狀況或經營狀態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了利益相關者(所有者、債權人、員工等)利益的時候,會自動啟動某種機制(比如在《破產法》或債務契約中進行相應的規定或安排),將企業控制權在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作出重新安排,以便實現對企業治理結構的重新調整。馬勝.企業破產制度重構——一個基于相機治理分析的研究框架[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29-30.
⑤ 有學者認為公司在派生訴訟中的第三人地位值得商榷,具體論述參見劉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創新:立法爭點與解釋難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63.還有學者認為在派生訴訟下公司必然是被告,參見鄧峰.普通公司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398-401.
⑥ 共益債務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為了全體債權人的共同利益而產生的費用,不是常規性支出。而破產費用是在破產程序進行中和債務人財產管理過程中產生的常規性和程序性支出,不支出的話,破產程序就無法正常進行。筆者認為債權人派生訴訟所產生的費用不具有破產費用的常規性特點,且維護了全體債權人的共同利益,應認定為共益債務。
⑦ “最低減讓財產”指對破產財產或債務人重建只有很小或沒有作用或價值的債務人財產。
參考文獻:
[1] 陳政.放權與控權:破產管理人破產財產處分權的合理配置[J].河北法學,2014(5).
[2] 甘培忠.公司控制權的正當行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5.
[3] 賀丹.破產重整控制權的法律配置[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199.
[4] 蔣大興.公司法的觀念與解釋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11.
[5] 楊勤法. 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以司法介入的限度和程序設計為中心[J].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
[6] 郁光華,伏健.股份公司的代理成本和監督機制[J].經濟研究,1994(3).
[7] 魏建等.法經濟學:基礎與比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3.
[8] 王欣新,李江鴻.論破產重整中的債務人自行管理制度[J].政治與法律,2009(11).
[9] 張維迎.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兼評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觀點[J].經濟研究,1996(9).
[10]張春霖.存在道德風險的委托代理關系:理論分析及其應用中的問題[J].經濟研究,1995(8).
[11]張婷.中國重整程序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研究 [M]//李曙光,鄭志斌.公司重整法律評論(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87.
[12][美]弗蘭克·伊斯特布魯克,丹尼爾·費希爾. 公司法的經濟結構[M].羅培新,張建偉,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1.
[13][美]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M].盛洪,陳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
[14][美]詹森等.公司治理經典文獻選編[M].宋增基,李春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6.
[15]11 U.S.C.§1104.
[16]11 U.S.C.§554.
[17]Lynn M. Lopucki and William C. Whitford,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of Large,Publicly Held Companies[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93,3(141): 684.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rol Right of Credito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during
Reorganization
LI Lin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When a corporation enters into the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procedure, the creditors replace the shareholders as the ultimate controller,and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creditors and the debtors become sharp; the judicial power based on efficiency considerations interven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ll of these have an impact on the creditors′ role effec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during reorganization.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creditors are seriously absent from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ultimate control of the creditors has been undermined by the court and the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This not only is in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interests, but also distort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make the creditors play a role as ultimate controller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during reorganization, the creditor derivative suit should be introduced, creditors should be give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terms of the seclection of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creditors′ control over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s right of disposition of property should be strengthen, the creditors′ right of deciding on the body of company management should be explicit, and creditors should be given interim supervision of debtors in the pattern of self- management.
Key words:during reorganization;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ontrol right of creditors;creditor derivative s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