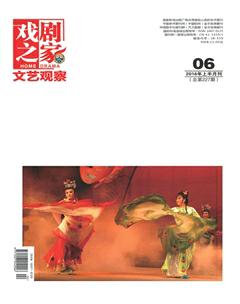中國(guó)戲劇評(píng)論“死水微瀾”現(xiàn)象之我見(jiàn)
【摘 要】當(dāng)下,整個(gè)社會(huì)都在發(fā)出一種共同的聲音,那就是對(duì)于整個(gè)戲劇行業(yè)而言,戲劇評(píng)論呈現(xiàn)出的一種“墮落”的狀態(tài)。經(jīng)過(guò)筆者的研究,認(rèn)為這是一種“死水微瀾”現(xiàn)象。筆者通過(guò)在2016年四川省戲劇評(píng)論人才培訓(xùn)班上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探討,結(jié)合國(guó)內(nèi)一流專(zhuān)家的授課,通過(guò)思想和學(xué)術(shù)的交流與碰撞,針對(duì)中國(guó)戲劇評(píng)論界“死水微瀾”現(xiàn)象對(duì)其進(jìn)行了探討,并對(duì)當(dāng)下的整個(gè)文藝評(píng)論氣氛以及學(xué)術(shù)態(tài)度進(jìn)行多維視角的評(píng)析。如有不妥之處,還請(qǐng)各位界內(nèi)前輩指正。
【關(guān)鍵詞】戲劇評(píng)論;藝術(shù)審美;死水微瀾;自我實(shí)現(xiàn);意識(shí)形態(tài)
中圖分類(lèi)號(hào):J805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7-0125(2016)06-0015-03
一、中國(guó)戲劇評(píng)論“死水微瀾”現(xiàn)象述評(píng)
在2016年四川省戲劇評(píng)論人才培訓(xùn)班上,不管是從開(kāi)班儀式上,還是在國(guó)內(nèi)專(zhuān)家授課的整個(gè)過(guò)程中,都在呼喚一個(gè)堅(jiān)硬的聲音,此聲音具有極強(qiáng)的穿透力度,這樣的力度著力展現(xiàn)于一個(gè)時(shí)代的發(fā)展,對(duì)于文化和一個(gè)意識(shí)形態(tài)所構(gòu)建出來(lái)的奮斗目標(biāo)。就整個(gè)培訓(xùn)班的授課而言,都有一個(gè)聲音在對(duì)外進(jìn)行呼喚,我們的戲劇批評(píng)需要重新去審視,需要站在一個(gè)更高的藝術(shù)水平的高度去衡量對(duì)于事物和現(xiàn)象的觀點(diǎn),需要在對(duì)作品內(nèi)容本身的理解上豐富其思想認(rèn)識(shí),用更加嚴(yán)謹(jǐn)?shù)目茖W(xué)態(tài)度去看待我們?cè)u(píng)論家對(duì)藝術(shù),對(duì)美學(xué),對(duì)人民,對(duì)歷史的標(biāo)準(zhǔn)的看法。因此,筆者在整合所有觀點(diǎn)后總結(jié)出了一個(gè)現(xiàn)象的到來(lái),即中國(guó)戲劇評(píng)論“死水微瀾”現(xiàn)象,并對(duì)此現(xiàn)象進(jìn)行解讀和分析。
《死水微瀾》是一部小說(shuō)作品,其內(nèi)容反映出的是四川成都以及周邊的小鎮(zhèn),鄉(xiāng)村的風(fēng)土人情、以及處于世界動(dòng)蕩、朝代顛覆更替時(shí)期中人們?nèi)缢浪话愕木駹顟B(tài)。筆者在本科階段主修的第一專(zhuān)業(yè)是音樂(lè)治療,輔修音樂(lè)新聞與評(píng)論專(zhuān)業(yè),回歸到筆者的專(zhuān)業(yè)學(xué)習(xí)中及性能解讀“死水微瀾”,心理學(xué)角度上我們將其定義為如何構(gòu)建自身價(jià)值觀,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一種意識(shí)狀態(tài),“我”對(duì)我自己身處于環(huán)境中的一種理解,“我”是否足夠有力量進(jìn)行自我實(shí)現(xiàn),縱使在萬(wàn)千世界的困苦環(huán)境的變化下,我依然是我自己,我依然保持我自己的鮮活的、充滿思想的生活狀態(tài),這是一種生活理念,也是意識(shí)形態(tài)中的一種核心概念。
前文已經(jīng)提到,“死水微瀾”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人們?nèi)缢浪话愕木駹顟B(tài),沒(méi)有思想,沒(méi)有見(jiàn)解,正如《紅樓夢(mèng)》中賈政的失語(yǔ)狀態(tài),無(wú)奈得如困獸一般地掙扎在時(shí)代的變遷和發(fā)展中。就筆者輔修的專(zhuān)業(yè)而言,這是一個(gè)偶然,接觸到新聞與評(píng)論專(zhuān)業(yè)的時(shí)候是因?yàn)楣P者酷愛(ài)著名音樂(lè)家高為杰教授所創(chuàng)作的《蜀宮夜宴》,因此對(duì)此作品創(chuàng)作了系列的分析和評(píng)論,于是我跨進(jìn)了新聞與評(píng)論專(zhuān)業(yè)。對(duì)于新聞學(xué)視域來(lái)說(shuō),這里有一個(gè)十分重要的概念如同和心理學(xué)思維所呈現(xiàn)的維度是一樣的,新聞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我們看到的世界的事實(shí)并非事實(shí)”這種觀點(diǎn),新聞學(xué)中筆者的導(dǎo)師就提出過(guò)當(dāng)下人民大眾的一種思潮即“死水微瀾”,對(duì)此,筆者進(jìn)行深思。
就《死水微瀾》作品本身而言,講的是在清朝將亡時(shí)期,腐朽的年代,人民的生活狀態(tài)如死水一般,只有淡淡的波瀾。的確,我們立即進(jìn)行心理學(xué)視域的解讀,首先,人民的生活如死水一般,那就是狀態(tài)都已經(jīng)失去了,精神已經(jīng)死去了,是否呈現(xiàn)出思想已經(jīng)消亡了呢?是否呈現(xiàn)出我們的思考能力已經(jīng)喪失了呢?是否呈現(xiàn)出我們對(duì)于文化研究的能力已經(jīng)弱化了呢?對(duì)于精神而言,在心理學(xué)學(xué)派中,心理學(xué)家們進(jìn)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正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中的結(jié)構(gòu)觀點(diǎn),即弗洛伊德的人格結(jié)構(gòu)理論,弗洛伊德把人格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gè)部分,如同戲劇一樣,我們?cè)谄浔疚业氖澜缋飳ふ姨幱诨煦鐮顟B(tài)的沸騰和激情。與符號(hào)學(xué)解釋一樣,正如四川大學(xué)趙毅衡教授在符號(hào)學(xué)中觀點(diǎn),認(rèn)為結(jié)構(gòu)主義的中心觀念其實(shí)不是結(jié)構(gòu)(structure)而是系統(tǒng)(system),結(jié)構(gòu)是相對(duì)于零星、散亂而言的,而系統(tǒng)是相對(duì)于孤立、片斷而言的。結(jié)構(gòu)觀念自古有之,亞理斯多德分析悲劇,找出六個(gè)因素,再分析這六個(gè)因素各自的功能,李漁講“密針線"的戲劇結(jié)構(gòu),這些都是結(jié)構(gòu)分析,但不是結(jié)構(gòu)主義,因?yàn)槠渲袩o(wú)系統(tǒng)關(guān)系的討論。
本我概念中通過(guò)戲劇形態(tài)放大到舞臺(tái)上展現(xiàn)出的一種狀態(tài),要求我們?nèi)タ吹阶晕遥吹饺说膬?nèi)心活動(dòng)的表達(dá)。人反映在社會(huì)中有一定的良心和道德力量,它不僅是藝術(shù)領(lǐng)域中的文化思潮,更是人類(lèi)文明的一部分,是人格中最高層次的體現(xiàn),是一種超我的狀態(tài)。但是,縱觀中國(guó)戲劇批評(píng),我們大量地喪失了批評(píng)家應(yīng)有的責(zé)任與良心,是否我們應(yīng)該從戲劇治療學(xué)觀點(diǎn)進(jìn)行深思?
同樣地,回到本文主題思維中進(jìn)行分析和探討,就標(biāo)題而言,誕生緣由是廣大人民的呼聲,對(duì)其戲劇批評(píng)需要一種良性的拯救,原因很簡(jiǎn)單,通過(guò)分析和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當(dāng)下中國(guó)戲劇批評(píng)存在的幾點(diǎn)現(xiàn)象可以歸納為:
(一)評(píng)論者寫(xiě)作的專(zhuān)業(yè)性匱乏,評(píng)論者文化基本功不夠扎實(shí);
(二)評(píng)論者根本是個(gè)門(mén)外漢,對(duì)評(píng)論寫(xiě)作本身而言,或其概念中根本不知什么是藝術(shù)評(píng)論;
(三)評(píng)論者的寫(xiě)作功利性太強(qiáng),對(duì)其作品呈現(xiàn)出自己的目的性展現(xiàn)。
筆者從事的是專(zhuān)門(mén)對(duì)評(píng)論和人性解讀的工作,就學(xué)術(shù)態(tài)度而言,必須嚴(yán)格地來(lái)進(jìn)行評(píng)判其寫(xiě)作的水平和寫(xiě)作的內(nèi)容。因此,對(duì)當(dāng)下的戲劇批評(píng)作品我用“死水微瀾”來(lái)進(jìn)行評(píng)判,很大程度上來(lái)講,這就是一種無(wú)知的賣(mài)弄。學(xué)術(shù)的境界在于不惜生命代價(jià)去進(jìn)行捍衛(wèi),一如既往地堅(jiān)持這樣的觀點(diǎn),嚴(yán)謹(jǐn)踏實(shí)地去工作和寫(xiě)作實(shí)踐。往往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就被一種惰性思維“然而并沒(méi)有什么卵用”的思維進(jìn)行相互的傳播和思考,事實(shí)上,確實(shí)如此,如果任何事情都沒(méi)有什么卵用了,你還工作干嘛?你還考大學(xué)干嘛?你還活著干嘛?這難道不是一種“死水微瀾”現(xiàn)象么?
二、戲劇治療:戲劇評(píng)論“死水微瀾”現(xiàn)象的解救良方
戲劇治療是筆者提出針對(duì)于當(dāng)下評(píng)論現(xiàn)狀出現(xiàn)的問(wèn)題提出的一種治療方案,即用心理學(xué)模式的戲劇治療來(lái)拯救戲劇批評(píng)的“死水微瀾”現(xiàn)象,筆者首先列舉當(dāng)下相對(duì)權(quán)威的幾大心理學(xué)派的整理研究,就心理學(xué)角度而言,縱觀整個(gè)學(xué)派,其心理學(xué)闡釋的是一種對(duì)研究人類(lèi)的整個(gè)心理現(xiàn)象、精神狀態(tài)的功能和行為動(dòng)機(jī)運(yùn)行的科學(xué),筆者這里提到的是科學(xué),在很大程度上,它具有強(qiáng)有力的科學(xué)性和嚴(yán)謹(jǐn)性,科學(xué)需要在不斷地進(jìn)行臨床治療研究數(shù)據(jù)分類(lèi)和分析統(tǒng)計(jì)中誕生的結(jié)果,有成功有失敗,同時(shí)它也是一門(mén)應(yīng)用學(xué)科,包括兩大領(lǐng)域,一是基礎(chǔ)心理學(xué);二是應(yīng)用心理學(xué)。基礎(chǔ)學(xué)派是處于淺層狀態(tài)的心理現(xiàn)象,而應(yīng)用學(xué)派如戲劇治療,呼喚人性的良性治愈,增加求治者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提升和建立自我概念的認(rèn)識(shí)。回到心理學(xué)本身,其涉及的研究包括在知覺(jué)、認(rèn)知、情緒、人格、行為、人際關(guān)系、社會(huì)關(guān)系等許多領(lǐng)域,也與日常生活的許多領(lǐng)域——家庭、教育、健康、社會(huì)等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恰恰是這些關(guān)聯(lián),反映出了戲劇人生的百態(tài),例如話劇《雷雨》中周繁漪的人物形象,就戲劇治療觀點(diǎn)來(lái)說(shuō),她呈現(xiàn)出的喝藥狀態(tài)便是一種病態(tài)的展示,心理學(xué)和戲劇有一個(gè)共性,體現(xiàn)在他們工作的對(duì)象和展現(xiàn)的對(duì)象是人,人是立體的、豐富的、多面的、鮮活的、有思想的。“喝藥”,是本質(zhì)上的藥嗎?沒(méi)錯(cuò)是藥,戲劇治療配方的藥物,源自于精神分析學(xué)派中的潛意識(shí)的剖析,源自于對(d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自我認(rèn)知,源自于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和對(duì)自己的救贖。正是這一神奇的現(xiàn)象,一方面我們?cè)诓粩嗟嘏L試用大腦的運(yùn)作和潛意識(shí)存在的這個(gè)動(dòng)機(jī)展現(xiàn)其基本的行為與心理機(jī)能的控制,顯然地,心理學(xué)也嘗試解釋個(gè)體心理機(jī)能在社會(huì)行為與社會(huì)動(dòng)力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筆者通過(guò)長(zhǎng)期研究認(rèn)為,這一角色動(dòng)力,和角色戲劇的沖突,就是整個(gè)當(dāng)今現(xiàn)狀的呈現(xiàn)和對(duì)現(xiàn)今社會(huì)形態(tài)的解讀。同樣地,它也與神經(jīng)科學(xué)、醫(yī)學(xué)、生物學(xué)等科學(xué)有關(guān),因?yàn)檫@些科學(xué)所探討的生理作用會(huì)影響個(gè)體的心智。戲劇也一樣,戲劇展現(xiàn)的是一個(gè)立體的人,我們看到的人,是一種多位的角色的夸張和放大,甚至可以通過(guò)舞臺(tái)上兩大演員反觀自己。因此,筆者認(rèn)為,戲劇家和戲劇評(píng)論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名心理學(xué)家,深刻地洞察了事物的本質(zhì)后,以一種正面的形式對(duì)戲劇進(jìn)行描述、解釋、預(yù)測(cè)和影響,有時(shí)候還要矯正行為和思想。
三、從“死水微瀾”到“心靈的會(huì)見(jiàn)”
筆者評(píng)論當(dāng)下戲劇批評(píng)的狀態(tài)為“死水微瀾”想象,其靈感源自于此次培訓(xùn)班上廖全京教授對(duì)戲劇評(píng)論的呼吁。在聽(tīng)取廖老師的課之前,筆者在文獻(xiàn)綜述的分類(lèi)和整理中發(fā)現(xiàn),如《多重文化結(jié)構(gòu)與中國(guó)戲曲的形成本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融合》中,廖老師的寫(xiě)作視域從多重文化進(jìn)行解讀,從交叉性的概念上來(lái)談中國(guó)戲曲以及西域文化的整個(gè)趨勢(shì),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視域的能力;《改編審美再創(chuàng)者的自我與自由徐棻版川劇塵埃落定的啟示》中,廖全京教授通過(guò)以心理學(xué)的自我和自由的作品作為一種模式,分別闡述了一個(gè)道理,藝術(shù)作品是一個(gè)摹本,以摹本的摹本再進(jìn)行構(gòu)建解讀的摹本化的摹本才是一種內(nèi)涵的體現(xiàn)。審美和創(chuàng)造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活動(dòng),滿足了一種心理學(xué)動(dòng)機(jī)的情緒體驗(yàn),因此,以直觀感受進(jìn)行創(chuàng)作也是一種技術(shù)手段的創(chuàng)新,是一類(lèi)思想理念,因?yàn)榫驮u(píng)論角度而言,筆者認(rèn)為,在學(xué)術(shù)科研領(lǐng)域,也非常具有創(chuàng)新價(jià)值和現(xiàn)實(shí)意義,它集中體現(xiàn)在以戲劇人物形象作為一種符號(hào)為其單元并完全依賴(lài)于系統(tǒng)才有意義,這在符號(hào)中最為明顯,如音樂(lè)學(xué)理論,戲劇表演體系、電報(bào)和計(jì)算機(jī),用最簡(jiǎn)單的符號(hào)單元(點(diǎn)與劃,開(kāi)與關(guān))組成了龐大的系統(tǒng),存儲(chǔ)傳送難以想象的巨量信息。戲劇則是以身體作為最強(qiáng)有力的信息產(chǎn)量所構(gòu)成的這一概念化的闡釋?zhuān)魏我饬x的傳達(dá)必須使用以某種方式被接收者感知的符號(hào)。同樣,這樣的符號(hào)以文學(xué)理念作為文本中傳遞出的物質(zhì)與精神財(cái)富是一致的概念,具有人性的精神思考,而非“死水微瀾”的狀態(tài)。正如趙毅衡教授在符號(hào)學(xué)觀點(diǎn)研究中闡釋的那樣,“不用符號(hào)而傳送一個(gè)意義是不可能的,意義本身就是從符號(hào)組成的信息中產(chǎn)生的。”同樣地,這個(gè)觀點(diǎn)對(duì)戲劇形態(tài)的認(rèn)識(shí)起到相關(guān)作用,這點(diǎn)不難理解。我們往往忽略的是我們所做的許多事看起來(lái)是實(shí)用的,無(wú)符號(hào)意義的,實(shí)際上卻常常是用符號(hào)傳出一個(gè)信息。這個(gè)觀點(diǎn),也就是筆者提出的對(duì)“死水微瀾”現(xiàn)象的一種最有力的解釋。同時(shí)也是對(duì)當(dāng)下人們對(duì)事物的一種“然并卵”狀態(tài)的批判。《文學(xué)何以失血對(duì)于一種文學(xué)現(xiàn)象的思考》一文中,廖老師從文學(xué)角度出發(fā),文學(xué)是一個(gè)學(xué)科領(lǐng)域在整個(gè)學(xué)術(shù)界而言,對(duì)于這樣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的思考充分反映出了一種對(duì)待問(wèn)題意識(shí)的體現(xiàn)。綜合以上幾篇現(xiàn)有的文獻(xiàn)中,筆者就領(lǐng)悟到一個(gè)特點(diǎn),那就是學(xué)術(shù)研究需要第一感覺(jué),感覺(ju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決問(wèn)題的一把鑰匙,那么這把鑰匙,其實(shí)就取決于對(duì)心理動(dòng)機(jī)的一種欲望,從而轉(zhuǎn)變成你對(duì)藝術(shù)的理解,你對(duì)戲劇場(chǎng)景中的畫(huà)面感呈現(xiàn)的理解,你對(duì)事物觀點(diǎn)的一種思考,你對(duì)戲如人生的態(tài)度。
四、廖全京“獨(dú)立自由的人文精神決定戲劇評(píng)論的高度”
獨(dú)立自由的人文精神決定戲劇評(píng)論的高度,從這個(gè)詞匯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人文精神則是反映心理學(xué)派的相關(guān)的論述,如人們對(duì)精神分析理論的述評(píng),精神分析理論以一種全新的理解來(lái)解釋許多疾病的形成原因,同樣地我們以符號(hào)替換的思維轉(zhuǎn)述到戲劇評(píng)論的角度而言,我看到的一些事物和狀態(tài)往往最直接啟發(fā)于我們對(duì)人性靈魂的思考,這與精神分析理論學(xué)派中的一些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創(chuàng)新意義。人類(lèi)意識(shí)層次的努力,是無(wú)法解決某些問(wèn)題的,正如本文主題提到的中國(guó)戲劇評(píng)論“死水微瀾”現(xiàn)象一樣,或者說(shuō),一些心理問(wèn)題的發(fā)生過(guò)程中,未必是意識(shí)層面的原因造成的,這時(shí)候,就需要我們對(duì)其進(jìn)行精神分析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通過(guò)精神學(xué)進(jìn)行工作意識(shí)突破了人類(lèi)長(zhǎng)期以來(lái)形成的因果邏輯的思想方法,以一個(gè)“潛意識(shí)”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來(lái)闡釋我們的心理問(wèn)題發(fā)生的原因,如同戲劇中的各個(gè)任務(wù)角色所反映出的對(duì)人性的思考。
回到標(biāo)題而言,這是廖全京老師在本次培訓(xùn)班上的小題目,他綜合了付文芯博士在對(duì)待小人物的心理的刻畫(huà),到李祥林教授多元文史哲打通的文化觀點(diǎn)以及《四川戲劇》李遠(yuǎn)強(qiáng)主編提出在戲劇批評(píng)中對(duì)精神分析學(xué)派的理解和精準(zhǔn)的運(yùn)用進(jìn)行了相關(guān)的闡釋?zhuān)畜w現(xiàn)了文藝批評(píng)的心靈會(huì)見(jiàn)。在講授的過(guò)程中,廖老師以《海鷗》為例進(jìn)行以心理學(xué)角度分析,用雙重結(jié)構(gòu)來(lái)分析尼娜作為戲劇人物角色的愛(ài)情,從最直接的表面狀態(tài)來(lái)看,這是一場(chǎng)表面的愛(ài)情的生死,更深刻地表現(xiàn)了這是一場(chǎng)不幸地對(duì)藝術(shù)的追求和對(duì)藝術(shù)的愛(ài)。
同樣地,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音樂(lè)治療專(zhuān)業(yè)教師劉書(shū)君老師也曾經(jīng)提出,心理學(xué)狀態(tài)反映的人文精神和思想意識(shí)形態(tài)綜合地在戲劇中展現(xiàn)出來(lái),人生如戲。但是很大程度上這便會(huì)有一個(gè)前提,我們?cè)谶M(jìn)行藝術(shù)生產(chǎn)和藝術(shù)實(shí)踐的過(guò)程中,更加應(yīng)該關(guān)注我們自我的超越,即你通過(guò)一部戲劇作品超越你自己,超越是心理學(xué)中的一種超越自我的一種狀態(tài),的確如此,我們?cè)趧?chuàng)作作品和文藝評(píng)論寫(xiě)作的過(guò)程中,更多的時(shí)候我們要超越作者的狀態(tài),超越國(guó)家和整個(gè)民族的領(lǐng)域,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來(lái)進(jìn)行對(duì)作品的評(píng)析和對(duì)自己的意見(jiàn)的獨(dú)特解讀。在更大程度上,筆者認(rèn)為,戲劇批評(píng)其實(shí)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評(píng)論者必須要有自己的個(gè)人魅力和鮮明的個(gè)性。俗話說(shuō)“玩的就是任性,你敢嗨嗎?”再如,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新聞評(píng)論專(zhuān)業(yè)教師李波老師的觀點(diǎn),就新聞理念而言,你看到事實(shí)非事實(shí),我們要樹(shù)立一個(gè)問(wèn)題意識(shí)形態(tài),即我們?cè)趯?duì)所有的新聞的解讀、新聞信息和現(xiàn)象的分析觀察中要有自己的洞察能力,即真相是什么?筆者認(rèn)為,這個(gè)思維點(diǎn)不僅對(duì)于一個(gè)新聞事業(yè)工作者而言非常重要,對(duì)于一個(gè)專(zhuān)業(yè)文藝評(píng)論者、戲劇批評(píng)者更為重要,如果評(píng)論者都無(wú)法完成自我實(shí)現(xiàn)以及在對(duì)事物意識(shí)的認(rèn)識(shí)中無(wú)法堅(jiān)持自己的態(tài)度,那么中國(guó)戲劇評(píng)論不就真的“死水微瀾”了嗎?
五、總結(jié)
筆者認(rèn)為,就戲劇批評(píng)和戲劇創(chuàng)作本身的整個(gè)過(guò)程來(lái)看,正如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藝術(shù)概論教師胡茵老師的觀點(diǎn),“藝術(shù)家在生產(chǎn)一件作品,通過(guò)藝術(shù)創(chuàng)作到藝術(shù)接受又發(fā)展為藝術(shù)傳達(dá)的這一歷程來(lái)表現(xiàn)對(duì)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涵的挖掘和解讀其內(nèi)涵的思考,人生的岔路口二者相遇非常不易,對(duì)于戲劇和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對(duì)于人性的思考的關(guān)系,如果我們不能以包容面對(duì)彼此,那么藝術(shù)的未來(lái)如何用心靈對(duì)話”確實(shí)如此,如果我們的戲劇行業(yè)在創(chuàng)作產(chǎn)業(yè)中能夠仔細(xì)去研究市場(chǎng),分析市場(chǎng)客戶(觀眾、來(lái)訪者)的需要,為其滿足精神需求,在藝術(shù)傳達(dá)中將藝術(shù)接受的轟炸性達(dá)到一定的爆點(diǎn),我相信,戲劇事業(yè)的市場(chǎng)將會(huì)如韓劇一樣的火爆,而戲劇評(píng)論界的“死水微瀾”現(xiàn)象,也將被根治。
參考文獻(xiàn):
[1]趙毅衡.文學(xué)符號(hào)學(xué)[M].北京: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0.1.
[2]趙毅衡.文學(xué)符號(hào)學(xué)[M].北京: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0.4.
[3]孫學(xué)禮.高等醫(yī)學(xué)院校教材[M].四川: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03.329.
作者簡(jiǎn)介:
趙立新,男,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中國(guó)青年文藝學(xué)會(huì)會(huì)員,樂(lè)山市音樂(lè)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藝術(shù)文學(xué)聯(lián)合社社長(zhǎng),四川音樂(lè)學(xué)院讀者協(xié)會(huì)閱讀部部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