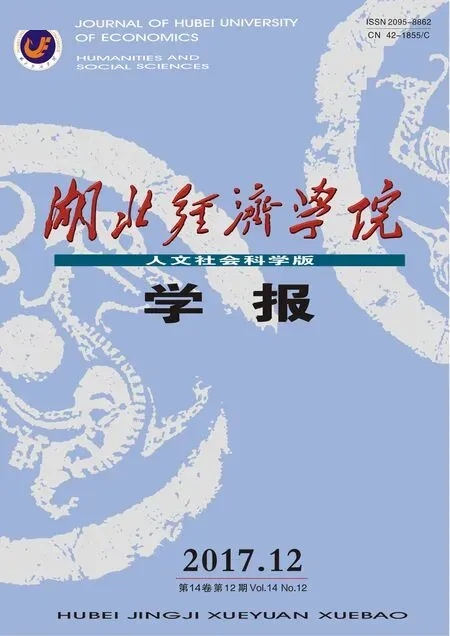從譯者的適應選擇看“譯者中心”
——基于《易經》兩英譯本對比分析
(廣東培正學院,廣東 廣州 510830)
從譯者的適應選擇看“譯者中心”
——基于《易經》兩英譯本對比分析
王云坤
(廣東培正學院,廣東 廣州 510830)
基于翻譯適應選擇論,在整個翻譯過程之中,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做出適當的選擇,將適應與選擇集于一身,完成翻譯活動。因此,本文將理雅各(James Legge)和汪榕培的《易經》英譯本進行對比,從譯者對需要、能力和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選擇三個方面進行分析,發現譯品之所以產生差異是由于不同的譯者為適應不同的翻譯生態環境進行不同的選擇,譯者位于整個翻譯過程中的中心。
適應;選擇;譯者中心;《易經》英譯
一、從譯者的適應選擇看“譯者中心”
翻譯適應選擇論認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1]譯者集適應與選擇一身,二者不可分割,適應中有選擇,選擇中有適應。選擇是一種主動行為,而適應往往被認為是一種被動地接受。但是在翻譯活動中,譯者并不是單純被動地“適應”,而是選擇性適應,以完成翻譯作品,使其能夠“適者生存”。而“選擇”也不是毫無章法可言,是適應性選擇,并受到“譯者責任”[2]的制約,從人的視角去審視文本,并實現文本的最終優化。胡庚申認為,適應和選擇都是譯者的本能[1],是譯者為了保證譯作的質量,對于譯文以及翻譯生態環境做出的下意識的、自然的判斷,從而體現了譯者在原文和譯文轉換過程中的中心作用。
同一部作品,譯者不同,譯文也各不相同,可能針對不同的讀者群體,可能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時代,可能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但是究其根本,都是由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適應”和“選擇”的不同表現所致。因此,本文重點把握譯者對需要、能力和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選擇的三個方面內容,對比分析理雅各(James Legge)、汪榕培在《易經》英譯過程中的適應與選擇,探討譯者的適應與選擇和譯品差異之間的關系。
二、譯者對“需要”的適應/選擇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曾提出需要層次,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的自我實現的需要[3]。需要也可分為內部需要和外部需要,譯者從自身的需要出發從事翻譯活動就是適應了其內部需要。而譯者作為社會成員,自我實現就體現在譯者能夠滿足社會的需要。
理雅各被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所吸引,曾對此作出極高評價:“他們的文明和我們的確有所不同,但卻絕對不是野蠻文明…中國和其四億子孫仍然在那里,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人們之中存在著某些道德和社會規范。”[4]而以《易經》為首的四書五經等中國經典就是最好的規范。同時,理雅各作為一名傳教士,其職責是在中國傳教,向中國人民解釋基督教義。理雅各鉆研中國典籍,研究如何將基督教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使民眾更容易理解,如何向本國傳教士介紹中華文化,消除誤解,更好地傳教。因此為了滿足理雅各了解中國文化內涵和完成傳教工作的內部需要,為了打破西方世界對于中國和中華文化的誤解,理雅各選擇了翻譯整部《易經》,包括解釋,并且還補充了他自己在翻譯中的心得體會,解釋了他之所以如此翻譯的原因。
自從1626年第一本《易經》拉丁譯本出版至新中國成立,令人遺憾的是沒有一個譯本是由中國人翻譯。其次,《易經》歷史悠久,版本眾多,眾說紛紜,一些問題懸而未決,影響了其理解與翻譯。而近年來考古學家對于甲骨文的深入研究,使這些問題有了新的的突破口,重譯《易經》在所難免。此外,《易經》中的許多生活智慧,如陰陽平衡,隨遇而安等,這些都和汪榕培先生的生活哲理不謀而合,因而他能夠更好地理解其精髓,表達原作的意圖。
由此可以得出,不同的譯作是不同時代的產物,不同的時代也賦予了其不同的歷史使命。譯者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做出最佳的選擇。汪榕培和理雅各選擇的原文并非完全相同,理雅各翻譯了整本《易經》,包括其經和傳,希望能夠呈現出《易經》和中國文化的原貌,幫助西方讀者理解和更好地傳教,而汪榕培則只翻譯了《易經》的核心與精髓。
三、譯者對“能力”的適應/選擇
胡庚申認為,“從譯者對‘內’的適應的角度來看,為了提高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的目的,譯者總是在可能的情況下,(以消極的方面來說)盡量不譯那些自己無把握的,或把握不大的作品;(從積極的方面來說)盡量選擇那些與自己的能力相適應、想匹配的作品去翻譯。”[1]傅雷先生曾說,“譯事…要以藝術修養為根本,無相當之社會經驗,無充分之常識,(即所為雜學),勢難徹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領悟。”[5]《易經》這部儒家經典歷史久遠,涉及語內和語際兩次轉換,要求譯者具有極強的雙語能力,此外,國內外易學界對其的研究和詮釋至今還有諸多分歧和爭議,這需要譯者在中西文化之間游刃有余,對《易經》有獨到的見解。
理雅各長時間在中國生活,漢語素養遠遠高于其他漢學家。海倫·理雅各在其對父親的傳記中曾寫到,理雅各曾說“對于儒家經典,我已經具有足以勝任將其翻譯成英文的中文學術水平,這是二十五年以上刻苦鉆研的結果。”[4]理雅各的治學態度也十分嚴謹。他在翻譯每一本典籍之前都要反復研究不同學派的觀點,認真做好記錄和注釋,仔細推敲,力求使譯文更加準確可靠[7]。理雅各在翻譯《易經》時就做了附錄,解釋自己的理解。同時,還有中國學者王韜的錦上添花,使理雅各對中國典籍的把握更為精確。
汪榕培從小熱愛文學,所讀之書貫穿古今中外。他是一名翻譯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名作家,用語言表達心中所想。從小培養的文學素養為其日后對典籍的理解和翻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外,他研究生畢業于復旦大學,專業知識也十分過硬,擁有了翻譯《易經》的雙語能力。
譯者根據其能力,包括譯者的風格,氣質,創造性等,選擇了所翻譯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通過對比可以發現,理雅各主要選擇異化策略,盡可能不去打擾作者,讓讀者向作者靠攏,使讀者更加接近原文。而汪榕培則選擇了歸化策略,以目標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幫助讀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譯文,將譯文的可讀性進一步提升。
四、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選擇
翻譯生態環境由原語文本,交際意圖,譯語文化等多個要素構成,且每個要素本身又有不同的維度和程度,而人們又不能滿足所有的維度,所以譯者主要從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維度進行適應性選擇轉換。
(一)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對整個翻譯生態環境熟悉之后,譯者首先應在語言形式上進行適應與選擇,實現原語和譯語的轉換。中國典籍十分講究遣詞造句,譯者在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可從選詞和風格兩個方面來探討。語言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詞義的發展變化更是如此,在詞語的本義的基礎之上,通過聯想,進行詞義引申。在《易經》的卦爻辭中,應選擇其本義還是引申義,譯者需要根據自己的理解做出合理的選擇。例如:
1.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大過·九二)[8]56
James Legge:the second line,undivided,shows a decayed willow producing shoots,or an old husband in possession of his young wife.There will be advantage in everyway.[6]127
汪榕培:a withered poplar tree sprouts;an elderly man marries a wife.Nothing stands in the way.[8]57
在這兩個版本中,選詞差異最大的是“女”字的翻譯與理解。從表面上來看,區別只在于是否強調“年輕”,在翻譯中,意義的增減也十分常見,其實則不然。實際上,這關系到譯者對于原義和引申義的選擇是否正確。“女”字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根據《漢英雙解新華詞典》,“女”的意思為“女子,女人,婦女”(women,female)[9], 包擴了所有年齡段的女性, 無論老幼。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詞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據《古漢語字典》,“女”的本義指未婚的年輕女子[10],在這里應取其本義。“女妻”,意為娶年輕的女子為妻,該卦爻辭用枯楊長出新芽,枯木又逢春來比喻老夫少妻,孕育著新的希望和生機,更為貼切且生動形象。理雅各選擇適應中國古漢語的用詞習慣,根據詞的本義來進行翻譯活動更為準確,而汪榕培則忽略了它在原文中的特殊含義。
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的時候,要深入研究原作,尤其是要從整體上把握原作的風格,包括其藝術風格,文體風格和語言風格等,從而從整體上把握譯文的整體基調。例如:
2.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蒙·上九)[8]8
James Legge:in the topmost line,undivided,we see one smitting the ignorant(youth).But no advantage will come from doing him an injury.Advantage would come from warding off injury from him.[6]31
汪榕培:In dealing with the ignorant,violent measures will only do harm,while proper measures will prevail.[8]9
《易經》時代久遠,用文言文所書寫,多傾向于書面語,和現代白話文的遣詞造句的習慣有所不同。在上例中,“擊”在理譯本和汪譯本中分別被譯為“smite”和“deal with”。根據《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smite”為詩/文用詞,意為“strike with a firm blow”[11],文學氣息濃厚。 而相比之下,“deal with”只是一個常用語,無法體現古文風格,以及其原文作者深厚的文學造詣。此外,還有《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之。”中的“三”被譯為“thrice”,《隨卦》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中的“系”被譯為“cleave to”,意為“黏住”,十分形象貼切。大量古詩文詞的運用增添了許多古色古香味,和原文風格更為相符。
(二)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更是一種跨文化活動,需要克服不同文化之間的障礙,實現雙語文化內涵的闡釋和傳遞。《易經》是中國儒家的經典之作,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下面主要從宗教,顏色和稱謂三個方面來解讀。
宗教文化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西方世界是由基督教支撐起來的話,中國就是由儒教,佛教和道教所支撐起來的。此外,它極為抽象事物,更難被他人所理解,所以,在有關宗教詞匯的選擇上,兩位譯者各有不同。例如:
1.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六二)[8]86
James Legge:Let the king,(having the virtues thus distinguished),employ them in presenting his offerings to God,and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6]187
汪榕培:The king is making offerings to the gods;This is a sign of good omen.[8]87
在上述例子中,兩個譯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帝”字的翻譯。理雅各將其翻譯為“God”,而汪榕培則把其意為“gods”。其差別遠非是否大寫和單復數。根據 《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God”的含義為“(基督教和其他神論宗教中)宇宙的創造者和統治者,精神權威之源;上帝”,而“gods”的含義為“被崇敬的人”[11]。
與此同時,理雅各在《易經》英譯本的前言中也強調,“三十幾年來,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我認為‘帝’,也就是中國人之父,所表達的含義和我們的上帝所表達的含義是相同的,因此我一直將其如此翻譯…我也非常高興地看到許多在中國的的傳教士用‘帝’或‘上帝’來代替‘God’。 ”[6]也就是說他認為所有人都是由上帝來領導的,基督教和儒教一脈相承。這并不是因為理雅各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不夠,而是因為宗教信仰很難改變,即使理解其他的宗教也并非一件易事,因而為了使西方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理雅各根據整個翻譯生態環境選擇了基督教詞匯。
顏色術語除了用來描繪大自然中的五彩繽紛,也可用來表達豐富的感情和文化內涵。
2.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上六)[8]1
James Legge:The sixth line,divided,(shows)dragons fighting in the wild.Their blood is purple and yellow.[6]21
汪榕培:When the dragon comes to fight in the wildness,blood runs black and yellow.[8]2
其最大的差異在于對顏色“玄黃”的把握。在《坤卦》上六中,陰氣太盛,陰極陽來,成為了“假陽”。“陽”象征“天”,也指龍,而“假陽”就象征“地”或“假龍”。當真假龍爭斗時受傷,流出青黃色的血。同時“青”象征“天”,“黃”象征“地”,其中也含有中國古代五行中相生相克的道理。但是,由于各個民族的文化不同,其語言中的顏色體系也不同,就可能產生文化空缺,因而沒有與中文的“青”這個顏色相對應的英語詞匯。所以,理雅各選擇適應中國文化,用“purple”這個藍色和紅色的混合體來象征“藍天”和“紅色的血液”的混合體。而汪榕培則是選擇了白色和“玄”相對,卻沒有體現出更多的文化內涵。
(三)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翻譯過程中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指的是“譯者除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換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1]《易經》的交際意圖可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層面,《易經》本就為占卜之書,為讀者提供信息占卜未來。第二層面是向讀者傳遞語言形式之美。第三層面是通過豐富的詞匯表達向讀者傳遞文化內涵和生活哲理。
兩個譯本基本上都實現了《易經》的第一層交際意圖,因為理雅各和汪榕培都翻譯了整本《易經》,包括64卦。此外,理雅各還增加了附錄,解釋他的翻譯過程幫助讀者理解。
在第二層面,從表達語言形式之美來說,理雅各的目標讀者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盡力適應原語的生態環境,重現語言規則和語言風格,即使詞句晦澀難懂。而汪榕培則不希望受到行文的束縛,盡可能地簡化《易經》中的詞句,因為他的目標讀者是普通讀者。
在第三層面,從傳遞語言的文化內涵來看,理雅各創造性地使用宗教詞匯來適應目標文化,根據原語文化來選擇適當的詞語翻譯顏色詞匯以體現其文化內涵。而從表達生活哲理來看,汪榕培選擇簡化句子直接向普通讀者講述生活哲理,而理雅各則向讀者呈現《易經》原貌,因為讀者受過良好教育,并且希望自己研究《易經》。
五、結論
譯者從內部和外部來適應需要,理雅各選擇翻譯完整的《易經》,并融入自己的觀點,而汪榕培則選擇翻譯其核心。同時,譯者為適應自己的能力選擇相應的翻譯策略,理雅各選擇異化策略而汪榕培則選擇了歸化策略,這都是譯者從宏觀上的選擇。而從微觀上來說,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維度都進行適應性選擇轉換。理雅各適應了原語的語言規則和語言風格,并盡力呈現原語的文化內涵,還對宗教詞匯進行了創造性處理,使目標讀者更容易接受,達到交際的目的。
因此,不同的譯者之所以會對同一原文創作出不同的譯本,究其原因,是由于譯者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之后,選擇了不同的原語文本和翻譯策略,從而導致譯文不盡相同,由此可見,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是翻譯的中心。
[1]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申.從“譯者中心”到“譯者責任”[J].中國翻譯,2014,(1):29-35.
[3]馬斯洛,著.林方,編.人的潛能和價值[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4]Legge,H.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
[5]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6]理雅各英譯,秦穎,秦穗校注,秦穎今譯.周易[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
[7]顧長聲.從司馬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汪榕培,任秀樺,譯.英譯易經[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9]姚乃強.漢英雙解新華字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10]《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M].北京:商務英語出版社,1998.
[11]《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編輯出版委員會.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詞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王云坤(1986-),女,河南安陽人,廣東培正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英語教育以及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