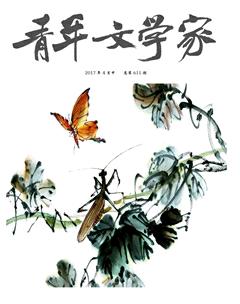斯托夫人筆下的白人女性形象解讀
史翠蘋+趙妍+佘婷
摘 要:美國作家哈利葉特·比切·斯托(斯托夫人)于1852年發表了一部反奴隸制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抨擊了奴隸制下人們的悲慘生活,其抗爭奴隸制的觀點引起了強烈反響,由此一舉成名,對當時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這部小說也奠定了斯托夫人的文學地位。除此之外,斯托夫人還寫過一篇虛構的維護女權主義的論文《我妻子和我》,文中對女性形象的刻畫飽滿豐盈而又性格各異,讓人感到真實而又為之動容。本文就由此出發,深入研究斯托夫人筆下的女性所具備的精神與力量。
關鍵詞:斯托夫人;女性形象;仁愛;抗爭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1--01
斯托夫人于1811年6月14日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當時黑人奴隸制還未被廢除,斯托夫人就處于這樣的一個時代,目睹著無數黑人的悲慘經歷。而廢奴制問題從19世紀2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許多作家都贊同廢奴制,斯托夫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員。《湯姆叔叔的小屋》引起當時社會的極大震動,隨后,為反駁保守勢力的攻擊,斯托夫人又在1852年發表《(湯姆叔叔的小屋)題解》,通過大量的法律文件與檔案等資料來證實小說中描述事件的真實性。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斯托夫人又寫了《德雷德,陰暗的大沼地的故事》(1856)《奧爾島上的明珠》(1862)《老鎮上的人們》(1869)《粉色和白色的暴政》(1871)等多部作品。而《棕櫚葉》則創作于斯托夫人的晚年時期,描繪了她在佛羅里達寧靜安逸的生活。斯托夫人生于美國奴隸制還沒被廢除的時期,受信仰加爾文教的牧師父親影響,堅決倡導廢奴隸制運動,再加上她親眼目睹了奴隸毫無尊嚴、于水深火熱之中苦苦掙扎的真實場景,更對奴隸制充滿憎惡,她用自己敏感而又強大的筆觸書寫出她對奴隸生活的同情與憐憫,抒發她對奴隸制度的憤慨與抨擊,希望能夠引起全社會對廢奴制的關注。為此,斯托夫人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對黑奴命運的刻畫,描寫了大量奴隸主對黑奴的殘酷與剝削情景,也有奴隸對待命運的不同態度。林肯曾評價斯托夫人是“寫了一部書,釀成一場大戰的小婦人”。當然,斯托夫人不僅僅是一名反奴制“戰士”,同樣為爭取女權,維護女權做出了突出貢獻。《我妻子和我》就是她專為維護女權地位而發表的論文,無論是文學地位,還是現實意義都非常重大。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飽滿而豐盈,立體而深刻,給人以震撼。筆者以此為中心,對斯托夫人刻畫的女性形象進行深入分析。
奴隸制下的生活悲慘而絕望,令人同情而又氣憤。斯托夫人不僅嚴厲抨擊著奴隸制度,也將美國社會中的一部分鮮為人知的弱勢群體展示出來——白人女性,他們雖然不是黑人,卻也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難逃命運的磨難,成為犧牲品。
其一,善良美麗的品質。雨果說過:“善良的心就是太陽”,莎士比亞也曾說,“善良的心地就是黃金”。可見,眾多仁人志士,文學巨匠對善良品質的向往。虔誠的斯托夫人同樣對善良、仁愛有著無比的熱愛。因而她筆下的女性中都會存在著這樣一個善良、高尚的形象,影響著周圍的人與事。但可惜的是,他們的這種善良并不能幫助他們改變現狀,也并不能使他們脫離苦海。就如她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刻畫的奴隸主太太謝爾貝,她溫柔嫻淑,善良美麗,她用自己的愛心感染著身邊的人,即便她是奴隸主太太,對待黑奴時也并沒有什么偏見,更多的卻是平等與自由的想法,她認同人生而平等,不應當對奴隸如此殘忍冷酷。得知丈夫要賣掉黑人時,她非常生氣與羞愧,但她并沒有什么說話、做決定的權利,只能默默忍受。在黑人奴隸的母親想要帶著黑人奴隸逃跑時,謝爾貝太太盡力給予幫助。由此可以看出,謝爾貝太太本性的善良品質,但也可以看出,她并不會表現出對丈夫的反對,而是一味地忍讓與順從,她在丈夫面前毫無地位,即便是她再同情黑人奴隸的生活,也難以改變丈夫的決定,難以改變奴隸的悲慘處境,更不會對黑人的解放有什么實質性推動作用。但至少,他讓當時社會中痛苦絕望的人看到了一絲光明,給他們帶去了一絲溫暖與希望。
其二,自私虛偽的面孔。黑人奴隸的悲慘生活源于社會偏見,源于制度壓迫、源于每一個奴隸主的謾罵與剝削。斯托夫人描繪中,有很多令人憎惡的白人女性。他們自私虛偽,貪得無厭,對黑人奴隸沒有絲毫的人情味。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有這樣一個人物形象,她就是農場主的女兒瑪麗,她秉承了奴隸主的冷酷與自私,十分嬌氣、野蠻,不僅對待奴隸刻薄,更沒有盡到一個母親應盡的責任。但是,她的女兒伊娃卻與之恰恰相反。伊娃富有愛心,渴望平等、自由的生活,在她眼里,沒有等級差異、沒有階級觀念,只有善良與天真,只有天使般的美好的心靈。在她的請求下,湯姆叔叔暫時擺脫了那段艱苦的日子,當上了車夫。這個小女孩用她的純真感染著周圍的每一個人,讓人們看到這黑暗的世上還有這樣無邪的笑容,像陽光普照大地般的給人溫暖。相比之下,瑪麗的自私與虛偽是如此的令人鄙夷,盡管她自己并不這么認為,事實上,她確實體會不到伊娃的快樂,也當然感受不到而仆人瑪咪的痛苦。其實,斯托夫人筆下的瑪麗,也諷刺了當時社會的絕望。盡管瑪麗享受著殷實的生活,但她并不幸福,她被孤獨與冷漠包圍,只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別人,發泄心中的不滿,這何嘗不是人性最悲哀的一面。
參考文獻:
[1]論《湯姆大伯的小屋》中的女性主體意識[J]. 周海燕,羅曉梅.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