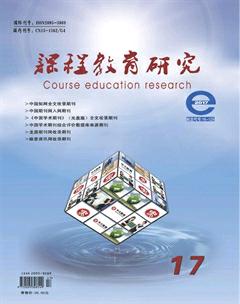從《活著》英譯本看意識形態對白睿文文學翻譯的操縱
王志敏 陳啟晗 周小春
【摘要】本文借助安德烈·勒菲弗爾的意識形態理論,討論意識形態對白睿文《活著》英譯本的影響。白睿文的文學翻譯觀深深烙著文化相對主義社會意識形態和他個人意識形態的印跡,體現了他對原作的尊重,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對翻譯工作的鄭重。
【關鍵詞】意識形態 文學翻譯 文化相對主義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17-0100-02
1.引言
翻譯和意識形態密不可分。一個譯本能否取得成功, 不完全取決于原文本在原文化里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看譯入語文化讀者對異域文化的接納程度如何。翻譯過程中,準確傳達原文本土文化特色的內容,并讓譯文讀者更好地接受和理解,成為一大難點。然而,經過對比不難發現不少譯文和原文存在很大的出入, 有的甚至面目全非。翻譯研究中的文化派認為,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操控著翻譯,對翻譯過程的方方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很難擺脫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其本身個人意識形態對其翻譯活動的影響制約,兩者通過譯者這一翻譯主體來產生最終的翻譯結果。
2.意識形態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翻譯研究出現重大范式變革,歐洲低地國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學者從文學接受和文化傳播的角度,以譯文描寫替代原文分析,將翻譯產生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進行系統考察,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翻譯觀和翻譯研究的模式。
在翻譯研究范式的轉變過程中,比利時裔美籍比較文學學者和翻譯理論家Andre Lefevere (1945-1996)提出,翻譯是一種改寫,翻譯文學作品要樹立何種形象,主要是由兩種因素決定,這兩種因素是譯者的意識形態(不管是譯者本身認同的還是贊助人強加給他的)和當時在譯語環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詩學觀。(Andrew Lefevere, 1992:41)從宏觀層面上,意識形態會影響翻譯的目的,翻譯題材,翻譯標準,翻譯策略;從微觀層面上會影響到具體詞語的翻譯。而在論及意識形態對翻譯的影響時,原文語言和“文化萬象”帶來的各種難題,譯者也會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依據自己的意識形態尋找解決辦法。根據勒菲維爾的這一理論,置白睿文于美國21世紀跨文化交際的語境中,來分析他的文學翻譯觀。
3.《活著》及其譯文
《活著》是余華20世紀90年代推出的力作,該作品的英文譯本由加洲大學芭芭拉分校東亞系副教授Michael Berry (白睿文)翻譯,于2003年8月由蘭登書屋(Random House)首次出版發行。
《活著》的作者余華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活著》就是講人承受生活的故事。作者在小說的序中有所提及:“……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這首歌深深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余華在《活著》中,只關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撐人的存在的所有支點,這些支點不只是頹廢的、無望的、帶著世紀末情調絕望的吶喊與顫栗,還擁有濃郁的人文關懷,閃耀著人類引以為豪的生命力。
在《活著》英譯文中,譯者白睿文在忠實體現原文作者初衷的基礎上折射出原作中的人文關懷。白睿文對《活著》的再現主要體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上他成功的再現了原作中的語言形式,即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情節,在文本結構上與原作保持一致(文字平實易懂,對白口語化,敘述手法傳統化),并在人物刻畫上與原作相契合。在微觀層面上,白睿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成功的傳譯了中國人的人生觀和生命哲學。而且對于文中特定的文化詞匯的翻譯,白睿文用了直譯加注的方法,沒有加上自己任何的主觀感情色彩。另外原文中的修辭手法,譬如明喻和重復在《活著》英譯本中也得到了忠實的再現。照勒菲弗爾的理論來看,白睿文的這些處理主要是由他所處的社會意識形態和他本身的意識形態兩個因素決定的。
4.意識形態對白睿文文學翻譯的影響
4.1 文化相對主義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懷著對種族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厭惡和對落后國家文化的理解與尊重,建立了“文化相對主義”,其中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茲·博厄斯認為,任何一個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邏輯、社會思想、世界觀和道德觀,人們不應該用自己的一套標準來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衡量文化沒有普遍絕對的評判標準。繼博厄斯之后,該理論的核心人物梅爾赫爾斯科維茨認為“文化相對主義的核心是尊重差別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種社會訓練,它強調多種生活方式的價值,這種強調以尋求理解與和諧共處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毀那些與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東西。”簡單點說就是承認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根據這一說法,跨文化交往的研究,就成了文化相對主義的重要內容。
二十一世紀,由于全球信息社會的來臨,各種文化體系的接觸日益頻繁,東西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跨文化交流的新世紀,美國人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異域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能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文化相對主義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推崇。而且,余華最終所達到的思考深度仍不過是宿命式的東方神秘主義,與西方宗教精神有所不同。但在表現人類共同生命體驗上還是非常到位的。因此余華的作品便具有了足夠的世界性,能吸引更多的西方讀者。
因此, 白睿文在翻譯時, 不但考慮了自身所處的時代、所屬的民族、階級的文化背景和作品受眾的需要, 還考慮了原作體現的文化、思想、風格和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 作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創作意圖, 以及譯文可能產生的藝術效果和社會作用等。
4.2 白睿文個人意識形態的影響
翻譯過程中的多數決定最終由譯者做出。譯者在整個過程中, 自始至終受到各種因素, 主要是譯語文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但這并不說明譯者在這個過程中是被動的。恰恰相反, 譯者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處于中心能動的地位,譯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對于他對文本處理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活著》的譯者白睿文出生于美國芝加哥,是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也是臺灣留美漢學家哈佛教授王德威的學生,現職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東亞系副教授。白睿文的翻譯策略是跨國界的,他的翻譯作品向西方讀者顯示了中國文化的豐富多樣。在翻譯作品的選擇上,白睿文主要基于自己的愛好:“我做翻譯純粹是出于愛好,一定要自己非常喜愛這部作品,才會把它介紹過來。” (吳赟,2014:48)
1996年,白睿文翻譯了著名作家余華的小說《活著》。中文國際報章星島日報評論白睿文先生不僅中文造詣極深,更難得的是他能準確地抓住并傳遞原作的精神。白睿文在2014年的一次訪談中談到了自己的翻譯主張:“身為譯者,我希望讀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風格。我希望我扮演是一個透明人的角色。通過我,原作可以在英語環境中開口說話,來表達原作的精神世界。” (吳赟,2014:49)
翻譯完成后,他聯系了十幾家出版社,都被拒絕。2002年左右,當年拒絕白睿文的世界最大英語商業圖書出版集團蘭登書屋的一位主編卻主動聯系他,想要出版《活著》的英譯本。出版社為了照顧到英美讀者的閱讀習慣,常常要求譯者對譯作進行一定的刪減和改動,舍棄作者某些文學特質,使作品更為美國化,而白睿文對這種要求選擇了說不:“那時編輯寄回給我的譯稿,滿版都是密密麻麻的改動,我覺得他改得有點過了,離原作的意思有點遠,于是我就把那些改動都還原,再寄給他;……我盡量不做太大的妥協。否則我覺得就失去了原作的精神……” (吳赟,2014:50)
由于翻譯經驗豐富,白睿文已經成為中西文化的使者,把中國的當代小說鮮活地引入西方世界:“中國當代文壇非常豐富多彩,有很多經典作品,很可惜的是那么多經典沒有翻譯到國外,沒有得到海外的認可……我有責任把這些作品介紹西方讀者。” (吳赟,2014:52)
以上對白睿文翻譯《活著》過程的追溯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譯者對原作處理的成因。白睿文的翻譯主張體現了他是個文化相對主義者,他不僅對原作尊重,對中國文化尊重,而且對翻譯工作極為鄭重,這些都能解釋他在譯文中對原作的把握。總而言之,在文化相對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白睿文文化相對主義的個人意識形態決定了其翻譯的行為和結果。
5.結語
白睿文的文學翻譯中,他對文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使用等方面體現了意識形態操控。在當今世界一體化和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國小說在美國開始有點吃香,但整體來說中美之間的文化失衡還是相當嚴重。白睿文力挽中英翻譯的意譯風尚,以直譯的方式向西方讀者輸入了原質的中國文化,有利于中國文化在西方社會的傳播和了解。同時,白睿文的文學翻譯觀也驗證了意識形態對翻譯行為的操控,是譯者與社會的相互交融產生出了這一翻譯成果。從意識形態角度探討翻譯活動,無疑是對翻譯研究的深化和擴充,使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走向了文化的大語境中。
參考文獻:
[1]Berry, Michael. To Live: A Novel [M]. New York: Anchor?鄄Random House, 2003.
[2]余華.活著(中文版前言)[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4.
作者簡介:
王志敏(1979-),女,漢族,湖北大悟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英漢翻譯與英語教學。
陳啟晗(1996.8-),女,漢族,北京人,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英漢翻譯。
周小春(1970.11-),女,漢族,江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漢翻譯與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