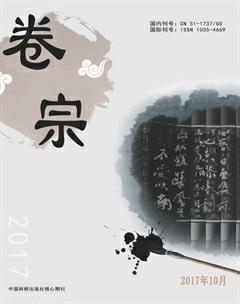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究
摘 要:政治儀式作為普遍存在于政治生活中的行為現象,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正是對人們思想進行教化,因此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通過儀式的舉行,可以創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豐富教育內容,擴增教育對象,整合教育資源等,從而保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而閱兵儀式作為政治儀式的重要代表,具有政治儀式的顯著特點,這為我們研究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突破口。
關鍵詞:政治儀式;閱兵;思想政治教育
閱兵儀式無疑是當前國內最受人關注的政治儀式,僅剛過去的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儀式中,就有超過80萬網友通過在線直播觀看盛況。而閱兵式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之聚焦效果,與其特有的儀式形式與內容是分不開的,如何利用好閱兵式使其產生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當前學界理應關注的焦點。因此本文試圖從儀式論的角度對以閱兵儀式為代表的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進行剖析。
1 政治儀式的理論解讀
1.1 政治儀式的概念
埃米爾·迪爾凱姆(?mile Durkheim)有關儀式的定義在早期社會科學領域最具影響力,他將儀式與宗教實踐聯系在一起,認為儀式將世界劃分為兩個階層:神圣階層和世俗階層。他聲稱儀式是“一些行動法則,規定一個人如何令自己的行動與神圣事物的表現保持一致。[1]”史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對儀式所作的定義更具經典意義,他指出“儀式”這個詞表示,“受規則支配的象征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2]”。
與上述普遍意義上的儀式相比,政治儀式有其獨特的屬性。從詞義上講政治儀式與儀式的區別在于前面“政治”二字的限定,這一定語揭示了政治儀式的本質屬性與功能。政治權力與秩序的維系不僅表現在對公民思想上的教化,更應該在具體的行動上面來表現。政治儀式的舉行無疑將這種維護政權合法性的行為具體化了,通過儀式的舉辦,可以喚醒和重構集體記憶,并增強受眾的認同感。
1.2 政治儀式的特征
首先,政治儀式具有規律性與周期性的。政治儀式通過其程式化、規模化和重復性的舉行,進一步強化其功能,使儀式的參與者通過遵守規則重復操演,達到教化的目的。歷次閱兵儀式在社會背景和意義上存在差異,相應儀式的程序也有所變化。
其次,政治儀式具有確定價值和意義。不同于其他類型的活動,人們在政治儀式中不能率性而為,其行動被賦予了確定的意義。參與儀式的人在儀式的全過程都有一種神圣感與責任感,并贊同和擁護儀式的意義和價值。
最后,雖然政治儀式的舉辦場所是固定的,但儀式的效用卻不僅限于舉辦儀式的場合,具有發散性的特點。
2 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2.1 營造思想政治教育情景
李輝在《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研究》中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景是如下定義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景是教育過程中的一種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內在的、主體的體驗、氣氛和人際互動[3]。身處于這種情景之中,受教育者可以全身心的浸染于教育之中,而教育者則可以利用情景制造出全方位立體式的效果,將教育內容更有效的傳達出去。與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比,政治儀式是有其獨特優勢的。政治儀式的舉行離不開相關宣傳報道,而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能夠滲透入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挖掘出其潛在的意義,這種不易察覺的教育方式顯然比傳統枯燥乏味的教育更能激發受教育者的興趣,從而被受教育者所接納,達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目標。在政治儀式所營造的教育情景中,儀式充分調動了受教育者的感知、情感和理智諸方面的能力,因而容易使參與者對教育內容產生共鳴,正是由于儀式的這種特性,使它能營造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景,成為歸化儀式參與者思想情操的重要途徑。
以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為例,莊嚴肅穆的閱兵儀式給觀眾營造出莊重的氛圍,使那些感受到這種情景和氛圍的觀眾如身臨其境般成為了這場政治儀式的參與者,特別增加的抗戰老兵乘坐禮賓車出場具有極強的感染力,成功把觀眾帶入到七十多年前的烽火中,喚起人們的政治記憶,成為人們難以忘記的畫面。正是在這神圣而莊嚴的氛圍中,營造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景,受教育者如同身臨其境般沉浸其中,從而得到思想上的升華,在不知不覺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
2.2 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
政治儀式盡管從外在來看是一個行為過程,但并不僅限于儀式活動,更擁有深刻的主題和豐富的內容,其自身就具有極高的價值和意義,深入挖掘和研究政治儀式,這有助于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不同于依靠語言文字進行教育的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政治儀式通過現場多種感官方面的刺激,將儀式的主題及意義傳達給受教育者,將儀式的價值賦予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從而豐富了教育的內容。
2.3 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
陳華洲在其《思想政治教育資源論》中對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概念進行了總結,他認為所謂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是指被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來的,有利于實現思想政治教育既定目標的各種因素的總和,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開發和利用的物質、文化和信息的總稱。[4]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包含物質資源與精神資源。物質資源主要指具有具體形態的,能夠展示在人們眼前的具有顯性特征的資源,比如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等建筑設施,以及現場的紅旗鮮花等標志,這些符號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質資源。而精神資源則是指儀式舉行過程中現場所烘托出的氛圍,流露出的情感,傳達出的思想觀念等無形之物,可以說是具有隱形特征的皆可歸為精神資源,這些資源能夠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的想法,從而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 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實現路徑
3.1 彰顯儀式主題的時代性
政治儀式要想取得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就必須把握時代內涵、突出時代特色。因此政治儀式在籌備期間就應該注意當前時代的特征,不能與時代脫節,在儀式舉辦過程中更要時刻注意輿論走向與群眾反饋,及時調整儀式的形式與內容,做到緊跟時代主題與潮流,只有這樣才能將政治儀式真正做到受眾的心里去,從而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果政治儀式過于程式化,因循守舊、裹足不前,不但起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使人們產生逆反心理,留下一個流于形式和表面工作的壞印象,不利于實現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endprint
閱兵儀式不同的歷史時期自然擔當起不同的歷史任務,比如新中國成立伊始,深受國際社會環境影響,我國舉行的閱兵儀式呈現出濃厚的對抗和震懾色彩,如開國大典上空中受閱部隊是掛載實彈通過天安門上空的,而抗美援朝時期舉行的閱兵式,受閱官兵在儀式結束后隨即開赴前線作戰,呈現出很強的戰爭動員意味。而八十年代后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主流,而我國也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閱兵儀式側重點也在變化,不再是單純地武器與士兵走過天安門廣場,更加突出激發人民堅持改革開放大力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熱情。
進入21世紀,閱兵儀式更有了跟隨時代步伐的創新,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儀式舉辦時間不再僅限于國慶節當天,紀念主題也不再僅限于國家成立的周年慶典,有了更多時代性的意義。如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紀念香港地區回歸20周年閱兵儀式等。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7月31日在朱日和戰術訓練基地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90周年閱兵儀式,首次在天安門廣場以外的地方舉行,并且形式上也與傳統廣場閱兵大不相同。根據現狀與國際國內環境來相應調整政治儀式的主題、內容與形式,保持時代性,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以政治儀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3.2 豐富媒介傳播的手段
媒介傳播以信息傳遞的高速化、傳播效率的高效化和影響范圍的擴大化為特征,它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新聞的深度報道或系列報道,對所發生的事件進行專業的歸納與整理,提取相關內容并傳遞出去,其所傳遞出去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大眾的思想具有引領作用。因此我們要積極利多種媒介手段來擴大政治儀式的傳播力度和影響力,在儀式舉行的過程中烘托出氛圍,引起廣大受眾的關注。因此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實現過程中,多種媒介方式相結合的宣傳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要注重各種傳播媒介之間的區別于聯系,做到全面協調,優勢互補,從而實現政治儀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政治儀式舉辦前,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宣傳籌劃過程、儀式內容、儀式的意義等為儀式的舉辦造勢,調動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儀式舉辦過程中,通過多種媒介方式將政治儀式所舉行的盛況傳播到民眾中間,擴大儀式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活動結束后繼續相關的報道、并形式多樣的活動來深化儀式的主題,從而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順利開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要重視視覺、聽覺多維度的信息傳遞,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與微博、公眾號等新媒體相結合來達到信息傳播的目的。
以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90周年閱兵式為例,這次儀式很好的做到了從紙質媒體到電視媒體和網絡媒體聯動,共青團中央選擇在國內青少年中擁有極高人氣和影響力的視頻網站嗶哩嗶哩(Bilibili)上網絡直播此次閱兵盛況,讓更多人通過網絡了解到此次儀式,直播間氣氛熱烈,很多人都被受閱官兵的精氣神所震撼,也使更多青少年了解建軍歷史和國家發展現狀,達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3.3 加強儀式主客體的互動
儀式的主體與客體的界限是分明的,主體是指儀式的組織者與舉辦者,而政治儀式的主體便是政府與國家,即使為個人舉辦的紀念性政治儀式的組織者同樣也是集體,因此也算在主體內。而客體則是指儀式的受眾,這里的受眾不僅指儀式的觀眾,同樣包括儀式的參與者,儀式的參與者通過身體上的操演,同樣在思想上受到了教化,可以說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當前我國閱兵式中,國家作為組織者是固定的,那么要想做加強主客體互動,只能從參與者方面入手。當前閱兵式參與主體方面正在朝著多元化發展,除了特定人群,國家領導人、受閱官兵、受邀嘉賓等,我們也能夠在花車巡游,廣場翻花翻字等找到普通民眾的身影,他們通過夜以繼日的訓練,已經將自己與儀式緊緊聯系在一起,從而達到情感上的共鳴。但不可否分的是,當前政治儀式的主客體之間互動還有缺乏,民眾的參與度整體來說并不高。因而,官方組織儀式的過程中應該想方設法用更加柔和的方式宣傳價值,選擇引導性的方式而非直接灌輸的方式傳輸價值。
注釋
[1]Dufkheim(1915:37,41)
[2]Steven Lukes, “Political Ritual and Intergration” , Sociology, 9(1975),pp.289-308, esp.p.291
[3]李 輝: 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研究[D]: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249
[4]陳華洲: 思想政治教育資源論[M]: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2007
參考文獻
[1]Steven Lukes, “Political Ritual and Intergration” , Sociology, 9(1975),pp.289-308, esp.p.291
[2]王海洲.合法性的爭奪:政治記憶的多重刻寫.[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27
[3]李輝: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249
[4]陳華洲:思想政治教育資源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2007
[5]中國廣播網2000中國共產黨大事記[EB/OL].http://www.cnr.cn/2007zt/sqd/ddzs/200710/t20071010_504590025.html
[6]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3
[7]馬敏:政治象征:作為權力技術和權力實踐的功能,[J]:探索與爭鳴2004(2)
[8]郭于華: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J]:讀書1999(9):16-18
[9]蔣建國.祭祀消費:儀式傳承與文化傳播——以晚清廣州為中心[J].廣東社會科學.2006(06)
作者簡介
王妍晴(1994-),女,漢,內蒙古巴彥淖爾人,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