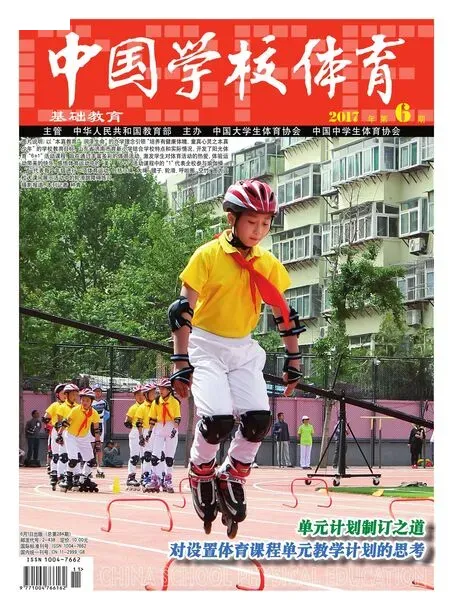技能“單元主題”的提出及價值認識
孫喜和陳昌福
(1.浙江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科學學院,321004;2.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東吳中學,315113)
網研集錦
技能“單元主題”的提出及價值認識
孫喜和1陳昌福2
(1.浙江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科學學院,321004;2.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東吳中學,315113)
編者按:本期話題研討是續“案例研析”欄目關于“如何合理制訂單元計劃”的第6次專題系列,以“操作性動作技能教學單元計劃”為主題,以水平二(三年級)原地側向投擲壘球為例展開的話題研討,旨在引導參與研討的教師能夠理解“感知身體”及其價值。本次研討特邀浙江師范大學孫喜和博士帶領全國一線教師以“感知身體”為主線探討課時內容、評價方式的合理性,結合案例,促使參與研討的教師思考其價值的同時,也為教師在設計單元計劃時拓展思路。本期選擇浙江師范大學孫喜和博士針對研討主題,解讀本期研討的思路;一線教師邱謙從運動概念的視角對操作性動作技能單元設計的探討等文章,給一線教師在設計操作性動作技能教學單元計劃以借鑒。后續“案例研析”欄目將繼續就本系列專題進行深入研討,請各位教師繼續關注,并積極參與(參與話題研討網址:http:// bbs.jsports.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75)。
本期案例研討,從參與情況和議論的問題來看,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首先,參與討論的教師和學生們已經認識到教學內容的設置要以“運動原理”和“教學原理”為支撐,否則教學本身的依據不足。其次,從對“運動原理”和“教學原理”的認識來看,也具有了一定的深度,打破了從概念到概念的簡單認識方式,并從實踐意義上對為了教而教的“教教材”的現象進行了深入解析,并且,以此為出發點,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教學內容如何在一個單元里落實和完成的思考。但是,還是有很多認識和看法,并沒有切入到本期案例的主題,甚至根本不對研討提綱進行思辨,偏離主題地提出一些疑問,出現了研討效果不佳的現象。為什么會這樣呢?固有經驗或者已經定勢的思維是其觀點的本源,因為,體育的功能是多元的,如果側重于某一項功能去認識一堂課,就會在課堂上體現出“自己”想什么就會“教”什么的現象,“自己”是什么就會“教”什么的問題,如,強調“體能”,就會側重于練習;如果強調技術“動作”,就會側重一個一個動作的細節。這樣的思考也未嘗不可,但是,當轉換一個視點來看這樣的教學,就會發現問題,因為,學習對于學習者來說是一個知識“內化”的過程,而每一個練習正是一種技能形成時不可或缺的“內化”的手段和方法。由此所做的每一個練習和每學一個動作,便被賦予了“知識的價值”。那么,每一個練習、每一個動作的實際意義是什么呢?這樣的練習或者是動作對整體(一個項目)教學的貢獻是什么呢?這樣思考時,就是教師所教或學生所學的內在關聯的表現,不應該是一次一次孤立的課的存在。一次課所教(所學)的內容應該是一個項目(運動文化)被有效地分解為可教(可學)的一個知識點,而這些點的連續就是一個知識的集合所形成的單元,進而單元與單元的累進與遞加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內容,最后表現為所學的知識體系。可以說,一次一次的課雖然只是所教(所學)的一個一個很小的知識點,但這些知識點應該服務于這個項目(運動文化),這也是筆者所強調的大運動觀。那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一個一個知識點表現出來,形成單元、形成體系,達到運動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本期研討所提出來的“身體感知”這個主題,就帶來了這樣的思考和啟示。
一、對“感知身體”的理解
體育學科的運動技能學習與其他學科的文化知識學習的根本不同點在于活動的“主體”不同,如果其他學科的學習是以腦為中心展開的思維活動,體育學科的學習則是腦身聯動的身體表現類活動,其典型特征是學習結果的直觀性。如,其他學科的學習成果,只有經由教師的批改作業、考試等判斷后,結果才會呈現出來,屬于延后判斷。而體育學科學習的成果具有即時性和表現性,效果的好壞一看就知,因此,體育學科的學習更具有難度和挑戰性。
1.對“知”的理解,這一點與其他學科相同,屬于“腦”的功能。布魯姆對“認知目標”的分類規定:認知目標有六個方面,即識記(知道)、領會(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和評價,并且這六個方面還可以被分為兩個層次,即初級層次的知識把握和高級層次的能力體現。運動學習同樣存在著這樣的規律,一個技術動作的“知”的內容包括布魯姆所說的全部六個方面,如,籃球的雙手胸前傳球,從動作結構的記憶到競賽場上瞬息萬變情況下的靈活運用,并不是一個動作的簡單再現,是從對初級層次的動作把握到高級層次靈活運用的能力表現。
2.對“身體”的支配,這一點與其他學科明顯不同。任何一個動作都包括肌肉群間與腦的聯動過程,有時,即使我們很清楚“知”的內容,但卻不能很好地把動作做出來;有時,我們能夠完成動作,但卻感覺到不充分,都屬于腦身聯動問題,此問題在運動解剖學和運動生理學教材中都有解釋,不再做具體說明。
“身體感知”實際上說的是我們在學習一個動作或者完成一個技能時,自我感覺的程度問題。這種提法也是“活生生”的自己的一個詮釋。運動學習時,“我”是否知道我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樣,非常重要。教師(他)只能根據“我”做的結果來提供指導意見,最終動作的好壞還是由“我”的“知”和“身體”表現來決定。本期案例研討提綱中提到的“不管是拋得準,還是擲得遠,其關鍵點是控制身體的用力,保證器物按照合理的軌跡運行。由此,引申出對身體的控制和對器物的控制兩個核心要素,即‘身體如何移動?’和‘器械如何控制’兩個核心要素,也就是找到投擲時的身體感覺是教學的關鍵點和難點。為了探尋這樣的身體感覺,我們嘗試制訂水平二(三年級)原地側向投擲壘球的單元計劃,此單元計劃暫不考慮出手角度問題,側重解決身體的合理運動及對器械的控制能力,在‘運動學習中,讓學生能夠直觀地體驗到他所做的運動’是單元指定的基本出發點”這樣一個提法,恰恰符合由“我”的認識來決定“我”的行動這樣一種思維認識,這也是“身體感受”提出來的關鍵所在。
二、技能主題的凸顯
在案例研討中,雖然“身體感受”是作為設計的中心和第一個問題點被提出來的,但是,如果進一步思考,卻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技能主題”問題。
以往的教學,出現過“快樂小孔雀”“我是郵遞員”這樣的課堂主題的教學,在此,對于其功過是非不作評價,但給我們的啟示是這樣的生活主題反映了一種教學思想。這樣的教學思想不管從傳統的教學角度講,還是從現代學習論上解釋,都有其歷史貢獻和價值。然而,如果從技能教學的角度來思考,在龐大的運動技能知識體系中,如何去提取技能的關鍵點,有效地傳授(教)和學習(學),就缺少不了這樣的技能主題的存在,因為一個一個的技能主題才可能構成一個技術或戰術的體系,否則很可能會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如,籃球的核心技術并不多,而“傳、投、運”是技術中的重中之重,如果不對其主題進行明確,就會把“傳球”泛化和簡單化處理,卻還不知錯誤所在,如,小學教的“雙手胸前傳球”和初中教的“雙手胸前傳球”以及高中教的“雙手胸前傳球”的內容可能相同,但因其主題不同,卻可以使得教學豐富多彩。
這樣的技能主題的確定,要按照運動技能形成規律、運動學習規律和技術、戰術體系規律來規定,如,小學的“雙手胸前傳球”可以規定為“傳球游戲中的雙手胸前傳球”,以此為基礎進行各種基本活動能力前提下的雙手胸前傳球教學;初中的“雙手胸前傳球”可以是“技術技能拓展中的各種傳球”,高中的“雙手胸前傳球”可以是“戰術及比賽中的傳球技巧”。雖然這是一種理論構想,但具有可操作性,從中可以看到知識體系的連續性和系統性,也對只見一次課不見整個項目的教學是一種完善和發展。
由此可見,技能主題的提出,是單元可操作化的關鍵所在,也是泛化單元具體化(如,小學的籃球單元、初中的籃球單元、高中的籃球單元實際上是一種泛化的說法)的一種表現,而這一切的根本就是內容的體系化的要求。
盡管本次案例的研討提出了新的問題和視點,但還是有很多問題存在,如,技術的感知與身體的感知的區別是什么?技術單元的主題也不夠明確,這些問題均有待于更深一步的討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