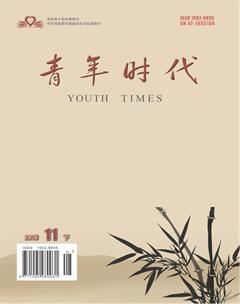河洛體育文化與隋唐大運河
周明華 周靖坤
摘 要:不同時代的體育與該時代的經濟也保有著千絲萬縷的微妙關聯。欲深刻理解隋唐時期的大運河、體育與經濟,不可回避的就是當時的大運河經濟與體育的關系。隋唐大運河經濟與體育的關系解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隋唐運河經濟繁榮推動了體育的發展;二是體育蓬勃發展為隋唐運河經濟創造商機。
關鍵詞:隋唐大運河;經濟;體育文化
體育的發展受生產工具、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直接影響,隨著生產力的變革而不斷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關系密切。從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人類基本上都處于體力勞動時代。這種時代形勢下的體育在中國還沒有衍生出與現代相同的體育概念形態及活動形態,它的存在需要依附更多的娛樂、祭祀等風俗本質,更多的蘊含在文化范疇中。我們恐怕無法套用當前解讀體育與經濟關系的相關理論去詮釋它,理解它。
隋唐大運河經濟繁榮對體育發展的推動。隋唐大運河的核心位于洛陽盆地的洛河,使之成為隋都洛陽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御河。河道沿岸經貿繁盛,武則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在洛陽立德坊南營建新潭:“天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填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那時,“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在洛河上是“漕船往來,千里不絕”。其經濟的繁盛場景毋庸贅言,由于隋唐大運河經濟的拉動,隋唐經濟繁榮、地區間經濟往來頻繁。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為那一時期的體育發展帶來了兩個推動。
隋唐大運河的經濟繁榮推動了體育活動形式的豐富。隋唐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運河洛陽段體育文化的勃興,一方面運河本身就包含著豐富多彩的體育形式,例如龍舟競渡、舞龍舞獅、雜技等運河河流民俗體育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受到運河文化及經濟的影響,運河周邊區域地域文化也繁榮起來,出現了像角抵、蹴鞠、秋千、馬球、武術等更多的娛樂性體育文化素材。這些娛樂文化形式又在后期的發展中伴著古絲綢之路的來往貿易引進來,走出去,日漸繁盛或凋敝。
隋唐大運河的經濟繁榮推動了體育相關產業的發展。隋唐大運河的經濟繁榮在豐富了體育活動形式的基礎上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包括各種體育活動器材的制作材料與技術革新,活動場地的建造與維護等等。根據考古資料顯示,隋唐時期的足球制作工藝比漢朝時期有所發展,具體表現在內外結構上,外表現在球殼是由原來的兩片皮革材料合成發展為由八片皮革對接縫合而成的;內表現在殼內部的內含物是由原來的填充毛發物品改變為充氣式的。后一種改變模式具有歷史創造意義,使蹴鞠的形制逐漸接近現代足球的樣式,因此說,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充氣足球是源于我國,它體現了我國先民們所具有的智慧和創造性。關于馬球,史料考究發現,新疆塔什庫爾干縣城(古絲綢之路要塞之一)北面約一公里的地方還殘留著一個寬大約50米到60米的古代馬球場,為方便觀看,該場地兩側還設置高臺以供人欣賞。這都是運河經濟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直觀證明。
可以說,沒有隋唐大運河帶來的經貿繁盛、文化往來態勢,不可能有中國隋唐特色體育的發展與演變,更不可能出現技術變革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體育蓬勃發展對運河經濟繁榮的促進。體育的經濟效益一般可以解讀為直接經濟效益和間接經濟效益兩大部分。直接經濟效益是指體育活動本身產生的各種經濟運營活動帶來的經濟收益。間接經濟效益則側重于受體育活動及其體育文化發展的要求與影響,為體育活動器材、場地提供材料、設施及食宿服務等產業在其間接的供給過程中獲得的利好。隋唐體育活動的蓬勃發展對運河經濟繁榮的促進也存在這樣的兩個組成部分。
體育活動的開展與興盛,需要龍舟、龍獅、馬、蹴鞠球、角抵場等器材與設置的提供。體育活動開展的越普及,參與的群眾越多,其直接相關的經濟貿易需求必然越高,東市買馬,西市買球的情況自然形成。關于體育活動的經濟往來在那時盡管可能不是經濟貿易的重點,但也是運河經濟往來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的發展也為大運河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綿薄之力。
體育活動的開展,體育貿易的發展也在不斷地帶動著相關行業的發展。即便是采購制造參與活動中,衣食住行仍為生存之本,人無論走到哪里都需要不斷地與社會及他人進行經濟貿易交流。例如去異地采購制作體育活動器材的用品,不可避免的會發生食宿消費,這種間接的經濟行為也是促進隋唐運河周邊區域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
總之,隋唐時期一下子誕生了幾十座沿河的繁榮城市。它們因河而生,因河而旺,又因需要人才聚集,各有分工。衍生出了運輸、搬運、收稅、管理、造船、倉儲、貨物集散、做買賣,經營旅店,飯店,美人街,唱戲娛樂,辦學堂等等各行各業。體育與它們一樣,都在享受著大運河經濟繁榮的同時,又為這份繁榮的經濟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隋唐大運河影響下的河洛體育文化形態。隋唐時期(581-907),是中國封建經濟向上發展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強盛的時期。唐代前期社會經濟的繁榮,封建統治者對軍事和科舉(包括武舉)制度的重視,有力地促進了體育活動的全面發展,在開元天寶年代,出現了體育上的鼎盛局面。除繼承并發展了南北朝盛行的各種與體育有關的觀賞娛樂性項目(如舞蹈、雜伎、圍棋等)外,武藝、各種球戲、角抵及民間體育活動也得到復興和明顯的發展。五代時(907-960),軍閥割據,連年戰亂,體育活動逐漸衰退,但某些項目如擊鞠、角抵等,仍然在流行。
隋唐時期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歷史時期,隋煬帝建立大一統的政權后,為了加強對南北方的統治和控制,從公元605-610年開鑿了以洛陽為中心的,北至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運河,到了唐代對隋大運河進行擴充、整理,形成更為宏大的大運河水運系統,運河打開了南北交通,這樣的交通便利極大地促進了南北經濟的交流,洛陽成了商賈云集之地,促進了洛陽及周邊地域的經濟的高度繁榮。
隋煬帝時期,河洛地區的中心城市是洛陽,當時洛陽經濟的發展得益于隋唐大運河的開鑿,運河打開了南北交通,這樣的交通便利極大地促進了南北經濟的交流。因此,洛陽成了商賈云集之地,促進了洛陽及周邊地域的經濟繁榮。由于經濟的繁榮,國庫糧倉的豐滿,以至于到了唐朝初年,隋政府倉庫中的糧食還沒有使用完,可見其數量之巨大。因此,元人馬端臨認為,從古至今隋朝最富有,盡管他的說法不一定準確,但具有一定客觀性,所以,諸多歷史學家認為,隋朝是我國各個朝代最富有的朝代之一,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種巨大經濟實力的環境下其當時的體育文化一定是有堅實的物質基礎作保證的。
河洛地區的經濟繁榮除了隋煬帝時期,在唐朝也表現得非常突出,隋煬帝大運河迎來了唐代的開元之治和宋代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唐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礎。隋朝雖短,可是換來了唐朝的長治久安。例如:“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就是對當時盛世時期歷史景象的高度概述。根據《元次山集》記載:“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可見,盛唐開元時期,到處開墾農田。到了唐玄宗時期出現了“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較量”。以至于唐代大詩人杜甫在他的《憶昔》中生動地描述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由此可見,河洛地區在漢唐時期,其社會經濟相當繁榮,這為河洛地區的人們參加體育活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堅實的物質基礎,于是,便出現了像角抵、蹴鞠、秋千等更多的娛樂性體育文化素材。
隋唐大運河的開鑿把幾大水系的串通在一起,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與交流以及中外的國際交流,大運河仿佛為絲綢之路接上了手腳,一方面把地中海周邊和中亞的文化和中國內陸的文化鏈接了起來,輻射開來,另一方面,把北方的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鏈接了起來,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生成、鞏固和壯大。此兩者的文化大交流因隋代大運河的挖鑿而在后代大放異彩,結出具有深遠影響的豐碩成果。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把中原文化帶到了北方,帶到了南方,也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魚米桑茶水鄉文化帶到了中原,實現了中華文化的多元化、互補化和共繁化。可以說,沒有隋唐大運河帶來的經貿繁盛、文化往來態勢,不可能有中國隋唐特色體育的發展與演變,更不可能出現技術變革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唐朝體育文化在隋唐體育文化當中,可謂是絢麗多姿、博大精深,堪稱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精粹,它是中國體育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時代體育文化。我們可以使用“史無前例”和“空前發展”兩個詞匯來形容和概括唐代體育文化。因為,唐代的體育是在當時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并孕育的,故此,該時期的體育對后世乃至亞洲很多國家的體育文化都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
此時期的體育活動內容既有繼承,又有引進、改進和創新,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了蹴鞠、馬球、角抵、競渡、拔河、圍棋、百戲、春游踏青、重陽登高、寒食蹴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