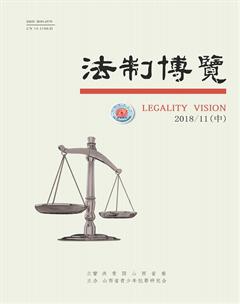我國讓與擔保制度淺談
摘要:雖然讓與擔保在實踐中已較為普遍地存在,法學界對于讓與擔保制度的研究也頗多分歧。但基于我國為成文法國家及讓與擔保自有的缺陷,在立法未正式確立該項制度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不應隨意突破物權法定原則和流質契約無效的限制。最高法最新判例引用《民法總則》相關條文作為裁判依據,對各級法院認定讓與擔保效力提供了指引。
關鍵詞:讓與擔保;理論研究;司法實踐;裁判依據;指引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32-0216-02
作者簡介:李繼輝(1972-),男,四川營山人,碩士,西華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治理論與實踐。
讓與擔保(或稱非典型性擔保)目前并未被我國立法所確立,但在實踐中卻已廣泛存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對讓與擔保的裁決并不一致,極大地損害了司法權威和法制統一。法學理論界對于讓與擔保的效力也頗多分歧。本文擬從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兩方面對讓與擔保問題作一淺議。一、基于最高法判例的司法實踐情況分析(一)最高法判例梳理
截止目前,經中國裁判文書網全文分別檢索“讓與擔保”“非典型性擔保”,最高法共7起判例涉及“讓與擔保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問題。其中,認定房屋買賣合同有效的判例1例([2011]民提字第344號);認定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判例4例([2013]民提字第135號、[2016]最高法民再113號、[2017]最高法民申3248號、[2017]最高法民再154號);未直接認定房屋買賣合同效力,但認定“無買賣房屋的真實意思”的判例2例([2015]民申字第3051號、[2016]最高法民終52號)。
(二)最高法判例認定讓與擔保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裁判理由
1.違反禁止流押強制性規定和物權法定原則
(2013)民提字第135號民事判決書觀點:雙方當事人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行為成立一種非典型的擔保關系。既然屬于擔保,就應遵循物權法有關禁止流質的原則。(2013)民提字第135號民事判決一定意義上催生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7)最高法民再154號民事判決書觀點:根據《補充協議》安排,雙方系以在借款到期前以讓與房屋所有權及保有回購權的方式為借款提供擔保。基于物權法定原則,因雙方沒有按照法定擔保方式設立擔保物權,雙方合同約定內容不能產生物權效力。在債務不能清償的情形下直接由債權人取得擔保物所有權的約定,系我國法律明確禁止的應認定為無效的流押情形。
2.虛假意思表示隱藏真實意思,虛假意思表示行為無效
(2016)最高法民再113號民事判決書觀點:《民法總則》143條第二項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意思表示真實”的條件。《民法總則》146條規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案涉《房屋買賣合同》買賣店面的約定本身是當事人之間的虛偽意思表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真實目的是以案涉店面擔保借款債務的履行,當事人間達成一致的真實意思即隱匿行為是將案涉店面作為借款合同的擔保。根據《民法總則》146之規定,案涉《房屋買賣合同》本身作為偽裝行為無效。
(2017)最高法民申3248號判決書觀點:因雙方系以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形式為借款提供擔保,也即名為商品房買賣實為擔保,雙方并不存在真實的商品房買賣的意思表示,因此雙方以虛假意思表示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應屬無效。
最高法2017年12月的二判例中,均是以同樣的理由闡釋讓與擔保房屋買賣合同效力。(2016)最高法民再113號裁判文書則是直接明確引用了《民法總則》146條,(2017)最高法民申3248號裁判文書雖沒有直接引用該法條,但實際上是該法條的應用。(三)最高法判例的指引意義
1.最高法司法判例關于讓與擔保房屋買賣合同效力認定的主流觀點是無效說。
2.最高法司法判例否定讓與擔保買賣合同效力的裁判理由引入了認定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的新規則。
長期以來,司法實踐中基本以物權法定原則和流質契約無效否定讓與擔保,最高法2017年的二判例引用《民法總則》146條確立了認定讓與擔保買賣合同效力的新規則。
3.《民法總則》146條確定了從“意思表示”角度認定民事法律行為效力的新規則。
(1)《民法通則》關于“意思表示”對民事行為的效力認定。因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第58條)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的行為為無效(第58條);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的行為(第59條)為可變更或可撤銷。
(2)《民法總則》關于“意思表示”對民事行為的效力認定。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第146條);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第154條);基于重大誤解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第147條),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為可撤銷(第148條);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第149條);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脅迫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脅迫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第150條)。
對比二者可知,《民法通則》與《民法總則》從“意思表示”要件認定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則有了較大變化。《民法總則》將《民法通則》中“可變更或撤銷”統一歸為“可撤銷”,而取消了“可變更”。《民法總則》146條則是從“意思表示”要件確立了認定民事法律無效的新規則,此處的“意思表示”不真實是雙方通謀而為,與可撤銷情形下的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實屬于不同情形。
4.通謀而為虛假意思表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可能性。名為房屋買賣實為借貸關系中,當事人可以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形式掩蓋借貸中不受法律保護的非法利息。
5.從立法層面追索,《民法總則》被認為是我國對《德國民法典》117條的法律移植:須以他人為相對人而做出的意思表示,系與相對人通謀而只是虛偽地做出的,無效。另一法律行為被虛偽行為隱藏的,適用關于被隱藏的法律行為的規定。我國臺灣民法典第87條也是源于德國民法典: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但不得以其對抗善意第三人。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于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
結合最高法判例和《民法總則》146條,各級法院認定讓與買賣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既有司法實踐判例指引,亦有明確的裁判依據。二、法學理論界主要觀點梳理(一)肯定說
代表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楊立新教授。楊立新教授將房屋買賣合同作為擔保稱為“后讓與擔保”,認為應當肯定其效力,其性質是物的擔保,不是傳統的物權擔保,而是非典型性擔保①。肯定說者基于讓與擔保在現實中的廣泛存在而提出應突破物權法定原則,認可讓與擔保這種新型擔保形式。(二)否定說
代表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王利民教授等。否定說者提出,讓與擔保違反了禁止流質契約的規定。房屋買賣讓與擔保本質上就是未來物上的抵押權,并非一種新型物權②。否定說基于物權法定原則對讓與擔保予以否定。因此,司法實踐中,持此觀點者以流質契約無效而否定讓與擔保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說
部分研究論者提出,應肯定擔保效力,否定合同之效力,或者應肯定合同之效力,而否定擔保之效力。
(四)讓與擔保制度在我國《物權法》立法過程中始立終棄,說明讓與擔保并未為法學界主流理論認可
總之,我國為成文法國家,雖然讓與擔保在各領域的法律實踐中已經普遍存在,法院裁決還是應以現行立法為準繩,而不宜隨意突破物權法定原則和禁止流押之規定。《民法總則》生效后已可為讓與擔保效力認定提供裁判依據,最高法裁判文書也已經明確引用《民法總則》146條為裁決依據,各級法院應當遵循。[注釋]
①楊立新.后讓與擔保:一個正在形成的習慣法擔保物權[J].中國法學,2013(3).
②董學立.也論“后讓與擔保”——與楊立新教授商榷.中國法學,2014(3).(上接第218頁)
如果該禁止規定的實施,不僅不能達到保護特定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反而會給特定相對人造成不利后果,在這種情形下,執意執行該禁止規定很明顯違背了立法的初衷,也違背了相對人的意愿,相對人應有權拒絕“被保護”。在上述案件中,如果沒有《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的禁止性規定的約束,陳某完全可以與A公司解除勞動合同,并順利拿到其應得的33萬多元的經濟補償金。正因為有了《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使A公司維持與陳某的勞動關系符合法律的規定,并得到勞動仲裁委及各級法院的一致認可和支持,但同時也令陳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為比陳某晚入職A公司的幾位老員工,已經各自拿到幾十萬元經濟補償金離開了A公司,陳某成為被動“被保護”的對象。
“被保護”應是陳某的權利,對于該權利,陳某本應享有行使或放棄行使該權利的選擇權,也就是說,陳某有權選擇放棄該“受保護”的權利。然而,基于現有的法律規定,若發生與陳某案情類似的案件,相同的裁決、判決、裁定將會再現,除非對《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進行立法修訂,才能避免勞動者再次“被保護”。
四、對《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的修訂建議
為了更加精準地保護需要保護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使需要保護的勞動者獲得應有的保護,不需要保護的勞動者避免“被保護”,需要賦予勞動者選擇權,讓勞動者在被保護前享有表達并決定是否需要被保護的權利。故此,作者建議將《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中規定的“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修改為“勞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同意被解除勞動合同的除外”。[參考文獻]
[1]張在范.論勞動法的直接目的與終極目的[J].河南社會科學,2009(1):91-94.
[2]廣州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穗勞人仲案[2014]2650號仲裁裁決書.
[3]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書.
[4]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一終字第2423號民事判決書.
[5]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