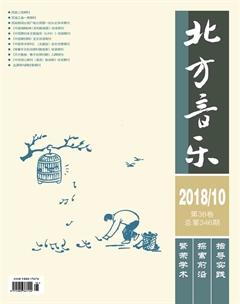談交響樂隊指揮藝術
陳蕙如
【摘要】交響樂隊的演奏是一種科學而又嚴謹的藝術形式,成功的交響樂曲演奏通常都是在樂隊指揮合理的藝術構思與富有成效的排演手段下形成的。但這是否意味著指揮在作品排演的任何時刻都是樂隊唯一的意志體現和藝術動力呢?樂隊演奏員在千變萬化的技巧因素中的藝術地位及其與交響樂隊指揮個性特征的關系究竟如何,這是樂隊訓練中首先需要明晰的問題。
【關鍵詞】交響樂隊;指揮;個性;尊重;配合
【中圖分類號】J615.2 【文獻標識碼】A
指揮,將一百個人焊成一個歌唱的巨人,發出最美妙復雜的聲響,一揮手就能讓喧鬧的弦樂降至喃喃低語,再一揮手就能讓銅管迸出勝利的號角;抬一根手指,再一根,再一根,就知道樂團的每分子時刻準備掀起一輪狂喜的波瀾;他傾身向前,有一刻靜止不動,手里空空,接著用最后一揮讓他們全體咆哮歌唱,
一、指揮功能與發展
今天,指揮的首要功能是詮釋。不過人們清楚的是,有音樂的地方就有節奏。節奏能引起明顯的反應,聽眾無論是成人還是小孩,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感受到節奏時都會踮腳、搖晃身體、揮舞手臂。當一群人聚在一起演奏或歌唱時,需要有一個人提示大家開始。這對五六人的小團體同樣適用,比如意大利牧歌或伊麗莎白時代的牧歌(牧歌音樂的節奏有時相當復雜)。古代文獻中也會提及節拍問題,比如賀拉斯讓少女和小伙子注意薩福式的腳步和響指。這樣說來,賀拉斯就是一個指揮,他用手和腳為自己的歌曲打節奏。
對指揮職責的最早描述之一來自埃利亞斯、薩洛蒙的《論旮樂》,年代約在十三世紀晚期。薩洛蒙寫道:“指揮應是歌手中的一位,且必須了解所唱的歌曲的方方面面。他用手打著拍子,給其他歌手何時休止的信號。如果有人唱錯了,他會對這人耳語‘你太響了‘太輕了或是‘你的調子錯了,這樣其他人不會聽見。有時如果他發現其他人走調了,還得自己唱出聲來糾正他們。”
十五世紀,西斯廷唱詩班的習慣是由一位主管拿一卷紙或一根短棍來打拍子,此工具稱為指揮棒。如果沒有專家在場,就由某位歌手來指揮。《音樂行為探微》的作者奧尼索帕庫斯描述了首席歌者的手的動作,“他根據音符的特性,以小節為單位來指揮一首歌曲。”1583年天文學家伽利略之父溫琴佐·伽利略在《對話錄》中提到古希臘人“不像現在人一樣習慣打拍子”。
此類早期打節拍的人無非是確立正確的速度,以免音樂沖得太快。這種實踐似乎在十八世紀早期之前是很普遍的。10年的一幅畫可能畫的是巴赫在萊比錫圣托馬斯教堂的后繼者約翰·庫瑙,畫中頭戴假發的音樂家對著樂隊和合唱隊揮舞一卷紙。171約翰·貝爾寫過有人用拳頭指揮,還有人用頭指揮,也有人用手,有些用雙手,有些用一卷紙,有些甚至用一根棍子。
隨著樂團的進化,此類指揮漸漸消失,直到一百多年后才重新出現。這是一個奇特的進化過程。先是指揮消失,然后隨著樂團越來越復雜,又出現了與之同樣復雜的交響樂團指揮。“指揮”幾乎永遠是作曲家,他常常為曼海姆、巴黎、薩爾茨堡、萊比錫的特定樂團作曲。在這種情況下,作曲家的配器方式取決于與他合作的樂隊配置。樂曲的配器法須適應個體演奏者的需要。
二、指揮個性
指揮通過樂隊將音樂符號轉化成有意義的聲響。每位指揮對符號的解讀都不同,因為他們個性不同。小孩會問“天上有多遠”,而對一位指揮來說,“多快才算快?”可不是什么幼稚的問題。多快才算快?當莫扎特寫下“小快板”,到底是快步還是小跑?每位指揮都會有自己的想法。他要做的就是跟隨直覺,這些直覺的基礎是多年的思考和學習。指揮擁有統帥力,無比的尊嚴,極佳的記憶力,豐富的經驗,強烈的風格和寧靜的智慧。他已經受過烈火的考驗,但仍未熔化,反而閃耀出一種刺目的內在光芒。他有多重身份:音樂家、管理者、執行官、使節、心理學家、匠人,哲學家以及可以隨時發怒的人。像許多偉人一樣,他出身低微,在公眾眼屮,他是天生的演員。就事論事,他是個自大狂,指揮必須是。如果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沒有絕對的信任,他就什么也不是。
指揮和他的樂團應該融為一體。如果他有知識和內在力量,就可以讓樂團完全聽從于自己。然而這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成就的(除非是尼基什或萊納那樣的人物),彼此熟悉、磨合的過程往往需要好幾年。但前提條件是指揮必須優秀。一支樂隊通常只要花上15分鐘就知道面前的新指揮是真誠還是虛偽,是不是在例行公事,是優秀的音樂家還是偉大的音樂家,個性是不是負面,是否強勢到能夠在任何反對聲中將自己的理念推行到底。越偉大的指揮家,就越有原創力,思想更強勢,對同時代人的沖擊也越大。這種沖擊相較而言更容易描述,因為獨創性總能引起敬仰之情(或者說羨慕),接著就會有大量文字試圖評價(或支持或反對)和闡釋這種獨創性。只要遍閱那些與偉大指揮家相關的文獻,你就會發現其中驚人的一貫性一一個時代如何呈現這些人物。哪怕是反對的聲音(事實上多半正是這些反對的聲音)也為某人在歷史上尋找一席之地提供了寶貴的幫助。1855年戴維森攻擊瓦格納的文字就恰好證明了瓦格納指揮的力量以及他把保守思想逼瘋的能力。的確,偉大指揮家的核心特點能夠得到精準地重現。里希特不動聲色,彪羅矯揉造作,尼基什有催眠效果,門德爾松速度快,馬勒有張力。
指揮通常會用一根七至十五英寸長的銀色錐形細棍,一頭有木柄,重量不超過一盎司。這叫指揮棒,指揮揮舞著它打下嚴格的節奏。有些指揮比如理査、施特勞斯或卡爾,穆克,會紋絲不動地站著,用極小的動作移動指揮棒的尖部。但庫塞維茨基和迪米特里、米特羅普洛斯不用指揮棒,他們會抽搐、顫抖、踮高腳跟;至于富特文格勒,第一次看到他打拍子的樂手們都會絕望,因為完全不知所云。還有一些指揮比如伯恩斯坦或萊昂,巴津,會以無限大的幅度抽動空氣,臀腿臂肩并用。這類指揮有時會直接挑戰萬有引力,離開地面,以一種創意和體力的全面迸發翱翔于空氣中。
三、指揮和樂團之間尊重與配合
樂手們有上百種殘忍的方法考驗指揮,他們會無視他的指示,質疑他的拍子,在樂譜里加上錯音,把正確的音符奏高八度或低八度,制造錯誤的平衡。如果指揮要求他們緊跟自己,他們會尊重他;但如果他沒有注意到錯誤,他們也心知肚明。如果失去他們的尊重,站在他們面前的那個人可就慘了。有個可憐的倒霉蛋的故事,他有錢卻沒天分,花錢當上了指揮,卻搞得一團糟,定音鼓手終于忍無可忍,敲出一聲震天巨響然后嫌惡地扔掉了鼓棒。指揮四處張望,他也懷疑哪里出了問題。“是誰?”他想知道。對指揮來說,買下一個樂團的費用很清楚,但要贏得他們的尊重的費用卻永遠是未知數。
指揮和樂團之間至少需要有相互的尊重和理解。而互愛,則要求太高。樂手們傾向于視指揮為做規矩的人,有時會沒心沒肺,甚至是虐待狂、而指揮傾向于把樂手們看成一群沒規矩的小孩,如果不加管教,到了青春期一定會惹麻煩。兩方都有道理。
一個交響樂隊,對作曲家通過音樂旋律、節奏、和聲、配器等復雜過程創作出的交響樂曲,在指揮的組織調動下,給以深入理解,準確詮釋,恰當處理,精心排練,最后在舞臺上呈現給觀眾。這一系列的過程就是交響音樂的再度創作過程。這一創作過程,不是作曲家那樣的個體智慧,而是交響樂隊默契合作的整體效應。可以說,這是交響樂隊對交響音樂藝術再創作的一個特點。
參考文獻
[1]姜興東.指揮工作設計研究——以合唱《嘎俄麗泰》為例[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10.
[2]姜興東.合唱作品案頭工作設計研究[J].北方音樂,2013(09):57-58.
[3]韓德森.高師合唱指揮課程綜合改革構想[J].中國音樂教育,2000(1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