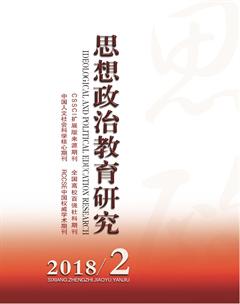政治穩定視閾下的高校輿情治理研究
肖克 劉桃
摘 要:從政治穩定視角研究高校輿情,可以將高校看作二級系統,是政治國家的子系統。通過設定政治穩定的指標體系,可知高校作為子系統,對一級系統政治穩定的短期影響主要體現在政治態度上,長期潛在影響體現在由政治態度引起的政治參與可能性。當下,對高校輿情治理的重點應放在輿情所顯現的政治態度上。高校輿情所體現的政治態度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大學生政治態度上對主導意識形態的接受程度;二是對于政府等公權力部門具體政策與行為的評價;三是對于本國與外國社會政治情況的比較與評價。對其治理也應從多方面著手:制度架構建設與機制動態監測并舉;輿情管理與輿情引導并舉;政府外部引導與高校自我疏導并舉;意識形態引導與文化認同并舉。
關鍵詞:政治穩定;高校輿情;治理;系統理論
DOI:10.15938/j.cnki.iper.2018.02.027
中圖分類號:G6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8)02-0077-06
中國共產黨一向重視輿論輿情工作,并深刻認識到輿論引導、輿情治理與政治穩定之間的密切聯系。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制機制。……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1]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和國家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做好高校宣傳思想工作,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建設,是一項戰略工程、固本工程、鑄魂工程,事關黨對高校的領導,事關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后繼有人,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2]2016年底召開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強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關系高校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3]高校是政治穩定的重點領域,關系國家政治穩定的大局和未來,大學生是政治穩定的主要影響力量,如何從政治穩定的角度探討高校輿情治理的核心要素、特殊性與路徑,為整個社會與政治系統的政治穩定服務,正是本文目的所在。
一、輿論輿情:涵義與特征
對輿論的關注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關于公共輿論的概念,在西方世界思想史上有悠久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對政治過程性質的早期思考。直到18和19世紀廣大民眾參與民族國家的政府活動的程度日益提高時,這一概念才開始頻繁使用。在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中,盧梭是第一個使用這一概念的。”[4]在西方,對輿論輿情的關注和研究開展的比較早,柏拉圖認為輿情對于正義城邦的實現只有負面效應,根據輿情的政治制度設計自然導致“暴民的統治”。[5]來自文藝復興前期的馬基雅維里盡管出于統一意大利的現實政治目的而贊同君主制,但他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為群眾為輿論輿情的正當性正名的人,他主張明智君主首先應該是個“政治心理學家”,掌握民眾心理,引導輿情站在自己一方。[6]作為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的理論旗幟與精神導師,盧梭曾將輿論說成是“心中的法律”,在他看來,公意(在某種程度上以普遍輿論形式體現)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應由其統治,這才能實現所謂“人民主權”。[7]西方輿情研究歷史上不可越過的一個人物就是勒龐與他的《烏合之眾》。同樣是法國人的勒龐沒有完全繼承同胞盧梭的理論,他的關注點與馬基雅維里相似:對群體輿情進行心理分析,但他的結論卻與柏拉圖相似:賦予輿情和民眾一種破壞性色彩,然后兜售一種特別精英的意識形態。只不過與柏拉圖不同的是,勒龐的方法是建立在現代科學與精神分析學的基礎之上。[8]1922年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出版了《公共輿論》一書,可以視為當代輿情研究和政治傳播學的開山之作,在書中李普曼將輿論權置于與行政權和立法權等傳統政治權力近乎平等的地位,討論如何建立一個公共輿論機構,以更好的實現民主。[9]
在我國,關于“輿情”的涵義,古已有之。《左傳》中“輿者,眾也”一句最早指出輿情的重要特征是與公眾密切相關。“輿情”一詞在《辭源》中被界定為“民眾的意愿”;《新華字典》將其界定為“群眾的意見和態度”。學術界關于“輿情”問題的研究成果也比較豐富。有人將輿情定義的較寬泛,指出“社會輿情是一定時期、一定范圍的群眾對社會現實的主觀反映,是群體性的思想、心理、情緒、意見和要求的綜合表現,是社會發展狀況的溫度計和晴雨表。”[10]有人將輿情內涵概括的相對狹窄,將之基本等同于政治態度:“輿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圍繞中介性社會事項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主體的民眾對作為客體的國家管理者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11]
本文認為輿情是社會民眾基于自身利益訴求而表達的對社會客觀現象(特別是熱點事件)的一種以政治態度為核心的普遍情緒,這種情緒的力量在于其經常轉化為對政府相關政策的影響。
輿情的定義揭示了輿情與政府之間的緊密聯系,或者說輿情的影響主要在于其政治效應,即輿情通過政治動員轉化為政治行為的能力。輿情具有客觀性、公開性、開放性、波動性、多數性和被動員性等特征。客觀性是指輿情一旦形成就是客觀存在的,就會持續對相關利益方與政治系統產生壓力。輿情的公開性和開放性主要在于就某一議題持相同或相近觀點的個體產生聚合,聚合后產生群體效應,并進而憑借此群體聚合效應產生壓力,因此它不可能是封閉的和私人的。波動性是指隨影響因素變化,輿情內容和指向也發生變化,甚至完全倒轉,更重要的是時間的流逝往往導致某一特定輿情影響力減弱。多數性指輿情的力量來源于群體效應,即支持某一輿情的人越多,該輿情影響力越大,當然這種多數性經常會被夸大。既然民主時代的輿情具有一種天然的正當性,因此某些政治團體或個體甚至政府,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往往操縱輿情,進而動員民眾,以獲得對其有利的結果。
二、政治穩定:理論與測量
從系統論與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看,任何系統的穩定都是該系統生存的首要問題。伊斯頓(David Easton)將系統理解為“政治生活可以視為相關活動所組成的全體”。[12]系統(見圖1)主要承擔價值分配,也就是“轉變(conversion)”的工作:系統外的環境中的輸入項(包含需求(demand)和支持(support)兩種)進入政治系統,然后政治系統作出決策,以輸出項(決策或決定)的形式重新作用于環境,并形成反饋。系統的穩定在于輸入、決策和輸出三個關鍵環節的通暢和功能正常,從而使整個系統處于動態平衡,這就是系統的穩定狀態。結構——功能主義也是從整體和系統視角看待政治穩定問題,認為組成系統的關鍵部分之間的關系構成“結構”,每個部分不僅有自己的作用,而且對其他部分有很大影響,所謂系統的穩定就是各部分都發揮有利于系統功能實現的正作用,同時與其他部分是一種和諧的關系。[13]
如圖1顯示,從子系統(二級系統)與一級系統的關系角度考慮系統穩定問題,政治穩定的關鍵在于政策“輸入”環節——子系統對一級系統是“要求”還是“支持”,“支持”意味著基本贊同一級系統決策,有利于一級系統穩定;“要求”則意味著給與一級系統壓力來改變既有政策,不利于系統穩定。
從系統論和結構—功能主義視角研究高校輿情對政治穩定的影響,主要有兩個層面(見表1):一是將高校看作二級系統,是國家的子系統,研究高校輿情對整個國家政治穩定的影響;二是將高校看作一級系統,高校自身的穩定問題關系其生存,因此對高校來說是“政治”穩定問題,即生死攸關問題。
本文主要是將高校視為二級子系統,研究其對國家層面一級系統政治穩定的影響。但政治穩定的這兩個層面不是孤立和互斥的,而是彼此促進的。高校二級系統的穩定有利于國家一級系統的穩定,國家系統的穩定也給高校的穩定創造條件,提供背景支持。從高校人口構成來說,管理者、教師和學生三個群體共同構成了高校系統,其中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學生群體顯然對政治穩定影響最大,而管理者和教師群體本身盡管對國家政治穩定具有直接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引導、政治行為規制與政治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對學生群體的約束環境。在我國高校行政化色彩還比較明顯的情況下,管理者與教師這一構成學生群體對國家政治穩定影響的環境因素顯得尤為重要。
政治穩定是國家發展的條件,是政府治理應達到的目標,是實現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礎。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將政治穩定界定為兩個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繼承性。秩序性就是指沒有發生暴力、壓抑或體系的解體。繼承性則是指沒有發生政治體系關鍵要素的改變、政治演進的中斷、主要社會力的消失,以及導致政治體系根本改變的政治運動。[14]普拉諾等人編著的《政治學分析詞典》中指出:所謂政治穩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領導層很少發生變化;或是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相同的憲政形式和過程;或是指在一個國家的政治過程中相對的說沒有暴亂和內部騷亂;在國際關系上,它通常是指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狀態,或是長時期保持國家之間的統治和依附關系。[15]我國國內學者也從不同角度界定政治穩定。鄭慧認為,政治穩定主要是指在特定社會,有利于鞏固政權有秩序的政治狀態和有規則的政治運作和政治運行。[16]吳志成認為,政治穩定指“政治系統在運行中所呈現的有序性和連續性。所謂有序性,指系統內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所謂連續性,指系統功能的發揮不受阻礙,保持正常運轉。”[17]綜合以上定義,本文認為,政治穩定是指政權性質和國家基本制度穩定前提下的政治運行有序。政治穩定的特征在于政權合法性得到認同,政治權力在制度框架內有序透明流轉,政治參與渠道順暢且對政策結果具有重要影響,全社會政治共識明顯。
政治穩定十分重要,但如果僅僅泛泛而論,就會缺乏可操作性,對政治穩定的實際貢獻將十分有限。因此,一種更有效的對政治穩定的研究路徑是將政治穩定分解為一系列相對可衡量比較的指標體系。如R·派伊(白魯恂,Lucian Pye)提出政治穩定的標準在于:政治文化的一體化;政府權威和職責的合法性;政府的有效性;政府的包含性強,以至于公民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參與意識能夠得到滿足;公民參政與政府決策的一致性;社會分配均等。本文主要從政治結構、政治過程、政治參與與流動,國家認同和政治文化五個指標出發來衡量政治穩定,如表2所示。
政治穩定的5個測量指標不是同一維度的,其中政治結構和政治過程2個指標偏重于正式機制(formal form)的測量,更多體現在對公權力和政府政治穩定貢獻的量度上;其余3個指標則側重于測量社會與國家互動結果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政治穩定的環境與長效機制上。對高校等非權力機構和二級系統來說,顯然其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更多的體現在后3個指標上。高校學生不可避免的會形成政治態度和政治意識,并經群體效應而擴散和自我固化,從而形成對政治一級系統的正(支持)態度和負(要求)態度,如果高校學生整體對政府政策持批判甚至否定態度,并通過政治行為力圖表達該態度和實現相關政治目的,那么對政治穩定就是負面作用;與此相反,高校學生群體對于政府合法性與政策均持贊同態度,政府反過來會回饋和獎賞這種支持[18],從而使得以學生為主的高校成為支持維護一級政治系統政治穩定的二級子系統。
三、高校輿情治理:特點與特性
作為特定組織領域內的輿情,高校輿情指發生在高校這一特定社會空間內,圍繞高校內和高校外社會性事件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作為輿情主體的高校學生,對國家政治管理者所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
高校輿情是社會輿情的晴雨表,它與社會輿情在某些方面有所重疊,但很大程度上還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高校的主要群體是大學生,這個群體特點是想法多,較自信,對新事物接受能力強,對網絡技術比較熟悉,信息獲取渠道廣泛,信息共享程度高,并且很容易形成輿情擴散效應,但同時也很容易被混雜的信息所困惑。其次,高校輿情的關注內容廣泛,焦點豐富。當前容易引起高校學生關注的輿情內容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是國內外的突發事件; 二是國內外的熱點問題; 三是高校的熱點問題;四是學校內部改革政策;五是學校教學、管理和服務質量。焦點集中于“教育公平”“教育改革”“校園暴力”“學制改革”等問題,同時“高校腐敗”“師生關系”也成為近幾年的新焦點。再次,高校輿情的傳播方式多樣化,主要以網絡傳播為主。高校輿情的傳統傳播途徑主要是校內布告欄、校內廣播站、新聞媒介。但是隨著現代傳播方式的發展,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網絡途徑成為高校輿情傳播的主要方式,主要包括QQ、校園終端微信公眾號、網絡跟帖等。最后,高校輿情具擴散效應。高校輿情一旦形成效應,不僅涉及國內眾多高校群體及在校師生和工作人員,更是家長關心的焦點;不僅在某地區小區域擴展,通常伴隨網絡會擴散到全國甚至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各類群體當中大學生是最容易被輿情所動員而采取行動的群體之一。一旦被錯誤的輿情觸發行動,那么這種行動的潛在破壞力就值得管理者重視和防范。我們必須通過有效措施使得高校輿情對政治穩定的正面效應充分發揮,同時使其負面效應被壓制和防范。
基于高校輿情的研究現狀和治理現狀,政治穩定成為高校輿情治理的基本價值導向。高校輿情治理針對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高校師生對國家方針政策的理解、貫徹和執行,對自身利益訴求的合法、理性解決;對國家和民族的心理認同,以及以高校群體的創新優勢及知識儲備帶動國家進步等。
四、高校輿情治理:難點與路徑
我國高校輿情治理與研究正處于探索階段,高校輿情治理仍面對很大挑戰。當代輿情網絡化和突發性的特點,遭遇高校輿情的特殊性,造成目前高校輿情治理的難點。具體而言,有以下治理困難:
首先,作為二級系統的高校如何與作為一級系統的國家政治系統在輿情治理上有效對接。目前,很多高校與官方新聞媒介缺乏有效銜接機制,與政府缺乏信息共享機制,導致高校輿情治理中學校與政府和媒體的脫節,使得高校成為輿情的“信息孤島”和“治理孤島”。如何使得高校管理者認識到,高校不僅是學習的場所,更關涉國家政治穩定,使得高校教師認識到高校課堂不僅傳授知識,更擔負政治社會化和政治維穩的任務,這不是一項短期內能迅速完成的任務。同時,作為一級系統,政府相關部門如何與高校互動,對高校提高支持,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其次,高校管理者需要改變輿情治理思維與方式。民主政治與全球化發展推動了公民主體意識與維權意識加強,高校大學生更是如此,這不僅要求轉變輿情治理方式,由傳統的重“控制”輕“引導”轉向重“引導”輕“控制”。更加要注重治理方式的新穎化,要貼合大學生思想動態,符合大學生審美標準,摒棄一味“文件式”和“說教式”的晦澀語言表達,融入更加生動活潑的語言。
再次,如何建立輿情預防和監測機制。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1次全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指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7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而從年齡結構上看我國網民仍以10~39歲群體為主,占整體的73.0%,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占比最高,達30.0%。[19]當前,各種各樣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在網絡交流、交融、交鋒,很有可能導致一些校園小事件演變為輿情大事件,這給高校網絡輿情治理帶來巨大挑戰。現實中大部分高校處理輿情和輿情引發的事件時,仍習慣于舊有的事發后才處理的“后發式”危機處理方式,而不擅長預先判斷輿情苗頭,更是很少能做到事先引導輿情了。
最后,如何建立有效的網格化的輿情快速反應機制。高校輿情集聚、傳播、爆發的過程往往時間很短,這其中除了互聯網的助推作用以外,誘發因素多樣性、隱蔽性、過激性、復雜性都成為高校輿情突發的影響因素。而這就要求治理主體在高校輿情治理中敏銳覺察輿情,及時把握進展,迅速做出回應。高校輿情治理是一項注重細節的系統工程,需要由專業人員進行,而很顯然,目前我國各大高校在輿情監測、匯總、研判、引導方面并沒有足夠專業的團隊,反應處理機制也沒有走向專業化。
此外,我們還應該擺脫一個誤區。高校輿情主體不僅包括高校大學生,由大學生所結成的社團、社會上的同輩群體以及所形成的家庭甚至網絡朋友圈都可能成為高校輿情關涉的對象,高校輿情體現的是這些群體之間的互動,這就要求高校輿情治理要在動態化的過程中解決,同時更要處理好高校與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人們似乎在放棄‘單方面的控制而轉向‘從雙方或多方面進行思考……在這些努力中我們所要解決的(主要)社會政治問題的更高復雜性、更快的動態性以及更大的多樣性等特征開始凸顯。”[20]
在充分認識到高校輿情治理的難點之后,如何有力突破困境,打開高校輿情治理新局面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在高校輿情治理中要始終以政治穩定為價值導向,以政治穩定指標體系為重要衡量。上文政治穩定的指標體系為我國高校輿情治理提供了思路。具體而言,要做到以下四點:
第一,“軟硬結合”:制度架構建設與機制動態運行并舉。高校輿情治理需要建立硬性制度與軟性機制,硬性制度應包括組織保障制度、資金保障制度、法律保障制度和網絡技術保障制度等,軟性機制包括高校與政府、媒體溝通分享機制、輿情交流協調機制、輿情匯集研判機制、輿情危機應急機制等。例如,高校輿情治理失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沒有提前掌握輿情動態,缺乏輿情分析數據參考。就輿情匯集機制而言,首先要明確高校群體輿情關注的重點內容;其次要組織專職人員定期生成動態匯報,可分為多個專題:日常輿情、緊急輿情、輿情波動等。高校輿情匯集生成之后,輿情研判機制發揮作用,就信息真實性,社會影響程度,相關責任主體等情況進行了解分析;輿情研判結果提交輿情反饋部門。輿情反饋機制要明確反饋程序、內容、要求,同時注重反饋的時效性,反饋要及時高效。高校輿情預警機制與輿情匯集研判機制功能相近,可以同時進行。
第二,“虛實結合”:輿情管理與輿情引導并舉。高校輿情網絡化態勢明顯,但并不意味著高校非網絡輿情就不需要被重視。高校輿情治理應堅持校內輿情與網絡輿情雙管齊下。校內輿情治理可在有條件的高校建立校內輿情監測研究中心,監測數據匯總后,可在日常教學中應用,也可以通過校園廣播站公布或召開校園發布會,邀請大學生參與其中發表見解。高校網絡輿情治理要突出發揮自媒體的功能。“引導輿論掌握自媒體傳播話語權,是現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選擇,要充分發揮自媒體思想政治教育的輿論引導功能。”[21]
第三:“里外結合”:政府外部引導與高校自我疏導并舉。治理的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各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22]高校輿情治理主體不僅包括政府教育部門、高校、媒體甚至包括大學生群體。高校可以通過舉辦活動、組織社會實踐等方式,為大學生積極參與政治討論搭建平臺,幫助大學生學習相關的政治知識,了解當前國家的政治現象,獲悉國家的政治動態。針對沒有條件建立檢測中心的高校,可以創建高校輿情微信交流平臺,經常推送大學生喜聞樂見的熱點問題,允許學生群體自由發表見解,同時可以就學校服務網上提交意見。也可以推行“一鍵式”舉報,對可能造成沖突的事件提前化解,優先解決。政府相關部門則可以一定程度上下放權力,但也要及時體察輿情動態,對輿情報送的內容、程序、類型、級別作統一性規范。
第四,“教學結合”:意識形態引導與國家文化認同并舉。高校輿情治理從長遠上來看,離不開大學生群體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和責任感的培養,而教育是提高國家認同的根本途徑。“高校的宣傳思想工作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教育要緊緊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實現從‘灌輸式的顯性傳播到‘滲透式的隱性傳播的轉變。”[23]同時準確地把握受眾特點,不斷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陣地意識與底線意識,恪守政治底線、法律底線與道德底線,以弘揚主旋律、傳遞正能量,全面引領輿論。
五、結論
作為國家政治系統的子系統和組成部分,高校不僅面臨著自身穩定問題,更是對國家的政治穩定具有深遠且切實的影響。高校系統最大的特點是其主要構成人員是青年學生,這使得高校面臨的政治穩定問題具特殊性。目前高校維穩面臨著一些困難,其中如何與國家政治系統更好聯接配合,如何主動引導塑造學生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如何預測監督和對突發性事件迅速反應,這些都是對高校和政府相關部門提出的要求。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EB/OL].(2013-11-15).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2]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 [EB/OL].(2015-01-19).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9/content_2806434.htm.
[3] 習近平在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 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EB/OL].(2016-12-08).http://www.moe.edu.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612/t20161208_291306.html.
[4] [美]杜魯門.政府過程——政治利益與公共輿論[M].陳堯,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35.
[5] [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331-333.
[6] [意]馬基雅維里.君主論[M].潘漢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73-110.
[7]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131-133.
[8] [法]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5-17.
[9] [美] 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3-249.
[10] 王建龍.把握社會輿情[J].瞭望,2002(20):1.
[11] 王來華.輿情研究概論—理論、方法和現實熱點[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32.
[12] David Eas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Ltd, 1965:1.
[13]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M].Glencoe: Free Press, 1949:221.
[14] [美]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89:1.
[15] [美]杰克·普拉諾,等.政治學分析辭典[M].胡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7.
[16] 鄭慧.“政治穩定”概念辯析[J].社會主義研究,2002(4):52.
[17] 吳志成.關于政治穩定理論的幾個問題[J].湖北大學學報,1997(1):103.
[18] Samuel Huntington.The Goods of Development, in M.Weiner and S.Huntington,eds.,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M].Boston: Little Brown Press,1994:21.
[19] 第41次全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EB/OL].(2018-03-05).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20][22]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219,4.
[21] 楊劍釗,許一飛.論自媒體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定位及優化路徑[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8):88.
[23] 馬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校大學生中的傳播與影響力研究—基于對廣東省30所高校大學生的實證調查[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4):147.
[責任編輯:張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