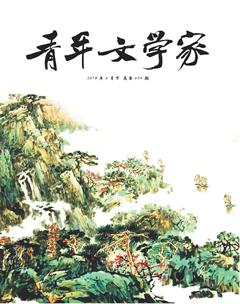論《圣亞尼節前夕》的批判精神
摘 要:濟慈的長篇敘事詩《圣亞尼節前夕》以中世紀傳說為題材,將圣潔的愛情放置在殘酷的現實環境中,詩中想象世界與現實世界交織轉換,在甜蜜與冰冷的鮮明對比中批判封建宗教思想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
關鍵詞:《圣亞尼節前夕》;想象世界;現實世界;對比
作者簡介:孫雯(1994-),女,漢族,山東濟南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1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的長篇敘事詩《圣亞尼節前夕》敘事結構獨特,以中世紀傳說為題材,在想象與現實之間自由切換,并在舒緩的敘事節奏、優雅的詩行中營構出一則浪漫的愛情故事。
溯本求源,該詩取材于充斥著宗教意味的中世紀民間傳說。圣亞尼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13歲時殉教,后被認為是處女的保護神,故民間設立了一個紀念她的節日——“圣亞尼節”。據說在該節前夕,貞潔的少女遵循一定的儀式規章,便能見到愛人的影像,接收到情郎纏綿的愛意。詩人借助此傳說歌頌自由與愛情,充滿反叛精神。
詩人營構了對比鮮明的兩個世界:現實世界與想象世界。詩作開篇塑造了一位現實世界中窮困潦倒的祈禱人,他活在自己的宗教世界中,一生為眾生之罪而痛苦悲傷,其凄苦、疲憊的生活是冰冷、麻木的現實宗教生活的真實寫照,與鮮活的愛情形成鮮明對比。詩歌以他“在一堆冰冷的灰燼里物化,長眠不醒”為結尾,交代了祈禱人的結局,暗合開頭“喪鐘已為他敲響”,也預示了他所代表的宗教思想必將消亡。
安吉拉是現實世界另一位重要的出場者,是男女主人公愛情的見證者和促成者,也是想象與現實兩個世界的連接者。她善良、膽小、謹小慎微,代表著長期受到封建統治階級壓迫的勞苦大眾。她在大廳中認出波菲羅后,驚懼不已,顫抖的手緊握波菲羅反復勸說他離開:“快走!快走!矮個子希爾德布蘭 / 最近得了場熱病,病中他詛咒 / 你以及你的宗族、土地和家園: / 還有莫里斯勛爵,盡管白了頭, / 卻沒有半點慈悲心——唉!趕快走! / 逃個沒影兒!”[4]安吉拉樸實的話語揭露出封建統治階級的暴虐以及現實世界的殘酷。然而,這位善良怯懦的老婦人最終因癱瘓死去,臉頰瘦的脫形。[5]其悲慘結局與她自身不無關系,她未曾進行徹底的反抗,答應波菲羅的請求是其最具反抗精神的事情。從這點來說安吉拉比祈禱人更進步,因為她幫助了一對年輕的戀人,而祈禱人從未想要離開也未曾幫助他人離開壓抑凄涼的宗教世界。他們是現實世界被欺辱、被壓迫的代表,其悲涼結局是對宗教世界與統治階級的血淚控訴,濟慈借此警示世人,反抗雖困難重重,但不反抗只能凄慘的死亡。
波菲羅和梅德琳則是勇于反抗、追求自由的代表,他們的愛情是詩人理想的寄托。然而,這份愛情滋生并發展于殘酷的現實世界的夾縫中,兩人“甜蜜的交融”時的現實環境是“西北風在猛烈地吹, / 刺骨的冰雪敲打窗戶,給戀人 / 提出警告,節夕的月亮已經下沉”。[6]夢幻的國度與冰冷的現實交織轉換,前者的美妙使梅德琳沉浸其中不愿醒來,以至于她被喚醒后無法分辨得清夢境與現實。詩人通過梅德琳清醒后的反應襯托出美夢醉人,同時批判冷酷的現實環境。
在似夢似幻的狀態下,兩位有情人互訴衷腸,“他完全融入她的幻夢中”。這種水到渠成的交融顯然與中世紀以來的傳統禮儀相悖,就連濟慈的好友伍德豪斯也認為波菲羅知曉梅德琳的愛意后,應馬上勸說她與自己離開并結婚,這樣才是一種圣潔的愛情。但濟慈堅決不接受這種看似明智的選擇,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感情上的太監才會對那樣一個少女置之不理”。[7]與傳統愛情觀相比,男女主人公的情不自禁更符合人性,他們的自由結合反映了新時代人們要求徹底個性解放的訴求。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并不徹底,殘余的封建制度與宗教思想依然束縛著人們,因此濟慈借波菲羅與梅德琳甜蜜大膽的愛情反映時代要求。詩人基于對現實生活的真實體驗和人性的深刻思索,于神圣的愛情中摻雜了合情合理的愛欲,使詩篇閃耀著人文主義的光輝。
然而,兩位有情人的結局并不完美,詩歌最后一節寫道:“他們倆永遠去了,在很久以前, / 這對戀人逃入了暴風雪之中”。兩個人私奔了,但卻逃進了“storm”中,或許他們能戰勝現實,或許會向現實妥協,一切皆有可能。而“那一夜男爵夢見了許多災變, / 好斗的賓客也都整夜做噩夢, / 夢見了妖巫,惡魔,啃棺的蠕蟲, / 不斷的鬼影憧憧。”[8]這些噩夢預示著以男爵和賓客為代表的封建殘余勢力已行將就木,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現實依舊像暴風雪般冰冷,要想讓他們完全消亡還需要更多梅德琳、波菲羅這類反抗者以及被欺壓人民的努力。
注釋:
[1][4][8]濟慈:《濟慈詩選》,屠岸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前言第1頁、第217頁、第241頁。
[2][3][6]②③⑥穆旦:《穆旦譯文集3濟慈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491頁、第500頁、第503頁。
[5]屠岸譯。原文為“Died palsy-twitched, with meager face deform”,穆旦譯為“老安吉拉癱瘓死去,早已不在”,沒有將后半句譯出,“因癱瘓亡故,臨終時變了面容”比較貼切。
參考文獻:
[1]傅修延.濟慈詩歌與詩論的現代價值[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333.
[2]郭偉鋒.濟慈《圣亞尼節前夕》的非唯美性解讀[J].社會科學論壇, 2005(4):19-21.
[3]劉治良.花神的國度想象的世界——濟慈早期詩歌淺析[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3):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