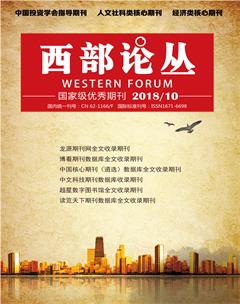引入市場機制的精準扶貧研究~基于政府視角
應澤華 黃東兵
摘 要:精準扶貧中引入市場機制,對提高扶貧資源配置效率,達到扶貧精準目標,打好扶貧攻堅戰,具有重要積極意義。本文主要梳理了引入市場機制對政府扶貧的必要性,市場機制在扶貧中的引入途徑,以及近年來出現的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由于市場扶貧模式的不成熟會產生一些問題,如何選擇扶貧模式和優化市場扶貧機制是我們現在主要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政府扶貧 精準扶貧 市場機制 新型市場扶貧模式
1 政府扶貧存在的問題
自1978年以來,政府一直重視農村扶貧工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扶貧政策,投入了大量的扶貧資金,中國貧困人口的數量和比例都得到大幅度減少。大量實證研究也表明了政府在解決大面積、集中性貧困問題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果[1-2]。隨著扶貧投入不斷加大,農村貧困人口分布也逐漸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新特點,同時貧困居民存在情況不明,使得扶貧資金和措施指向不準,難以扶到點子上。因此,在2013—2015年間,習近平在湘西、云南、貴州等地進行扶貧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的要求,即對象要精準,項目安排要精準,資金使用要精準,措施到位要精準,因村派人要精準,脫貧成效要精準[3]。但是政府扶貧一直存在以下問題。
綜合現有文獻,一方面是政府扶貧制度設計存在缺陷:(1)對貧困戶的判定標準各地情況不一;(2)扶持項目權屬模糊;(3)扶貧的動態管理與考核機制不健全;(4)扶貧資金來源單一;(5)政府存在多部門協調難;(6)貧困戶與政府存在信息不對稱、權力不平等的問題[4-9]。另一方面是扶貧對象自身的缺陷:(1)對扶貧的“建檔立卡”配合度不夠;(2)對政府過于依賴;(3)思想落后和文化程度低;(4)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5)農村黨員隊伍普遍存在老化[10-15]。
2 政府扶貧與市場機制
在扶貧中,引入市場機制可以實現扶貧資源配置最優和提高扶貧資金利用效率,從而實現項目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精準,派人精準,實現脫貧。由于我國市場機制比較成熟,在各地扶貧實踐中市場機制得到廣泛的運用,積累了豐富的
經驗。
2.1 市場在反貧困中的作用
在反貧困中市場對扶貧對象作用方面,劉冬梅(2003)認為市場經濟有助于打破貧困地區原有的封閉循環圈,促進產業開發和經營[16]。葉文振和嚴靜(2013)更具體地闡述了引入市場機制能夠讓貧困群眾借助龍頭企業學會有組織化專業化地生產商品[17]。徐志明(2008)認為引入市場機制有利于培育貧困群眾的市場意識,激勵貧困農戶主動參與到市場競爭中,激發貧困農戶的內在動力和能力[18]。吳敏(2015)認為引入市場機制能打通扶貧對象與扶貧主體之間的聯結,改變貧困人口的“等靠要”的惰性思維[19]。
2.2 市場機制在扶貧中的實踐經驗
底瑜(2005)從四川中巴新村的反貧困成功案例,分析了賦權參與式的扶貧方式,引入市場機制轉變以往的救濟式扶貧方式,實現了有效的扶貧效果[20]。
鄧永紅(2014)從麻陽苗族自治縣石羊哨鄉在該鄉譚公沖村推行“市場化產業扶貧”模式的成功經驗,分析了扶貧融資貸款難、集約經營難、科技種養難的三大問題,以及扶貧市場配置、市場要素、市場合作的三項改革[21]。
李麗榮和張偉(2015)從邢臺市的市場扶貧工作分析了運用市場機制扶貧可以更好地解決資金問題,通過幫扶互助、打造品牌、旅游市場等優勢,為扶貧工作提供新的思路[22]。
2.3 政府的定位
徐志明(2008)指出扶貧開發中政府必須轉變大包大攬的傳統做法[18]。劉冬梅(2003)認為在扶貧中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制訂出相應的經濟政策和規章條例[16]。張延君和劉進寶(2007)進一步指出市場競爭能夠調控的經營活動,政府就不應該直接介入,政府還需做的是進行提供技術和信息服務[23]。張笑蕓和唐燕(2014)還進一步指出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下放扶貧項目審批管理權,同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引導企業參與到扶貧攻堅中[24]。莊天慧等(2015)提出政府除了做好扶貧開發的頂層設計,還需要發揮好調控、監督作用[25]。
3 引入市場機制的途徑
如今,如何引入市場機制成為了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綜合現有文獻,政府扶貧中引入市場機制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扶貧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使得扶貧資源配置最優化;二是扶貧主體的市場化,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扶貧。
3.1 扶貧資源配置市場化
如何科學地配置扶貧資源,是實現精準扶貧的一個關鍵環節。王國勇(2015)提出政府需要下放項目、資金等到縣,調動縣級的積極性,建立以結果為導向的資金競爭性激勵分配機制[8]。鄭瑞強和曹國慶(2015)提出政府利用第三方扶貧服務的精準、專業、低成本、重服務的優勢,通過大數據來實現資源向貧困者流動,提高扶貧資源配置效率[26]。鄭寶華和蔣京梅(2015)提出建立需求響應型扶貧資源供給機制和建設成本分攤機制,讓村民自己決定實施,采取公開公平競爭,誰積極支持誰的政策,以提高扶貧資源配置效率[27]。
3.2 扶貧主體市場化
3.2.1 引導社會資本參與
實現全面脫貧需要全社會廣泛參與,僅政府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在21世紀的扶貧工作中,我們要打破單一的政府扶貧格局,引入市場機制來吸引社會資本,使政府資金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張延君和劉進寶(2007)提出政府資金除了要對貧困地區外部經濟項目實行必要的財政補貼,還要給予必要的稅收優惠,增加企業項目利潤[23]。劉解龍(2015)認為要創造各類市場平臺,從而促進扶貧對象與外部市場的聯系[28]。葉文振和嚴靜(2013)提出更具體的要求,首先要搭建工作平臺,為民營企業參與扶貧開發牽線搭橋,擇優適行;其次以媒體作為宣傳的平臺向社會廣泛宣傳,激發工商企業致富思源、回報家鄉的熱情;接著通過各種宣傳媒體提高民營企業社會影響和知名度,同時引導企業實現戰略性捐贈;最后構筑“村企合作”的共同致富的平臺,形成優勢互補的利益共同體[17]。
3.2.2 構建利益共同體
引入市場機制和吸引社會資本就是為了能夠形成村企的利益共同體。劉冬梅(2003)認為通過要素契約和產權關系,采取股份合作制或租賃機制,來建立企業與農戶之間的利益分配和調節機制[16]。汪三貴和劉未(2016)認為村企利益聯結可以解決貧困農戶所面臨的信息、技術、銷售及資金方面的問題,降低了貧困戶發展產業的門檻[3]。莊天慧等(2015)提出要創新推廣產業化扶貧組織經營模式,建立產業發展基金、眾籌資金等融資模式和渠道,建立契約型、利益返還型、參股合作型等多種形式的產業化扶貧利益聯結機制[25]。鄭瑞強和曹國慶(2015)提出產業鏈式扶貧新機制,通過實施組合式發展扶持模式,可以有效對接多維致貧因素[26]。王國勇(2015)提出當市場效益較好時,由農戶自行銷售,當市場效益較差,由企業實施保護價收購[8]。
4 市場化扶貧模式的新形式
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市場力量的強大,近幾年出現了新的市場扶貧模式,如政府購買服務扶貧、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也稱PPP模式)、扶貧資產收益扶貧等形式。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來梳理新型市場扶貧模式: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的特征,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的實踐,新型市場扶貧模式存在的問題。
4.1 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的特征
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扶貧方式的民營化,這意味著政府需要更多的簡政放權,扶貧項目下放給民營企業和組織。政府由管理型轉向服務型,很大程度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
王焰(2016)認為政府購買服務和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扶貧是通過政府部門和非私營部門、私人部門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現資金、信息等社會資源的進一步整合和優化配置,有效提高扶貧效率[30]。這兩種新型的社會組織與政府合作扶貧模式,打破了政府在公共領域的獨占性,通過借用社會資本的專業性,推動扶貧服務體制機制的改革,有效地提高政府資源的利用
效率。
向延平(2016)認為資產收益扶貧是通過成立相關產業的股份公司等經濟實體,貧困村將自身的各種資源和扶貧資金資產化進行入股,公司通過經營運作產生收益,以股份分紅的形式分配給貧困農戶[31]。這種扶貧方式是扶持失能和弱能貧困人口的有效方式,同時激發具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主體參與合作社等組織載體經營的主動性[3]。
4.2 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的實踐經驗
在政府選擇合作對象方面,發改委文件和財政部文件都指出了項目采購方式和合作伙伴選擇標準,可通過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競爭性磋商和單一來源采購等多種方式,公平選擇具有相應專業能力、融資實力以及符合項目需求的社會資本作為合作伙伴,形成項目競爭機制,也促使地方政府推出優等項目[32-34]。
在政府購買服務扶貧實踐方面,朱駿立(2013)提供了政府向慈善組織購買村級扶貧服務的案例[35]。商思旭(2015)提供了山東省鄄城縣3個村莊的政府向扶貧互助協會購買服務的案例[36]。
在PPP模式扶貧實踐方面,呂輝紅(2015)提供了湖南洞口借鑒PPP模式發展農村扶貧產業的成功案例[37]。周鏢和李曼曼(2016)探索了PPP模式運用于貴州旅游業的機制設計和關鍵問題[38]。云南省在“PPP模式+精準扶貧”方面也已經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運用。
4.3 新型市場扶貧模式現在的問題
綜合現有的文獻,政府購買服務所面臨的的問題主要有,一是我國政府購買服務制度規范尚不完善;二是政府依然占據著絕對的優勢和地位,存在合作的不平性;三是政府購買呈現出“內部化”特征和形式性購買,社會組織成為政府部門的延伸;四是在部分公共服務領域內,政府很難找到多家社會組織承接購買項目;六是缺乏專門的人員對服務的技術問題進行監管[42-44]。
資產收益扶貧模式能夠對收益分配向失能的貧困戶傾斜,增強了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但資產收益扶貧的理論問題探討還不是很多。余佶(2016)認為資產收益扶貧主要面臨著資源資金整合困難、政策配套尚不完善、風險防控難度大等問題[48]。
5 結論
現研究表明,我國政府主導下引入市場機制扶貧還不成熟,存在制度上、公平性上、監管上和技術上等問題,這都將影響扶貧的效率。所以新型扶貧模式與精準扶貧之間的有效銜接,處理好政府、社會資本和扶貧對象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針對多樣的市場化扶貧模式,如何選擇和優化是我們現在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新型市場扶貧模式中,我需要厘清它們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創新性地運用市場扶貧模式,避免單一化,結合地方特點,使各種市場扶貧模式有機結合,揚長避短,實現扶貧工作效率最大化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鑒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建議,使市場機制與精準扶貧有效銜接。一是完善貧困地區市場扶貧的法律法規體系;二是建立新型市場扶貧的示范和宣傳平臺;三是完善引入社會資本到扶貧中的服務規范;四是加強脫貧項目的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五是為了使扶貧工作更貼合實際,對新型市場扶貧模式進一步創新。
參考文獻:
[1] 蔡昉,陳凡,張車偉. 政府開發式扶貧資金政策與投資效率[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01,20(2): 60-66.
[2] 朱乾宇. 我國政府扶貧資金使用的績效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16): 37-39.
[3] 汪三貴,郭子豪. 論中國的精準扶貧[J].貴州社會科學,2015(5): 44-44.
[4] 公衍勇. 關于精準扶貧的研究綜述[J].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學報,2015(3): 75-78.
[5] 李博. 項目制扶貧的運作邏輯與地方性實踐——以精準扶貧視角看A縣競爭性扶貧項目[J].北京社會科學,2016(3):106-112.
[6] 李國治,朱曉蕓. 農村精準扶貧的問題與對策[J].山西青年,2016(19): 213.
作者簡介:1.應澤華,(1987.3—),男,江蘇蘇州人,碩士。研究方向:技術經濟管理
2.黃東兵,(1962.3—),男,貴州省貴陽人,博士,貴州財經大學管科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技術經濟管理。
基金項目: 貴州省科技計劃項目“基于大數據私有云的精準扶貧機制研究”(黔科合基礎20161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