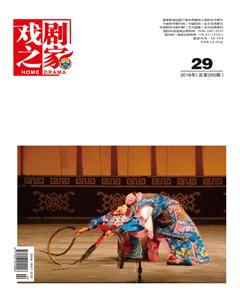在孤獨的自由中回歸偉大的平凡
李延芳 韓志強-
【摘 要】存在主義是一種西方現代哲學,在多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將存在主義理念蘊涵在電影中,電影的主旨便擁有了表達個體思考與陳述痛苦情感的哲學色彩。電影《將來的事》講述了一名哲學教師娜塔莉在遭遇了一系列打擊之后重新找回存在價值的過程。通過對娜塔莉這一角色的塑造,揭示了個體在生存過程中的意義,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關照下的個體生存價值。本文在存在主義視域下,探討片中所蘊含的哲學觀念,進而品析作品主題中對人的個性、生存意義、自由與平凡人生的思考。
【關鍵詞】存在;荒誕;選擇;自由;責任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29-0078-02
電影《將來的事》是由米婭·漢森·洛夫執導,伊莎貝爾·于佩爾、安德烈·馬孔等主演的劇情片。該片講述了一位哲學老師娜塔莉人到中年,看似美好平靜的生活被打破,遭受丈夫出軌離異、母親去世、出版被拒等一系列打擊后獲得了突如其來的自由,最終在迷茫、痛苦和逃避之后選擇了回歸生活的本質,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找尋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
“存在主義哲學思潮的廣泛流行,源于二戰后人們經歷戰爭從而思索個體生存的意義和責任。”《將來的事》集中表現了一名普通哲學教師的現實生活及其真實思想,正如存在主義哲學對個人的存在的強調,尤其是對人精神世界的哲學解析。從將“人”作為思考核心的角度來看,二者都體現了人道主義關懷,這與現代人自我意識愈加強烈、對自身研究的重視及其多維度發展的趨勢相契合。本文通過探討影片中蘊含的存在主義哲學理念,分析主人公行為及心理變化以揭示其個性,娜塔莉的克制、隱忍、自尊以及在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由所帶來的失重感中的暫時迷茫,在遭遇了一系列打擊之后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過程都可以在存在主義視域下加以詮釋。
一、直面荒誕的理性視角
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認為:“世界的陌生性,失去了我們賦予它幻想的含義。世界的這種厚度和陌生性,就是荒誕。”①存在主義者認為人之悲劇在于,懷揣希望的人面對這個荒誕的世界往往會變得不知所措、失落彷徨。《將來的事》在場景設置中每一天都是晴天,主人公經歷的灰暗與明亮世界的表征形成了極大的反差,產生了一種荒誕的呈現狀態。存在主義者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它的存在不會因為人的痛苦抑或失望而有絲毫的改變。在影片里學生們集會吶喊,用激進的方式企圖改變當權者的政策。娜塔莉不愿談論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她在課上引用的盧梭的話表明了其理性的態度:“如果神的臣民果真存在,他們便可以用民主制來治理,但如此這般完美的政府,并不適合于凡人。”
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娜塔莉的世界經歷了種種荒誕之事,但她沒有挽留,沒有歇斯底里,而是用理性的態度面對這一切。娜塔莉堅持自己的信念與原則,保持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對于作品的尊重,婉拒了出版商的不合理要求;保持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尊嚴,與離開的丈夫、觀念不符的學生訣別。她與書為伴,企圖在哲學中尋找這荒誕世界的出口,以理性的視角直面荒誕。
二、與他人共在的孤獨狀態
在影片的開始,娜塔莉課件中有一句話“人能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娜塔莉的母親有一定的精神障礙,不分晝夜以自虐的方式求得關注,如一周打三次電話給消防員,進入焦慮狀態就叫救護車,每天打無數個電話給娜塔莉,使她隨時都可能停止自己的生活去看望母親。疲憊不堪的娜塔莉只得把母親送到養老院,希望這是對母親最好的決定。而母親對此是極為抗拒的,絕食、不邁出自己的房門,她無法適應孤獨,最終溘然離世。母女之間都沒有站在對方的角度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悲劇發生的原因,也間接呈現了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在《禁閉》中提出的“他人即地獄”的觀點。
每個人在“自為的存在”中是絕對自由的,會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彼此相異,只能孤獨前行。從影片中的幾次家庭辯論中可以看出,貌似與娜塔莉精神高度契合的丈夫漢斯,實則持有不同的哲學觀點,映射了他們不同的人生觀。影片中多次出現,娜塔莉孤身一人的鏡頭。通過這些鏡頭語言呈現了人生的常態即孤獨,孤獨感也是存在主義哲學表述的重要觀點:人生而孤獨,也將孤獨而終。
三、自由選擇中的人生責任
薩特認為存在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承擔責任的絕對性質”。作為哲學家的漢斯早已看穿婚姻利益的本質,他在自由意志的主導下選擇追求愛情,搬去和新女友開始新的生活。與此同時他也需承擔自由選擇的后果與責任,孤身一人度過圣誕節,兒孫圍坐一堂的歡樂溫馨、妻子親手做的烤雞都與之無緣。在生下孩子的產房中,看著自己的父母互相揶揄,女兒克洛伊哭了起來,此刻的她后悔當初選擇戳破父親的偽裝,破壞了原本看起來平靜美好的家庭。這與存在主義中做出了選擇就必須承擔其帶來的痛苦與不安的觀點相吻合。
在薩特看來,我們努力的目標與終極價值應該是增進個人自由,即增進個人的具體選擇的可能性。然而,在大眾社會普遍要求淺薄與服從的社會經濟壓力下,我們往往喪失對身份和意義的追求。娜塔莉雖然在哲學思想中獲得了慰藉與精神獨立,但是她很少主動為自己做出選擇,而是如信徒般接受自己的境遇。娜塔莉去法比安的山間莊園小住,實則是對現實狀態的一種逃避,正如法比安尖銳指出的她的墨守陳規、她對于改變的畏懼。
即使畏懼但她仍對自己的人生秉持著負責任的態度。面對丈夫坦言出軌后用送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安,圣誕節求收留,娜塔莉都一一果斷拒絕,保持了自尊和獨立。離婚之后,娜塔莉選擇了與書為伴,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存在,保持與法比安亦師亦友的關系,拒絕了電影院中強吻她的陌生男子。
四、身份剝離與存在意義
丈夫搬去和新女朋友住,娜塔莉沒有挽留,決絕地剝離妻子的身份;母親突然離世,娜塔莉不再被依賴,失去了女兒的身份;孩子們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生活,娜塔莉暫時告別了母親的身份;在山間與法比安告別,更早的當她被法比安尖銳的話語戳穿時,娜塔莉已不再是導師;把母親留下的黑貓送出去,主人的身份也被剝離。最終孑然一身,此時已經拋開了生活的一切意義,剩下存在的本質與無盡的自由選擇。但同時,她又處于極度的矛盾中,生活可以被拯救或是重啟嗎?
在娜塔莉母親腳下待了十年的潘多拉一旦回歸山間立刻溜了出去尋找自由,娜塔莉對他的呼喚和擔憂正如對此刻的自己一般,擔心在這前所未有的自由生活中迷失,找尋不到存在的價值,這是社會人在重歸自然時無法適應的悲哀。影片里娜塔莉不斷告別,不斷剝離身份的過程,正是對個人存在的探求和重構。存在主義先驅克爾凱郭爾認為人的生存問題唯有人的主體性自身解決,而不是依托客觀真理。娜塔莉作為哲學老師,卻無法用哲學的理性來面對情感的波動。只有這一次次的剝離和告別之后,她才尋得自己的存在價值,不為任何人而活。
在影片的最終,經歷了意外降臨的自由之后的娜塔莉選擇回歸生活的本質,承擔責任,找尋到了生存的真正意義——告別從前的一切,承擔起老師的責任,教書育人,用哲學的智慧光芒啟迪學生;影片定格于已經作為祖母的娜塔莉抱著嬰兒沉浸于圣誕節的團圓氛圍里,在經歷了生命的孤獨與荒謬,她最終懷抱新生命迎來自己的新生活,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
注釋:
①[法]加繆(Camus).西緒福斯神話[M].新星出版社,2011.
參考文獻:
[1]朱斌,胡凡剛.《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存在主義視閾下的生存意義[J].影視制作,2017,23(11):82-86.
[2]唐玉婷.《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的存在主義解讀[J].電影評介,2016(01):68-70.
[3]田麗玲.存在主義視域下解讀《奇幻森林》[J].電影文學,2016(18):136-138.
[4]苗蕾蕾.王家衛電影中的存在主義美學呈現[D].安徽大學,2014.
[5]趙婧薇.第六代電影中的存在主義[D].南京師范大學,2015.
[6][法]讓-保爾·薩特(Jean-Paul Sartre)著.存在與虛無[M].三聯書店,1987.
[7][法]薩特(Sartre).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