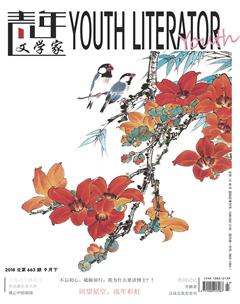從科學走向美學的深處
摘 要:科幻小說的誕生和發展伴隨著現代實驗科學的發展,經過了科技大爆炸的催化,與科學反思的影響。美學自律和審美現代性對社會現代性的反叛直接反映在科幻小說當中。當科幻小說發展成為一個有獨立審美性的小說類型時,他已經自覺地從科學主義走向了美學的深處。
關鍵詞:科幻小說;科學主義;美學回歸;審美現代性
作者簡介:葛虹局,重慶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講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7-0-02
科幻小說作為一個獨立的小說類型在文學史中有其重要的意義。它的發生、發展、獨立、完善經過了一個短暫激烈的過程,至今它的出現不過180年左右,對大多數主流文學形式來說,這一時間段僅僅足夠題材的展開,而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與成熟完善的理論構建還是一個頗為遙遠的目標。科幻小說并非一種趣味性的迎合潮流的消遣文學,它在過去、現在、未來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并伴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為其誕生的根源——科學技術,是一種確信無疑的實質,是可以應用的,可以實現的,可以重復的,理解世界的手段。古代的神話傳說與英雄史詩,它們流傳了數千年,在一段時期內甚至被當做真理的承載和世界的模范。而科幻小說未嘗不是另一段神話,它不是用神,而是用科學來解釋世界,它誕生于一個新的時代,科學的時代。人們不再依靠神靈,而是依靠科學來掌握世界。科幻小說的繁榮與其重要的意義便不言而喻了,它是最直接的觸及新世界本源的文學形式。在這一小說類型的發生與發展過程中,無疑緊密跟隨這一新時代的本源的發展道路。而它的成形也反映著科學帶來的人類思維范式的轉化與巨變。在科幻小說的發展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科學在文學領域的構建、沖突、妥協、融合。
一、科學的萌芽,于未知的迷霧中若隱若現
理論界普遍認同的第一部科幻小說是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在1818年發表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雖然這一說法在現代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但我們仍可以認為它明確地引進了科學幻想的元素,甚至它創造了一個頗為有名的科幻名詞:“科學怪人”。故事在傳統的善與惡的主題上引入了新的對象,一個人類用科學創造的怪物,它匯聚了人與非人,生與死,丑與美,愛與恨等一切矛盾的特質,最后回歸于毀滅。這篇小說籠罩在陰郁的氛圍之下,黑夜、暴風雨、謀殺、尸體……各種令人恐懼的元素結合在一起,讀這篇小說就像在一片黑暗的迷霧中尋找危險的野獸,隨時緊繃的神經使我們疲倦又緊張。科學的元素在這種神秘而陰郁的結構當中若隱若現,用生物科學與電化學制作出的“怪物”,與其說是一項科學實驗,不如說是一場神秘的召喚儀式,比起科學,它更像是魔法。
19世紀初,正是現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時期,人們普遍了解了科學這一手段可以讓我們認識世界,但神學的殿堂仍照耀著信仰的輝光,除了上層的貴族與知識分子,民眾對于科學的感受就如同巫師才能掌握的魔法,他們不知道科學能夠做到什么,又究竟會帶來什么。這時的科學在文學作品中以一種具有神秘主義或預言性質的“魔法”存在著,它多數時候只是一種新奇的元素,或是使故事合理化的前提條件。如同《弗蘭肯斯坦》,它可以說更像是一部集恐怖與偵探于一身的哥特小說。而科學元素在其間扮演了一個不甚體面的角色,它帶來了怪物與殺戮,有一種幕后大反派的遮遮掩掩的腔調,正體現出了當時人們對于科學的看法:少數人掌握的特權與魔法,是好是壞還無法分辨。在這一類文學作品中,科學技術以一種神秘主義的方式出現,多數只能算是一種幻想元素。它隱于迷霧之中,時不時顯露出身體的一角,又迅速隱沒,如同捉迷藏的游戲,我們總是很難抓住它的身影。
二、初創的熱情,于頌歌中建起新的神壇
19世紀,人類開始全面進入科學技術為主導的時代。各種科技發明層出不窮,人們逐漸脫新離了舊的神學思想的統治,開始觀看這個新的因科學而引起巨變的世界,科技發明充斥在我們的周圍,世界的模樣以一種純物質或純物理的形態于我們的頭腦中重新構建。籠罩科學的迷霧散去,它以一種充滿樂觀主義的精神態度登上了時代的舞臺,并領導世界的走向。文學作品中的科學元素終于脫去了神秘主義的外衣,以主人的態度介入其中。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具代表性的兩位科幻作家為科幻小說真正的奠基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儒勒·加布里埃爾·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他以其大量著作和突出貢獻,被譽為“科幻小說之父”。由于凡爾納知識非常豐富,他小說作品的著述、描寫多有科學根據,所以當時他小說的幻想,如今成為了有趣的預言。其著名的作品《海底兩萬里》(20,000 lieues sous les mers,1873)中的巨型潛水艇“鸚鵡螺號”便是其杰出的科學猜想的成果。“‘鸚鵡螺號兩端呈橢圓形,身體呈細長的圓筒形。……當這十分之一都裝滿了水以后,船就會完全沉沒在水面下,這便是其中的潛航原理裝置。”從純粹科學性的角度來看,這種水下潛艇在現實中也是可以完全達成的。而事實上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現代潛水艇就是如此模樣。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英國著名小說家。如果說凡爾納開啟了科幻小說的大門,那么英國人威爾斯則長驅直入、開疆拓土,指出了后世科幻作家可以繼續探索的多數道路。20世紀科幻小說中幾大主題,如“時間旅行”、“外星人”、“反烏托邦”等等,都是威爾斯所開創的。威爾斯善于把科學知識通俗化,并通過小說將其突出出來,正是這種才能使他的科幻小說深受讀者歡迎。
科學技術在當時很多的科幻作品中都以一種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它征服了時間與空間,生命與宇宙,未來似乎便存在于它的無限發展的偉力之中。這種解釋世界、掌控世界的方式,比起神的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更加深得人心,因為它是可以被人類所利用的。人們熱情地投身于這種新的力量,使之成為新的信仰,高筑神壇。科學主義的思想在文學作品中占據了主導,不再附庸于幻想和恐懼,它獨立出了新的主題與題材,科幻小說于文學的大流中分離出來,開始了自身的旅程。
三、繁榮的盛景,于成熟的深沉中閃現自省的靈光
20世紀初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幻小說進入了“黃金時代”,這是科幻小說繁榮發展,根深葉茂的成長成熟時期。20世紀30年代,科幻文學商業化大潮在美國興起的,涌現了一大批風格鮮明的科幻雜志。這些雜志也成了推動美國科幻小說發展的主要動力。最著名的有《奇異傳說》(Weird Tales)、《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新奇故事》(Astounding Stories/《新奇科幻》 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奇幻與科幻小說雜志》 (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銀河科幻》(Galaxy Science Fiction)。
科幻史一般公認,約翰·坎貝爾是美國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領導者。他的雜志《新奇科幻》聚集了當時幾乎所有的美國科幻大家:以撒·艾西莫夫、斯普雷格·杜岡、羅伯特·海因萊茵、雷·布萊伯利、范·沃格特……等等。Astounding SF致力于讓科幻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嚴肅”地出現在讀者面前:“首先必須來自真正的科學,同時,也必須是真正的歷史,”且不能兩者居其一。這樣,科幻小說中人文和科學的真實性都得到了加強。如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美國科幻小說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基地”系列創造了一部跨越千萬年的龐大的銀河系帝國的興衰史。
“黃金時代”的科幻小說開辟了各種題材流派,許多著名的科幻主題都在這一時期形成了。比如太空歌劇(Space Opera,或稱“宇宙史詩”)、賽博朋克(cyberpunk)、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人工智能、時間旅行等等。硬科幻與軟科幻的分類也在這一時期出現。專業性強,幾乎可以當做半個科普讀物閱覽的科幻小說被稱為硬科幻。而以科幻元素為背景,把人文關懷置于其上,更偏向于人文,技術含量不高的科幻作品為軟科幻。從軟科幻這一分類我們可以看出,科幻小說已經走向人性的回歸、生命的意義、宇宙的根源這些關系著人類命運問題的探索方向了。這是大部分文學作品關注的焦點,而因其人文、情感元素的增加,和題材結構等小說類型特點的成熟完善,其審美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強。科學技術有時候甚至只充當了一個背景,其上所演繹的故事已經深入了人類心靈的深處,激起情感的波濤、哲學的沉思。科幻小說的美學意義得到了發展與完善,它越來越向著獨立自律的小說類型前進。
四、多元化的融合,于回歸中掙脫舊的囚籠
經過了如火如荼的科幻“黃金時代”,人類進入了新的世紀交替時期,世紀末恐慌癥又卷土重來。科學技術帶來的災難不再只存在于科幻小說家們的臆測與猜想中,而是在現實世界滋生蔓延,以一種清晰明確、無可辯駁、無法忽視的姿態呈現在所有人面前。溫室效應、環境惡化、海洋污染、自然災害、物種滅絕、恐怖主義等等,世界以一種跳躍式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我們無法理解的時空,這個時空充滿了矛盾與悖論,科學也表現出一副扭曲的面孔,或是說人類的心靈扭曲了面孔。人類的思想情感與倫理道德在各種劇烈變化的沖擊之下顯得混亂、浮躁、焦慮、迷茫。對科學主義和社會現代化的反思成為了文藝界與思想界的主題,審美現代性作為反社會現代性、反工具理性的代表,在這個時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拯救人類心靈的鑰匙。科幻小說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向著美學回歸,以新的審美要求獲得了發展的空間,各種元素融合進來,不再局限于規定的題材與流派,而是盡可能地從多種角度解讀科學與社會,涌現出各種各樣的新的科幻小說形式,煥發出勃勃生機。
特德·姜(Ted Chiang)的科幻小說《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獲得了1999年的“星云獎”。這篇科幻小說以一種娓娓道來的平靜溫暖的敘事手法,為理性的科學融進溫情的生活態度,讀之使人仿佛漫步于散文的小徑,有藍天、白云、青草、微風。不管是“語言”這個創意帶來的驚奇感與陌生化,還是敘述過程的真情流露,都顯示出不同以往的游刃有余的自由度。科幻小說漸漸脫離了固定化的藩籬,向著更成熟的審美形態過度,進入了更廣闊的天空。
科幻小說誕生于科學主義的時代,它標志著一種新的解釋世界的方式成為了人類思維范式的主導,它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出科學的發展脈絡。但科幻小說是屬于文學的,它處于藝術的領域之中,當對于科學的反思逐漸深入,當審美救贖的要求愈加緊迫,它便自然回歸于美學,完成它的獨立自主的任務。科幻小說從科學主義出發,最終走向了美學的深處。
參考文獻:
[1]張法. 美學概論[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
[2]董學文. 西方文學理論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亞當·羅伯茨.科幻小說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