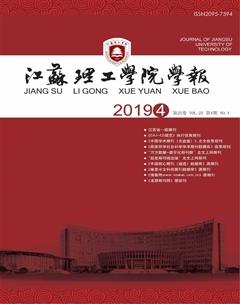江蘇省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研究
時大紅 謝忠秋



摘? ? 要:我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江蘇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第一方陣之省份,高質量發展是其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也對我國整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選取6個一級指標、35個二級指標構成江蘇省高質量發展的測度體系,運用“變異系數-主成分評價”方法,生成各指標權重,構建起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模型,對江蘇省13個地級市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通過分析測度結果發現,盡管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處于高水平,但其在高質量發展方面表現得并不盡如人意,而且各地市之間發展的差距較大。因此,江蘇需要借勢“一帶一路”交匯點建設,借機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和借力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重大機遇,在促進與更大區域的開放、融合、協作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提升高質量發展水平。
關鍵詞:江蘇;高質量發展;測度
中圖分類號:F062;X820?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5-7394(2019)04-0023-06
目前,江蘇省經濟發展已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總體發展水平居全國各省(市)前列。2017年,江蘇省人均GDP約為15 876美元,高于世界銀行同期發布的高收入標準[1]。因此,江蘇未來的發展已經站在了一個“高起點”上,但是“高起點”并不意味著“高質量”。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江蘇如何在“高起點”上實現發展的“高質量”,將是該省未來發展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對于區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研究,目前國內還處于起步階段。沈坤榮(2018)、李蕓(2018)等以江蘇為例對區域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進行了研究[2-3]。江三良(2018)對長三角地區高質量發展進行了研究,指出對外融合比開放更能夠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4]。劉國斌(2019)指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區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5]。詹新宇(2016)基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2000—2014年中國各省(市)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了評價[6]。師博(2018)通過構建基于經濟增長基礎面和社會成果兩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對1992—2016年中國省際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評價[7]。這些研究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1? ? 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所謂高質量發展是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的多維度協調發展,表現為質量更好、結構更優、效率更高、惠及更廣。其中,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開放是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以人為本發展的本質要求。此外,表現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上,還要講究高效,即高效率和高效益,它又成為發展應追求的基本目標。以上六個維度的發展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構成高質量發展的有機整體,從而不斷推動經濟與人、經濟與社會、經濟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
2? ? 測度模型的構建
依據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遵循指標體系構建的全面性、科學性、實際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原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有效”六個維度,選取了6個一級指標、35個二級指標;利用變異系數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取兩種方法所得權重的算術平均數作為各級指標的最終權重,從而構建了江蘇省高質量發展測度模型,如表1所示。
3? ? 測度結果及分析
3.1? 測度結果
測度對象為江蘇省管轄的13個地級市。相關數據均來自各市2018年的統計年鑒,及2018年江蘇統計年鑒。運用江蘇省高質量發展測度模型(表1)對2017年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指標數據進行處理,得到各市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及各維度綜合指數(見表2)。
3.2? ?結果分析
3.2.1江蘇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總體分析
從表2可見,江蘇13個地級市高質量綜合發展指數的均值僅為34.40%,低于50%的水平,表明江蘇省高質量發展的總體水平不高。其中,徐州、鹽城、揚州、泰州、鎮江、淮安、連云港、宿遷8個地級市的綜合發展指數低于全省平均值;蘇州市的綜合發展指數最高,為79.50%,宿遷市最低,僅為20.89%,兩者差值高達58.61個百分點;13個地級市綜合發展指數的離散系數高達47.18%。這些數據均表明,江蘇13個地級市之間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水平差異較大。
從六個發展維度的測度結果看:(1)協調發展指數的均值最高,但也僅為52.78%,其余五個發展維度的測評均值都在50%以下,開放發展指數的均值低至20.16%。江蘇高質量發展的現狀顯然與其在全國省域發展中所處的領先地位極不相稱,也表明江蘇發展從高起點向高質量的轉型道遠且阻。(2)從離散系數看,六個發展維度中有四個維度的離散系數大于綜合發展指數離散系數;協調發展指數的離散系數最小為37.32,開放發展指數的離散系數最大為131.65,其余由大到小依次是創新發展指數、高效發展指數、綠色發展指數和共享發展指數。如此之高的離散系數再一次凸顯出江蘇13個地級市之間各維度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3.2.2江蘇各地級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的空間分布
根據江蘇各地級市高質量綜合發展指數(表2),以該指數值35%和25%為參照,將江蘇13個地級市高質量發展劃分為由高到低三個層次。高于35%,即高于全省平均值34.40%的為第一層次,屬于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市,分別是蘇州、南京、無錫、南通、常州;介于25%到35%之間的為第二層次,屬于高質量發展水平一般的地市,分別是徐州、揚州、鹽城;小于25%的為第三層次,屬于高質量發展水平較差的地市,有泰州、鎮江、淮安、連云港、宿遷。特別要說明的是,此處分類是個相對的概念,目的在于方便比較研究。從空間分布來看,第一層次地市主要集中在蘇南地區,第二、三層次的地市主要分布于蘇北和蘇中地區。由此可見,區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高低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4? ?推動江蘇高質量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的對策建議
近年來,我國政府陸續推出了“一帶一路”發展重大倡議、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國家戰略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而江蘇正是這一大倡議、兩大戰略的交匯疊加省份,這不僅使得江蘇的高質量發展具有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更使得江蘇的高質量發展具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為此,江蘇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另一方面更要好好地利用這得天獨厚的優勢,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走在全國前列。
4.1? 借勢“一帶一路”交匯點建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江蘇要站在國家大力提高開放水平的高度,借“一帶一路”發展重大倡議這一探索全球經濟治理新模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勢,通過“一帶一路”交匯點建設,進一步擴大江蘇城市創新體系的開放度,促進江蘇與世界各國在引資、引智、引技等方面更深層次的交流和合作,不斷強化和優化江蘇在全球范圍內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為實現江蘇高質量發展提供創新驅動支撐。通過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務實合作,以大項目建設積極推動江蘇參與中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構建,爭取在金融合作、經貿投資、人文交流、基礎設施等領域取得實質性的更高程度上的突破,為江蘇高質量發展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全球城市網絡資源和國際環境。
4.2? 借機“長江經濟帶”協同發展,進一步提升綠色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水平
對于長江經濟帶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4月26日下午主持召開的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需要正確把握好5個關系:即“第一,正確把握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全面做好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工作。第二,正確把握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探索協同推進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新路子。第三,正確把握總體謀劃和久久為功的關系,堅定不移將一張藍圖干到底。第四,正確把握破除舊動能和培育新動能的關系,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第五,正確把握自身發展和協同發展的關系,努力將長江經濟帶打造成為有機融合的高效經濟體。”為此,江蘇要深刻領會,并以此為引領,將綠色發展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普遍形態,堅持生態優先,增強各項措施的關聯性和耦合性,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統一;將推動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轉變作為中心,實現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相統一;將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動力轉換作為關鍵,徹底摒棄以投資和要素投入為主導的老路,實現新動能和新經濟體系相統一;將江蘇打造成為引領全國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作為一種責任,樹立“一盤棋”思想,錯位發展、協調發展、有機融合,形成整體合力,實現自身發展和協同發展的相統一,以進一步提升綠色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水平,從而奮力寫好推動江蘇高質量發展走在全國前列的新篇章。
4.3? 借力“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加快形成更高能級的創新體系和產業體系
以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為契機,深度參與G60科創走廊建設,推動蘇州對接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以制定重大科技專項扶持配套政策為著力點,對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通信、航空發動機等重點方向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攻克“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形成核心技術創新體系,提升重大前沿技術源頭創新能力;打造蘇州園區建設品牌,支持上海虹橋蘇州(相城)數字經濟創新產業園、臨港常熟科技產業園建設,支持蘇滁現代產業園、中新蘇嘉現代產業園發展,加快先行啟動區與上海的全面深度融合,優化嘉昆太、青昆吳和環淀山湖等戰略合作機制,促進吳江等臨滬地區深入對接上海,并以產業園區為基點,推動新興產業擴容增效,推進園區拓展功能、提升能級,以形成更高能級的產業體系,從而為江蘇高質量發展提供高質量的產業支撐。要主動加強與長三角兄弟省市的合作,有效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建設,不斷提高一體化程度。
參考文獻:
[1] 江蘇省人民政府.江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形勢、現狀和重點任務[EB/OL].(2018-10-31)[2019-06-22].http://www.js.gov.cn/art/2018/10/31/art_34153_7859218.html.
[2] 李蕓,戰炤磊.新時代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的新格局與新路徑:以江蘇為例[J].南京社會科學,2018,12(12):50-57.
[3] 沈坤榮,趙倩.世界級城市群國際比較與區域高質量發展路徑選擇:以江蘇為例[J].江海學刊,2018,4(2):102-238.
[4] 江三良,趙夢嬋.新時代對內融合與對外開放再考量:以長三角區域高質量發展的衡量為例[J].工業技術經濟,2018,12(8):124-131.
[5] 劉國斌,宋瑾澤.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J].區域經濟評論,2019,6(2):55-60.
[6] 詹新宇,崔培培.中國省際經濟增長質量的測度與評價:基于“五大發展理念”的實證分析[J]. 財政研究, 2016(8):40-53.
[7] 師博,任保平.中國省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與分析[J].經濟問題,2018,12(4):1-6.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changing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Jiangsu, as the first provinc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six first level indicators and 35 second level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to form the measurement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Using the method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 principal component evaluation”, the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is generated, and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13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is at a high level,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is not satisfac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cities is large. Therefore, Jiangsu need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tersection construction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jor opportun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Key? words: economic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coefficient of variation;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composite index
責任編輯? ? 王繼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