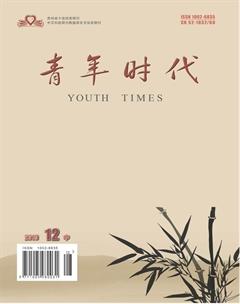《牡丹亭》兩個英譯本中典故翻譯的對比研究
向鵬
摘 要:本文在分析典故的定義、分類和特點的基礎上,通過舉例,從典源、典面和典義三要素的角度對比分析了《牡丹亭》兩個英文譯本中典故的翻譯。研究發(fā)現(xiàn),伯奇譯本在典故翻譯時多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力圖在翻譯中充分展現(xiàn)典故所蘊含的源語文化。汪榕培譯本多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讓譯文符合戲曲的舞臺表演性。
關鍵詞:《牡丹亭》;典故;翻譯
《牡丹亭》是有“東方莎士比亞”之稱的湯顯祖的代表作,是中國古典戲曲的巔峰之作。自從《牡丹亭》誕生以來,其動人的愛情故事及優(yōu)美的文字不僅讓無數(shù)中國讀者為之折腰,而且,當其傳播到國外后,也在外國讀者中獲得贊嘆無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牡丹亭》在國內(nèi)外已經(jīng)具有各類譯本二十多個,其中全譯本有三個,分別為伯奇、張光前和汪榕培的譯本。其中在國內(nèi)外影響較大是伯奇和汪榕培的譯本。在國外,伯奇的譯本受到了眾多知名漢學家的稱贊,宣立敦稱其為“里程碑式的翻譯”(Strassberg,1982);芮效衛(wèi)說伯奇譯本是“對杰作的杰出翻譯”(Roy,1982)。在國內(nèi),汪榕培譯本受歡迎的程度絲毫不亞于伯奇譯本,孫法理、郭著章、張政等都撰文評價過汪榕培的譯本。郭著章(2002:56)認為:“汪譯從整體上達到了‘傳神達意的目標,成為《牡丹亭》迄今國內(nèi)外最令人滿意的英文全譯本。”在本文中,我們將對比分析兩個譯本對《牡丹亭》中典故的翻譯,看看兩個譯本是如何處理典故這個翻譯中的難題的。
一、典故的定義及特點
(一)典故的定義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給典故給出了不同的定義。葛兆光(1989:20)在“論典故——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種特殊意向的分析”一文中是這樣界定典故的:典故乃是一個個具有哲理或美感內(nèi)涵的故事的凝聚形態(tài),它被人們反復使用、加工、轉(zhuǎn)述,而在這種使用、加工、轉(zhuǎn)述過程中,它又融攝與積淀了新的意蘊,因此它是一些很有藝術感染力的符號。葛兆光將典故視為一種藝術符號,視角非常新穎。不過葛兆光將典故局限在“具有哲理或美感內(nèi)涵的故事”顯然是將典故的范圍局限在了“事典”之內(nèi)。這樣的定義并不完整,因為除了“事典”外,還有“語典”。相比較而言,《辭海》給出的定義更為全面。《辭海》給出了“典故”一詞的兩層含義:一指典制和掌故;一指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夏征農(nóng)、陳至立,2009:453)。文學中所討論的典故通常是指第二層意思。羅積勇在典故研究的專著《用典研究》中對典故的定義是:為了一定的修辭目的,在自己的言語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來歷的現(xiàn)成話,這種修辭手法就是用典(羅積勇,2005:2)。羅積勇的定義強調(diào)了典故運用的目的和方式。到目前為止,雖然視角和偏重各有不同,不過研究者在“典故指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來歷的詞語”這一點上已經(jīng)達成了共識。《辭源》(1981)、《漢語大詞典》(1988)和《現(xiàn)代漢語詞典》(2005)都采用了這一定義。
(二)典故的特點
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符號,典故有其自身的有特點。首先,就其結(jié)構(gòu)而言,典故包含典源、典義和典面三個基本的要素。這三個要素對于典故的理解至關重要。北京師范大學王寧教授認為,典故的研究就應該從典源、典義和典面入手(見羅積勇,2005:34)。所謂典源就是典故的來源、出處;典義就是典故表達的意思;典面就是相對固定的典故的文字表達形式。其次,就其語法特點而言,典故多為合成詞或熟語,單音詞不能構(gòu)成典故。再次,就其語義特點而言,典故類似于成語,其意義往往是約定俗成的,不能簡單地通過字面意思的相加來猜測整個典故的意思。如果按字面意思來理解典故,往往就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要正確理解典故的意義,不但要追根溯源,找到典故的最初出處,還要結(jié)合典故運用的具體語境,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典故的意思。最后,典故是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的,因而典故帶有強烈的民族文化色彩。通過典故,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典故翻譯研究
正是由于典故具有上面提到的這些特點,典故翻譯歷來就成為了翻譯實踐中的一大難點。不過,對大多數(shù)研究者而言,典故翻譯的難度恰恰是典故翻譯的魅力所在之處。因此,研究者們紛紛從不同的視角對典故翻譯進行研究。
在中國知網(wǎng)中,以“典故”翻譯為題進行模糊檢索,一共檢索到文獻241條,最早的文獻是1982年錢維藩發(fā)表在《外國語》上的“希臘羅馬神話典故及其翻譯”。當然,這里統(tǒng)計到的文獻都是“專論”典故翻譯的文獻,“兼論”的文獻肯定會更多、更早。除此之外,大部分翻譯教材都會涉及典故的翻譯。由此觀之,典故翻譯是翻譯實踐研究中的熱門話題。
縱觀現(xiàn)有的研究文獻,典故翻譯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
第一,探討典故翻譯的方法及各種翻譯方法的優(yōu)缺點。這方面的文獻占了典故翻譯研究文獻的大部分。例如,錢維藩(1982)提出了典故翻譯的四種翻譯方法:放棄原文典故、解釋性翻譯、加注翻譯和套用對應典故翻譯。除了這四種翻譯方法外,直譯、意譯和音譯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典故翻譯的討論中。在討論典故翻譯方法時,譯者應該采用直譯還是意譯,是否要加注成為了討論的焦點。贊成直譯或贊成加注者認為這樣翻譯能幫助讀者了解源語文化,反對者認為直譯不便于讀者理解,加注會影響讀者閱讀的流暢度。例如,A.C.格雷厄姆(1982:233)就認為:“也許用一條注解來耽誤讀者的時間,還不如讓它匆匆地走過為好。”
第二,中外各種經(jīng)典作品中的典故翻譯研究。考察中外各種經(jīng)典作品中的典故翻譯也是典故翻譯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研究經(jīng)典作品中的典故翻譯對典故翻譯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這些經(jīng)典作品不但本身就是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文學精品,值得我們研究學習,同時經(jīng)典作品往往會產(chǎn)生杰出的譯作。這些杰出的譯作就是翻譯研究和學習的最好的材料。從現(xiàn)有的典故翻譯文獻來看,涉及較多的中文經(jīng)典作品有《紅樓夢》《圍城》《聊齋志異》、各種詩詞等;涉及較多的外文作品有《圣經(jīng)》、莎士比亞作品、希臘羅馬神話、《尤利西斯》等。
第三,從各種現(xiàn)代翻譯理論的視角來研究典故翻譯。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已經(jīng)擺脫了過往的那種經(jīng)驗式和感悟式的研究范式。當今的翻譯研究已經(jīng)不滿足于翻譯方法和技巧的討論,翻譯研究的理論性得到了加強。當今的翻譯界可謂是學派林立,理論層出不窮。這一點同樣反映在了典故翻譯研究中。研究者們紛紛運用各種理論來研究典故翻譯。其中用得比較多的理論有關聯(lián)理論、文化學派的理論、目的論、順應論、互文性理論、文化圖式理論等。這些理論視角的介入增強了典故翻譯研究的理論性,帶來了不同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三個方面的研究往往并非是各自獨立的,相反,這三個方面的研究經(jīng)常是融合在一起的。
三、《牡丹亭》中的典故翻譯
湯顯祖在《牡丹亭》中用典頗多,豐富的典故可謂是《牡丹亭》最典型的語言特色之一。正是由于大量使用典故,造就了《牡丹亭》文字簡練、語言瑰麗的特點。那么,作為公認的杰出譯作的伯奇譯本和汪榕培譯本是如何翻譯《牡丹亭》中的典故的呢?兩者的翻譯有何異同?下面,筆者將通過舉例來對比分析兩個譯本中典故的翻譯。
例1.原文:謾說書中能富貴,顏如玉,和黃金哪里?貧薄把人灰,且養(yǎng)這浩然之氣。
伯奇譯文:
“In books lie fame and fortune.”They say—
then tell me,where are the jadesmooth cheeks,
the rooms of yellow gold?
Ashen from need and hardship
I yet maintain my “overflowing breath”.1
(1.The quotation from Mencius, which originally seems to have referred to some kind of yoga technique, here indicates scholarly purpose.)
汪榕培譯文:
The saying goes that studies bring the wealth,
But where is pretty lady
And where is gold?
Although wretched poverty may discourage me,
I am as honest as of old.
這里的原文出自《牡丹亭》第二出開篇的唱詞《真珠簾》。在這兩句唱詞之中,一共有三個典故:“顏如玉”“黃金(屋)”和“浩然之氣”。這三個典故皆為語典。其中“顏如玉”和“黃金(屋)”源自宋真宗趙恒的《勸學詩》中的“書中有女顏如玉”和“書中自有黃金屋”;“浩然之氣”出自《孟子·公孫丑》中的“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在伯奇的譯文中,三個典故皆為直譯,分別翻譯成了jadesmooth cheeks、rooms of yellow gold和overflowing breath。雖然皆為直譯,伯奇的譯文對三個語典的處理并不一致,“浩然之氣”的翻譯overflowing breath加上了引號,并且加了一條注釋,標明了該典故的出處。而汪榕培的譯文中三個典故皆為意譯,分別翻譯成pretty lady、gold和as honest as of old。三個典故的翻譯都沒有用引號標明引用,也沒有添加注釋。從“典源、典面和典義”三要素的角度來分析,伯奇譯文中的“顏如玉”和“黃金(屋)”翻譯出了典面和典義,沒有指出典源;在“浩然之氣”的翻譯中,伯奇譯文很好地將典源、典面和典義都表達出來了。在汪榕培的譯文中,三個典故都只翻譯出了典義,而沒有翻譯出典源和典面。如果僅從典故信息的傳達的角度而言,伯奇的翻譯無疑要優(yōu)于汪榕培的翻譯。不過,《牡丹亭》是戲曲,戲曲的翻譯還要考慮是否適合表演。像伯奇譯本加注的做法顯然不適合戲曲表演。所有,兩個譯本各有偏重,各有特點。
例2.原文:中郎學富單傳女,伯道官貧更少兒。
伯奇譯文:Cai Yong,rich in learning,had one daughter only,Deng You,poor in office,lacked sons altogether3.
(3.Deng You,an honest and therefore poor official of the Jin Dynasty,disowned his son to save the life of his nephew in a time of rebellion.)
汪榕培譯文:Well learned,Cai Yong had a daughter of good fame;A poor official,Deng You lost his son but earned his fame.
本例中的兩個典故既為事典又為語典。說其為事典,是因為“中郎學富單傳女”指的是曾做過中郎將的東漢著名學者蔡邕,終身無兒,只有一個非常有才氣的女兒蔡文姬的故事;“伯道官貧更少兒”指的是河東太守鄧攸,遭遇石勒之亂時,為了保全侄兒,而丟棄了自己的兒子,從而無后的故事。說其為語典,是因韓愈在《游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唐》有詩兩句:“中郎有女能傳業(yè),伯道無兒可保家。”在此,對比分析一下兩個譯文的翻譯就非常有意思。同樣,從典源、典面和典義的三要素來分析,伯奇的第一個典故翻譯出了典面和典義,而第二個典故典源、典面和典義都翻譯出來了。而這次汪榕培的譯文兩個典故都翻譯出了典面和典義,都沒有標明典源。其次,從事典和語典的劃分來看,伯奇的翻譯顯然是依據(jù)事典中的故事,而汪榕培翻譯的顯然是語典,是依據(jù)韓愈的詩句在翻譯。那么,兩個翻譯哪個更恰當呢?在此,筆者認為,就這兩個典故而言,伯奇的翻譯要更勝一籌。因為熟悉《牡丹亭》故事的讀者都知道,在這個故事中杜寶一直因只有杜麗娘一個女兒,無兒子而深感遺憾。在古代社會中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說法。在封建社會中,沒有兒子來傳承家族血脈幾乎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大憾事。杜寶也不例外。在《牡丹亭》的故事中,杜寶曾多次言及少兒的遺憾。伯奇譯文中的only和lacked很好地傳達出了這種遺憾之情。因汪榕培的翻譯依據(jù)的是韓愈的詩,而韓愈的詩中這兩個典故是反用,前一個典故表達的是只要女兒有才,同樣能傳承家業(yè)的意思;后一個典故是對鄧攸為救侄兒而舍棄自己兒子這種大義的高度稱贊。據(jù)此,汪榕培的譯文表達出的是一種陳贊而非遺憾的情調(diào)。這樣的意思顯然與《牡丹亭》中杜寶的感情不一致。
例3.原文:杜母高風不可攀,甘棠游憩在南安。
伯奇譯文:Though I may not aspire to the noble standard of ancient Du Shi,“father and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yet may I take my ease here in Nanan as once Duke Zhao of Zhou beneath the sweetapple1.
(1.“Sweet apple”(gantang) is in fact used as a metaphor for a respected official,following the poem by this title in the Book of Songs,which is a eulogy of Duke Zhao of Zhou.)
汪榕培譯文:Although Du Shi exceeds me in esteem,Ive earned a good reputation in Nanan.
在此例中,同樣有兩個典故“杜母”和“甘棠”。“杜母”指的是東漢人杜詩在南陽做太守,受到當?shù)匕傩盏膼鄞鳎蛔鸱Q為“杜母”;“甘棠”指的是周代召公出巡,曾在甘棠樹下休息,因召公輔政期間政通人和,他深受人們愛戴,于是有人就寫了一首名為《甘棠》的詩來紀念召公。在伯奇的譯文中,第一個典故在文中加了一個解釋性的短語father and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第二個典故加了一個注釋,這樣很好地將兩個典故的典源、典面和典義翻譯出來了。在汪榕培的譯文中,兩個典故都只翻譯出了典義,而舍去了典源和典面。這里,兩個譯文各有優(yōu)劣。伯奇譯文雖然能忠實地傳達兩個典故的意義和文化蘊含,但顯得不夠簡練。原文兩行詩句,譯文翻譯成了四行,另外還加了一個長注。注釋可以提供文化背景知識,幫助讀者理解,但是也會影響閱讀的流暢度。反觀汪榕培的譯文,雖然典故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在翻譯中有所損失,但讀起來曉暢易懂,可謂真正做到了“傳神達意”。另外,伯奇將“杜母”翻譯成Du Shi,“father and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要么是將“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兩個典故糅合到了一起,要么就是將“杜母”的典故與“父母官”的說法混在了一起,并不是很準確。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Du Shi,the mother of his prefecture。
在《牡丹亭》的兩個譯本中,類似的典故翻譯的例子還非常多,在此筆者就不在多列舉。
四、結(jié)論
縱觀兩個譯本,筆者發(fā)現(xiàn)伯奇和汪榕培兩個譯本在翻譯《牡丹亭》中的典故的時候采用了不同的策略。伯奇譯本通常采用直譯來傳達出典故的典面和典義,用引號標明典故的存在。除此之外,對于一部分典故,伯奇還常常用腳注來傳達出典故的典源和解釋典故的典義。從翻譯的策略而言,伯奇譯本傾向的是異化的翻譯策略。汪榕培的譯本通常是采用意譯,舍去了典故的典源和典面,傳達出典故的典義。從策略上而言,汪榕培譯本傾向的是歸化的策略。從翻譯的側(cè)重而言,顯然伯奇譯本重在傳達原文的文化信息,幫助讀者了解中國的戲曲文化。而汪榕培的譯本更注重戲曲的表演性,其譯文更適合舞臺表演。總而言之,兩個譯本各有風格,各有優(yōu)缺點。兩個譯本中對典故的不同處理方式為研究者研究文化詞匯的翻譯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值得我們深入學習。
參考文獻:
[1]Roy,D.T.Review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Tang Xianzhu trans.Cyril Birch,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2,No.2,1982:702.
[2]Strassberg,R.Review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Tang Xianzu,translated by Cyril Birch,The Romance of the Jade Bracelet and Other Chinese Operas by Lisa Lu,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Vol.4,N0.2,1982:276.
[3]Tang Xianzu.The Peony Pavilion (Mudan Ting),trans.Cyril Birch,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4]Tang Xianzu.The Peony Pavilion,trans.Wang Rongpei,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5]陳望道.修辭學發(fā)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03.
[6]格雷厄姆.中國詩的翻譯[A].張隆溪.比較文學譯文集[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233.
[7]葛兆光.論典故——中國古典詩歌中一種特殊意象的分析[J].文學評論,1989(5):20.
[8]郭著章.談汪譯《牡丹亭》[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8):56-59.
[9]羅積勇.典故的典面研究[J].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4):34.
[10]羅積勇.用典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2.
[11]錢維藩.希臘羅馬神話典故及其翻譯[J].外國語,1982(2):10-17.
[12]夏征農(nóng),陳至立.辭海(第六版)[Z].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