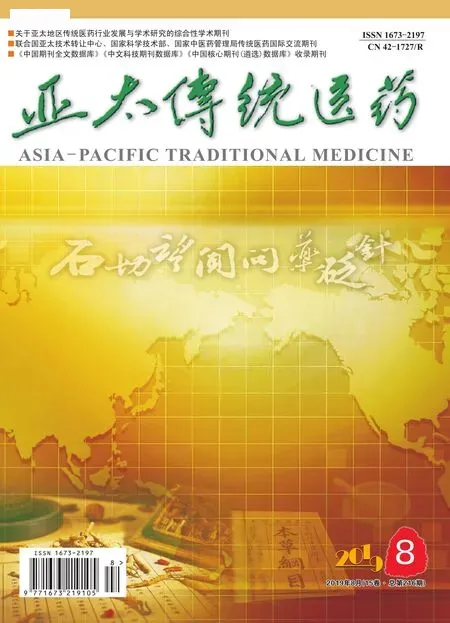從臟腑論治索拉非尼的皮膚毒性
朱金霞,高萍
(1.河南中醫藥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0;2.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血液腫瘤科,河南 鄭州 450000)
索拉非尼作為一種多激酶抑制劑,能抑制PDGFR、VEGF等靶點的同時,還可阻斷mek/raf等信號傳導通路,阻斷腫瘤細胞再生。索拉非尼不僅能顯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延長壽命,而且能增強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但其在抑制VEGF及PDGF的同時,皮膚毛細血管首先被損傷。眾所周知,皮膚是人體第一保護屏障,但是也最容易受到傷害,皮膚接觸外界壓力時,毛細血管再次受到損傷,皮膚毒性就會加重[1],使用索拉非尼后的過度抑制可能導致汗腺的生理性改變[2]、降低毛細血管的恢復能力[3],進而導致血管自我修復能力喪失,甚則血管發生退行性病變[4],皮膚毒性產生,其中最常見的是皮疹和手足綜合征,常常在服用后4~6周出現,甚則自服用當天起全身瘙癢、皮疹就會出現。患者體質不同,反應輕重亦不一,我們要發揮中醫優勢,中西醫結合減輕索拉非尼的副作用。本文從臟腑論治索拉非尼的皮膚毒性,闡釋如下。
1 從心論治索拉非尼的皮膚毒性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 (VEGF)抑制劑(此文指索拉非尼)抗血管生成的同時,阻斷了其他細胞生長通路,如: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和其他一些酪氨酸激酶,皮膚毒性隨之發生,如:手足綜合征,皸裂、干燥、皮疹、斑禿、甲溝炎等。這些均可歸屬于古代中醫學中“血燥”“斑疹”等范疇,其中描述了多種疼痛、瘙癢、瘡瘍等癥狀,正如《素問病機十九條》所言:“諸痛癢瘡,皆屬于心。”可見心功能的損傷是導致皮膚毒性的一個重要元素。下面筆者論述皮膚毒性與心火的關系,進而明確清心火的重要性。
1.1 心在五行中屬火
此處“心”古今醫家大多理解為“火”,心屬火,為陽中之陽,又稱“火臟”,火熱熾盛,熏蒸皮膚,煎灼津液,生風化燥,燒灼皮膚,繼而出現紅腫、風團、瘙癢、疼痛。“勞汗當風……心屬火,后化熱,故瘡瘍屬于心也。”明代醫家吳昆如是寫道,此可解釋為:熱甚則痛,熱微則癢,瘡乃熱之甚也,火灼肌肉,近則痛,遠則癢,火熱燒灼則成爛瘡,則心為火,故屬之。
1.2 心布于表
追溯到古代,諸多醫家均對心與表關系作出闡釋,如:“心屬陽,居膈上,心布于表也。”馬蒔如是說。《皇帝內經》曰:“肝生左,肺藏右,心布表。”張志聰論述心布于表時解釋道:“心為陽臟而主火,火性升發炎散,故心氣布于表。”皮膚在現代醫學被解釋為:包裹于身體表面-皮膚(身體表面包在肌肉外面的組織),與外界自然一切事物相通,發揮保護、排泄、調節體溫和感受外界刺激等作用的一種器官,在人體器官分布面積上處于第一位。所以此處之“表”可理解為皮膚也。
1.3 心主血脈,其華在面,在液為汗
心主血脈包括兩個方面,其中與皮膚毒性的產生密切相關的為:心主脈。心氣調控脈管舒縮,血液周流全身而不瘀滯,脈管通暢,進而濡養周身皮膚。“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榮色,意在表明心氣足,血流通暢,可供給皮膚新陳代謝,發揮汗腺正常排泄功能。心在液為汗,汗液化生的源泉為心血和心精,所謂“奉赤化血”。《素問·五臟生成論》言:“心在液為汗。”心血充足,汗化有源則可滋潤皮膚,心火過盛,則汗出過多,皮膚干燥、脫皮隨之出現;心血化生不足則導致血虛生風,風燥傷于肌膚,則肌膚失養,進一步導致全身瘙癢,甚則導致皮膚干燥、脫屑。
1.4 心藏神,主神志
《素問·靈蘭秘典論篇》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此處“神明”可理解為人的意識、思維、情志的作用。腫瘤患者多情緒焦慮,服用索拉非尼后因藥物副作用,加重心理負擔,甚則驚恐不安。瘙癢為人的主觀感受,即心的感受,此為心主神明的體現,心主神明,神明宜靜,瘙癢日久,劇烈難忍,則會擾動心神,出現煩躁不安、乏力失眠的癥狀,從而增加患者心理負擔,而長期的負性情緒積累又會降低免疫力,影響藥效。
2 從肺論治索拉非尼的皮膚毒性
2.1 肺氣宣發溫養皮膚
肺在保持呼吸通暢的同時,將營養物質傳輸至全身。通過肺氣的宣發,周流全身,將脾傳輸到肺的水谷精微也輸注全身,傳輸衛氣,外達皮毛,以溫養分肉,充養皮膚,調節腠理。《靈樞·經脈》云:“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簡單來說就是肺氣供養皮毛生長。肺氣不足則皮毛不生;肺氣失宣,則皮毛枯槁、脫屑。“邪在肺,則病皮膚痛”[5],索拉非尼常見皮膚毒性之一為皮疹,而皮疹按程度分為四級:皮膚出現丘疹、紅斑、瘙癢、小膿皰,可歸為Ⅰ級;癥狀輕,無需干涉,丘疹膿皰的覆蓋面積 <50% ,日常生活不受限制,歸為Ⅱ級;Ⅲ級、Ⅳ級由于丘疹、膿皰、皮疹分布面積廣,疼痛明顯、流膿藥物干預是必要的。索拉非尼所致皮膚毒性反應多屬肺衛受損所致,肺失宣發,衛氣不得開合,腠理失司,導致皮膚病。
2.2 肺氣足則皮膚堅
另外,還需重視補肺,《素問·痿論》指出:“肺主身之皮毛。”肺主一身之氣,皮乃肺之合也,發生于皮,肺氣足,皮毛生養有源,汗化有度,皮毛紅潤不致脫屑、發斑。反之,肺氣虛弱,肌膚失養,則毛發枯槁,甚至導致脫發。
3 從脾論治索拉非尼的皮膚毒性
《內經》言:“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脾主運化水濕,行津助載,若脾主運化水濕的功能失常,浸淫于皮膚,水濕不得散布,則發為水腫、脹滿。濕熱浸漬,浸淫肌膚,則發為濕疹、瘡瘍。
3.1 脾主統血,在體合肉,主四肢
《景岳全書》記載:“脾主統血,脾氣虛則不能收澀.”脾主統血實乃脾氣之運化、固攝發揮作用。脾氣為后天之氣,成于元氣而生,受營氣滋潤,協同于衛氣,固攝血液在脈中運行,脾氣虛,可見皮膚委黃;脾氣滯于脈中,發為紫癜、丘疹、膿皰。《素問·痿論》言:“脾主身之肌肉。”亦有《靈樞·五變》曰:“肉不緊,腠理疏,則善病風。”脾失健運,轉輸無力,四肢營養缺乏,筋脈枯槁,皮膚干燥、龜裂。
4 從肝論治索拉非尼的皮膚毒性
肝主疏泄而藏血。中醫認為瘙癢的主要致病因素是“風”,而“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肝藏血筋脈肌肉得以濡養,皮膚紅潤有光澤,若血不榮膚,在體表可見大片風團、紅斑、皮膚干燥甚則脫屑,可歸為“血虛風燥”。肝具有維持全身氣機疏通暢達、條達而不致瘀的作用。癌癥患者,常年擔心病情加重而抑郁寡歡,形成肝氣郁結的證候。服用索拉非尼后出現皮膚毒性的肝郁氣滯患者,此時暢情志、解郁結為當務之急。各種類型的腫瘤無論何種分期都會伴隨情志不遂、肝郁氣滯。積郁在心、肝郁氣滯、憂思傷脾,五臟失去陰平陽秘之平衡,木火刑金,而致皮膚毒性的發生。
5 驗案舉隅
筆者有幸侍診于高萍教授(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其臨床采用中醫辨證論治索拉非尼皮膚毒性,效果良好,現列舉高萍教授所治病案1例,介紹如下。
黃某,男70歲,退休職工,2018年2月22日確診為原發性肝細胞癌。行手術治療、TACE、化療4個周期后病情進展,于 2019年1月16日口服索拉非尼(200 mg qd po),服藥1個月后出現皮疹、皮膚干燥、脫屑,以手足部尤甚,瘙癢異常,于診所應用激素類藥膏后仍不緩解,遂求診于中醫,癥見:全身多發皮疹,局部脫屑,流膿,瘙癢異常,心煩,納差,失眠,夜眠不足3 h,小便短赤,大便干。舌尖紅,苔黃,脈弦。予水牛角9 g、生地黃10 g、玄參9 g、連翹12 g、金銀花12 g、竹葉心10 g、梔子9 g,桑白皮12 g、枇杷葉15 g、川貝母10 g、生白術15 g、炒白術15 g、雞內金15 g、柴胡15 g、酸棗仁15 g、茯神12 g、全蝎3 g。7劑,水煎服,早晚溫服。患者服藥7天后,再診,刻下見:全身散在陳舊樣皮疹,局部已結痂,無流膿,瘙癢較前減輕,心煩緩解,納轉好,二便調。舌微紅,苔薄白,脈稍弦。辨證論治后,上藥去犀角、梔子、連翹,加用桔梗15 g、枳殼12 g,14劑,水煎服。患者服藥后皮疹消退,無瘙癢,流膿、納可,眠可,二便調。舌紅,苔薄白,脈緩和有力。遂繼續服用索拉菲尼治療原發性肝癌。
按:高萍教授治療此案,注重于清心火、安心神,同時注重宣肺健脾、搜風通絡。《素問·至真要大論》曰:“熱淫于內,治以咸寒,佐以甘苦。”遂用水牛角(犀角乃國家保護動物)清熱解毒,生地滋陰涼血,玄參清涼瀉火、解毒滋陰,共奏清熱而養陰之效。連翹、金銀花、竹葉心歸心經,清心火,解熱毒,輕清透泄,使熱邪有外達之機,體現“入營尤可透熱轉氣”。桑白皮、枇杷葉、川貝母宣肺而養陰;生白術、炒白術、雞內金健脾養胃,以防寒涼藥物滋膩傷胃;柴胡以疏肝解郁,減少郁滯。酸棗仁;茯神安心神,蟲類藥物全蝎搜風通絡、以毒攻毒。后癥狀好轉后,去犀角、梔子、連翹,加用桔梗15 g、枳殼12 g。寒涼藥物苦寒礙胃,故去之。加用桔梗、枳殼一升一降,達到宣降肺氣、暢通氣機的效果,臨床療效好。
6 結語
索拉非尼作為一種新型靶向藥物,在延長患者壽命,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其皮膚毒性成為困擾患者的一大難題。高萍教授著重從臟腑考慮,根植于病機十九條:“諸痛癢瘡,皆屬于心”,癢痛在表,其本在心火。高教授著重清心火,多用生地、水牛角、玄參、連翹、金銀花、竹葉等清熱之品;著眼于“肺在體合皮,其華在毛”,肺氣損傷,失于宣發開合,腠理失司,皮膚毒性自然而生。其倡導宣肺不忘補肺氣,用貝母、桑白皮等宣肺氣之品;立足于“脾運化水濕”采用健脾之品,多用黃芪、白術、雞內金、太子參等平補脾氣之藥。基于“風”與皮膚瘙癢的關系,從“諸風掉眩,皆屬于肝”出發,應用平肝疏肝之品,如柴胡、白芍、香附、佛手等。臨證加減,體現“治病求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