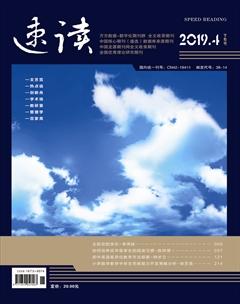從國寶中看盛唐對外交流
張茜
摘 要:眾所周知,唐朝(公元618—907年)在中國歷史和古絲綢之路對外交流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甚至是核心地位,本文試圖從對國寶的解讀和鑒賞中窺探盛唐的大國外交與文化交融,以期能夠從“開放性”“多元化”的角度了解唐朝歷史。
關鍵詞:唐朝;國寶;外交;絲綢之路
唐朝連同隋朝被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是繼秦漢之后中國歷史發展的第二帝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國力最為強盛,科技最為發達,文化最為繁榮的黃金時代,以致至今國內外社會仍大多使用“唐人”“唐裝”等明顯具有唐元素的稱呼,足見盛世唐朝在世界的強大影響。然而,“引進來”在唐朝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在發揮著重要作用,多元化作為其重要特征,無論從科技、經濟還是文化、藝術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借鑒亞歐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影子。
一、鑲金獸首瑪瑙杯
唐鑲金獸首瑪瑙杯于1970年在陜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現藏于陜西省博物館。鑲金獸首瑪瑙杯杯長15.6厘米,口徑5.9厘米。選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紋理雕琢而成。杯上口近圓形,下部為獸首形,獸頭上有兩只彎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卻似牛,嘴部鑲金帽,眼、耳、鼻皆刻畫細微精確,獸首的口鼻部有類似籠嘴狀的金冒,能夠卸下,突出了獸首的色彩和造型美。獸首瑪瑙杯是已發現的唯一一件唐代的俏色玉雕,也是已發現的唐代玉器中制作工藝最精湛的一件。
此件瑪瑙杯其造型是西方一種叫“來通”的酒具。“來通”是希臘語的譯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獸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體可以從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來注神酒,當時人們相信用它來注酒可以防止中毒,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禮儀和祭祀活動。
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見,在中亞等地的壁畫中也有出現。在中國,從唐代以前的圖像資料來看,這種酒具常出現在胡人的宴飲場面中,唐朝貴族以追求新奇為時尚,而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貴族崇尚胡風,模仿新奇的宴飲方式的見證。
從瑪瑙的材質上,也能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跡。纏絲瑪瑙多產自西域,類似這樣造型的器皿,在中亞、西亞、特別是波斯較為常見。
從寶物的出處上,在《舊唐書》中有“開元十六年大康國獻獸首瑪瑙杯”的記載,此件寶物很有可能是中西亞某國進獻給唐朝的禮物,其意義非同一般,另有一說是唐代能工巧匠比照著外來的樣式打造而成,但無論是哪種可能性,無疑都將古代中國文化與中亞、西亞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是在東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誕生的一件重要文物。
二、鹿紋銀碗(又稱鹿紋十二瓣銀碗)
鹿紋銀碗(又稱鹿紋十二瓣銀碗),1963年出土于陜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為唐朝的盛食器,現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銀碗高4厘米,口徑為14.7厘米,碗壁錘揲出12個凸凹起伏的瓣狀,口沿以下內束,折成略有弧狀的斜壁,圈足。內底中心飾一只花角立鹿。口沿下刻銘文一行。這種制作技法和造型風格在古代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十分流行,是西方傳統器皿的特征。
鹿作為器物的裝飾紋樣,在中國和西方地區均有,但形象特征卻有區別。巴克特利亞和粟特藝術中鹿是常見題材,但從此銀碗上的12瓣樣式中可以看出,每瓣較粗大,比起在巴爾干半島銀器上的細密的瓣相比要少,因此更貼近于粟特地區的風格。
中國裝飾紋樣中鹿的形象均為平頂,呈靈芝狀,有時被稱為“肉芝頂”鹿。沙坡村鹿紋銀碗中的鹿角左右展開,每面四個支角,整體呈火焰狀,正是“花角鹿”的形象。據林梅村先生考證:這個銀碗,特別是碗心的鹿紋圖案,和馬爾夏克刊布的OS136號粟特銀碗基本相同,后者打制一粟特王族族徽符號,類似的符號亦見于粟特王發行的錢幣。口沿下銘文屬于粟特文,讀作“祖爾萬神之奴仆”。馬爾夏克將這種銀碗的流行年代定在公元7—8世紀。從器物特征及時代上看,產地還是最接近中亞粟特地區。
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一帶的古老民族,語系為古中東伊朗語,從我國的東漢時期直至宋代,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以長于經商聞名于歐亞大陸。主要商業活動內容是從中原購買絲綢,而從西域運進體積小,價值高的珍寶,如瑟瑟、美王、瑪瑙、珍珠等。絲路北道的碎葉城即粟特人所筑,入唐后王方翼擴其形制,定為北道征收過往商稅的關卡所在。《南部新書》記長安“西市胡入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栗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國境內的粟特人主要承擔著這種以畜易絹的互市活動。新疆境內作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較短途的牲畜生意。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官方往來,還是市井貿易上,唐朝和以粟特人為代表的中西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往來比較密切,時至今日,在新絲綢之路的征途上,仍然是我們開展友好交流、互通合作的重要內容。
三、盛唐成為亞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幾點原因
唐朝時期的中國成為亞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不僅在于其國家統一,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最強大的國家,還與唐朝實行的“開放”的對外政策分不開,對外政策開明,對“遠夷”不歧視。唐太宗認為自己對華夷是一視同仁的。這種開明的對外政策,不僅在唐朝有少數民族官員,甚至有相當數量的外國官員。由此,唐朝對以漢文化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高度自信也可見一般。唐朝認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對外來文化、藝術,毫無恐懼感,而采取“開放”政策。這是積極主動的文化政策,它采納、吸收有益的外來文化,對之進行改造,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向外大力宣傳和輸出唐文化,影響亞非乃至世界各國文化。唐朝堅信“盛世無忌”和中華傳統文化有吸收、改造外來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懼怕外來文化的沖擊。